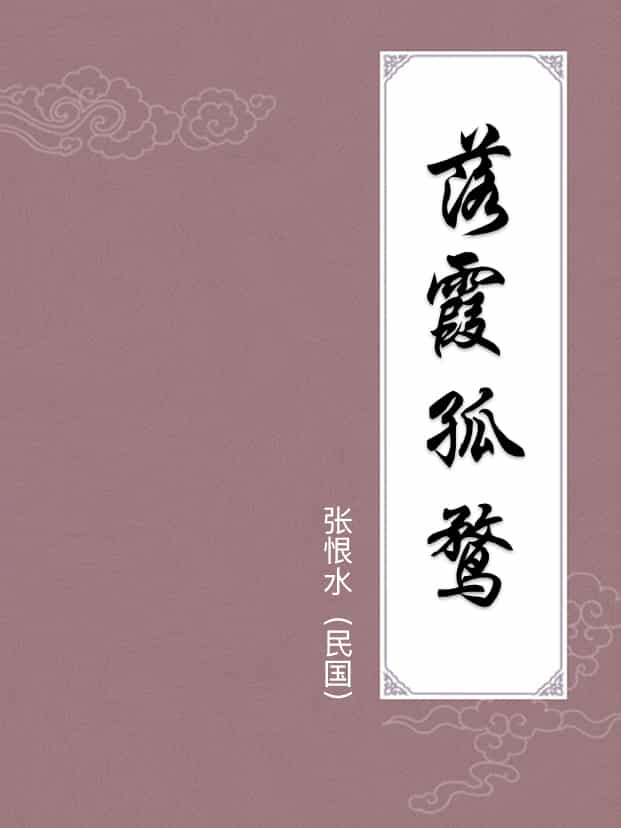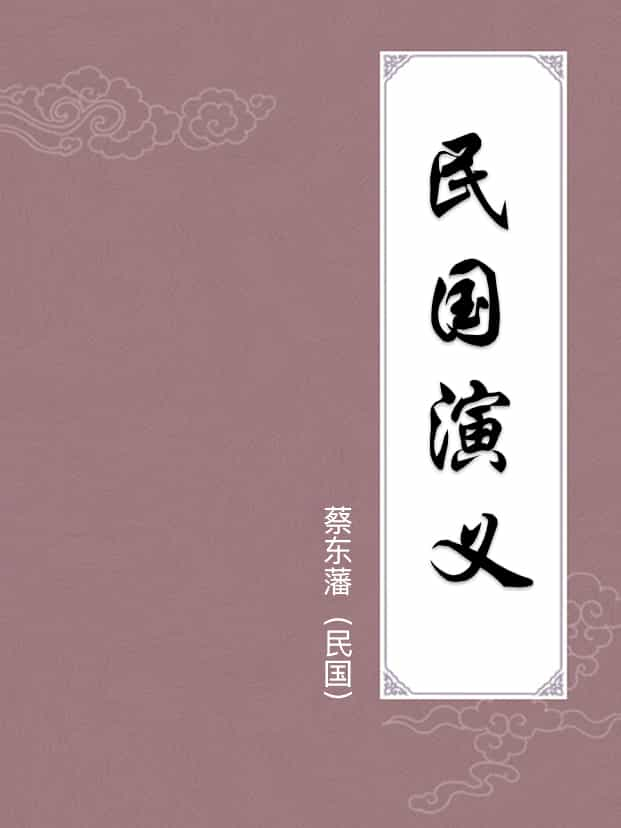却说冯姥姥反问一声,有什么事找我办的吗?这一句很平常的话,她倒难为情起来了。冯姥姥以为她怕惹祸,不敢招待,便道:“姑娘,我是老远地跑了来,特意看你的。咱们在小胡同里走走,我有两句话对你说一说。你能不能抽开一点工夫?”
落霞道:“凭怎么忙,说两句话的工夫,总有的。”
冯姥姥于是携着她一只手,慢慢地转弯抹角地在小胡同里走,先看了一看身后无人,便笑道:“你救的那个人,在南方做了官了,你这份功德不小。”
落霞道:“哦!做了官了,这也谈不上什么功德,天下事就是这么样,人家敬我一尺,我敬人家一丈,谁让我受过人家恩的呢!”
冯姥姥点了点头道:“姑娘,你这份心眼儿不错,他有信到北京来,派人问候问候着我,也问候问候着你。”
落霞道:“这倒不敢当,我心里就惦记着,这人逃出命来没有。既然是很好,这件事揭过去了,也就不必谈了。因为我可和旁的人,弄得不好,容易生出麻烦来的。”
冯姥姥道:“不,人家可忘不了你的好处。他写了一封信,托我转交给你。”
说着,把身上带的那封信掏了出来,向落霞手里一塞。落霞一看那信皮上写着“落霞女士亲启,江缄”几个字,不觉两朵红云,在脸上泛了出来,且不看信,向衣襟底下一塞。
塞在衣襟下一会儿,又掏了出来,交还给冯姥姥道:“这个不好,我长这么大,没有和外人通过信,再说,我也认识不了三个大字,还瞧个什么信?”
冯姥姥道:“哟!姑娘,你这是什么话,我老远地送了来,你瞧也不瞧,你交给我做什么?我带回去吃呢?我带回去穿呢?人家寄来了,反正我也退不回去。”
落霞道:“由哪儿来的由哪儿退,还有什么退不了的?”
冯姥姥道:“为什么?你恨那个写信的人吗?你瞧瞧也不要紧,他说的是好话,你就听着;他说的不是好话,你就当没有接着这封信,那不就完了,也许他信上有什么要紧的事哩!”
落霞道:“那我就留下吧。可是这位先生,也太多事,写个什么信。幸而这封信,是请你交给我的,我不怎样认识他,你是知道的。若是这封信落在别人手上,这可会成了笑话了。”
说时,把这一封信,又很不在意地,揣在身上去。冯姥姥道:“你先瞧瞧好不好,也许……得,你拿回去慢慢地瞧也好,恐怕你还有不认识的字,慢慢猜着去。你若是得闲的话,可以到我家里去坐坐,我们小二妈,老惦记着你,盼望着你去谈谈呢。”
落霞道:“我倒也想着这位大嫂子,你见着她,替我问好。我要回去了,怕家里人找我呢。”
冯姥姥握着她的手,望着她的脸道:“你好好地做事,耐着吧!一个人总有个出头之日的。”
落霞真也怕家里有人找她,便道:“我要回去了,有空我一定去看你。”
说着,抽转身,向回路就跑。跑了十几步,她又跑回来,叫道:“姥姥,姥姥,我还有话说。”
冯姥姥看她那样着急的情形,连忙就转过身来,站着问道:“姑娘,我叫你别忙,有话尽管说,你又忙着要走。”
落霞站到冯姥姥身边,低了头,眼光下垂,却将一只脚在地上涂抹着,画椭圆形的圈圈。冯姥姥道:“姑娘,你有什么事,别为难,我一定给你去办的。”
落霞低了头,低声说道:“这一封信的事,你可别对人说。”
口里说着,脚下依然在地上不住地乱涂。
冯姥姥道:“这个你放心,我长到这一大把年纪,难道这一点事情,我都不明白吗?”
落霞道:“这信没贴邮票,是封在你的信里呢,还是有人送到你那儿的?”
冯姥姥于是把万有送信的话,略略说了几句,落霞道:“唉!这可不好,别种人知道还好一点,这种人知道,飞短流长,可别出乱子。”
冯姥姥道:“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能瞎说什么。要不,他要来问回信的话,我就说我没有找着你就是了。这样一来,以后也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
落霞道:“对了,千万不能把我这里的住址告诉他,知人知面不知心,也许将来他借着缘故找上门来,那我可受不了。”
冯姥姥也觉她这话顾虑得是,连连点了几下头。笑道:“你回去,我心里明白就是了。”
落霞听冯姥姥所说,非常的诚恳,这才放心回家去了。
到了家里,所幸家里还没有什么人叫她,马上向自己屋子里一溜,闩上了房门,将那封信从身上掏出,背对着窗户,伏在床上,将信展开来看。那信几乎完全是正楷字,写的是:
落霞女士惠鉴:我写上这一封信,恕我冒昧了。我上次有了生命的危险,蒙你不避嫌疑来救,我用不着说客气话,实在是感激到一万分。我的良心责备我,不许我对女士置之不理。但是离开北京几千里,没法感你的大德,所以只好写一封信来问候。你若是用得着金钱帮忙的地方,请你不客气,转告着送信的人,要把钱寄到什么地方,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帮助。钱虽是万恶的东西,用之得法,也可以帮人做好事,帮人做好人。
我想你是个有热血的女子,一定不会为一点不相干的嫌疑,以及施恩不图报的话,拒绝了我这点敬意。我现在是在南方飘流着,有时候在上海,有时候在香港,有时候又在广州,不过我和送信人是常通信的,这人也很老实可靠,有信让他转,决不误事。我这封信字字是真言,所以不谈那些写信的虚套,当不见怪。祝你平安。
受恩人江秋鹜上言
落霞看完了这封信,才知道“江秋鹜”三个字原来是这样写。当时草草看了一遍,觉得人家的意思,原不算坏。将信捏在手里,一听屋子外,并没有什么响动,于是忍不住把信纸展开,又重新看了一遍。起初觉得信上的字,有十分之七八可以认识。再仔细地斟酌一番,把不认识的,也慢慢猜出,也就很明白了。
将这张信纸放到信皮里面去,然后叠了好几叠,放到身上小衣袋里,信是不看了,便坐在床沿上默想那信中的话。设若我真和他要钱的话,几百块钱,或者可以帮助我的。有了几百块钱,我就可以跳出这个火坑了。像这样的冬天,我真冷得够受,第一件,我就要做上一件大棉袍子穿。长了这么大,没有盖过一条新棉被,有了钱,也得尝尝新。我屡次想找我的娘家,总无法子可找。假如有了钱的话,我在南方几省的大报上,到处登广告。好在我是云南人,我总是记得的,我在云南报上,更把广告登得久久的,把我四五岁时匪人拐走以前的情形,记得的都说出来,或者我父母知道了,把我寻了去也未可知。到了那父女重逢之日,真是乐事了。
这样想着,便觉得十分高兴,索性拉了那两个破枕头,叠着一叠,放在旧被上,自己横着向床上一躺,将头高高地枕起,把这有味的事,更仔细想上一想。第一层所想到的,便是怎样地摆脱赵家呢?若要说是用钱来赎身,也许这里的主人,要大大地讹诈我一笔。而且我自己出钱赎自己,人家问我钱自何来?若是托别人来赎,谁又是可托之人?再不然,便是偷跑了,跑出去了,哪里可以托脚呢?若是不找个固定的所在,一个六亲无靠的女子,无钱是行动不得。有了钱,行动也是处处担心。若是不走不跑,单要人家一些钱来,那么,又在哪里存着?难道也像这封信一样,藏在小衣袋里吗?那么未免不像话了。若是让人知道了,说我偷的,倒也罢了,反正主人说丫头做贼,那是常事。若人家说我是用身体换来的,那就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我要钱有什么用?一个人到了有钱都无用处,这活着还有什么意味?自己只管这样一层一层想着,由有办法,想到无办法;由无办法,更想到用不着要有什么办法,这个人的心事就灰透了。
就是这样地呆想着,渐渐地不知不觉在睑泡上挂着两行泪珠,翻了一个身,将脸偎在破棉被中间,正想大哭一顿,忽听得一迭连声地叫着落霞,她一听之下,一面答应来了,一面赶紧用袖子擦着眼泪,就向外走。
赵太太在屋子里躺在沙发上,很自在的样子,口里衔着一支烟卷,一见落霞便板了脸道:“我口渴得要命,快给我倒杯茶来。叫了你这大半天,你到哪里去了?”
落霞哪能说是在屋子里想心事,只有不做声,倒了一杯热茶来。赵太太道:“看你这死样子,倒一杯茶,好像都不服气,怪不得我叫上了你的脸,都不答应了。我喝我自己的茶,为什么要看你的颜色?放在茶几上吧。哪个要喝你倒的丧气茶?”
落霞听了,心里倒好笑。人讨厌罢了,怎么倒的茶也丧气?既然是知道我倒的丧气,那不该叫我去倒。心里这样想着,因为忍住笑,就淡淡的样子,将那茶杯在茶几上放着,脸也就不向着赵太太。赵太太道:“我越说你不服,你倒真给我不服起来了。你要不服,就给跪下去。”
落霞道:“我又没做声,怎样是不服了?”
赵太太道:“你口里没做声,我猜着你心眼里,这会子也不知在怎样骂我哩。你就是不做声,难道我看你的颜色,就看不出来吗?我告诉你,你那种手段,不必用到我面前来玩,我比你会得多呢。”
落霞知道太太要打起人来,就是突然而来的几下,不屑于先骂起来作通知。现在她骂个唠唠叨叨,这是往骂的一条路上办,索性不做声,让她一人叽叽咕咕骂去。自己低了头,便挨挨蹭蹭,也要往房外走。
不料赵太太今天却变了态度,突然走上前来,一把揪了落霞的短头,就向怀里一拖,骂道:“贱人!你往哪里走?你好好给我跪倒!你若不跪倒,今天不要想活命。”
说着,咬了牙齿,将脚一顿,把落霞的头,就向下一按。落霞一看赵太太发了恶,若要再执拗着,免不了皮肉受苦,便趁着势子跪了下去。赵太太见她已经跪下,才把揪头发的手松了。鼻子哼了一声道:“我看看是你强得过我,还是我强得过你?”
两手一抄,向沙发上落了下去。
那沙发是个半新旧的,直把她半截身子吸了下去。落霞见她的气生大了,哪里还敢做声,跪在地上抬头不得。赵太太嘴里又叼了一支卷烟,斜瞟着。落霞跪在地上,她倒清闲自在地那样躺着。
落霞约莫跪了半小时,那个表少爷朱柳风却来了。他在堂屋里张望了一下,见屋子里地上跪着一个人,觉得一走进来,这个跪的人,未免有点难堪,就不曾进来,在外面屋子里坐下了。赵太太道:“柳风,你为什么不进来?”
柳风见姑母见召,不能不进来。便笑着走进来道:“你老人家又发雷霆之威。”
赵太太道:“并不是我生气,这东西她存心和我闹别扭。我就和她闹一闹,看是谁闹得过谁?”
柳风笑道:“你老人家,犯得上和她一般见识?高兴教训她几句,不高兴随她去。这大的人了,跪在地上也真不矮,我讲个情,放她起来吧。”
赵太太便向落霞喝道:“看在表少爷面上,饶你这一次,滚起来吧!”
落霞实在不好意思见人,听了一声说起来,两腿一起,头也不抬,向屋外就钻。赵太太道:“你忙什么?人家和你讲了情,也应该谢谢表少爷,怎么一拍腿就走了。”
落霞知道表少爷在这儿是个红人,更不敢得罪他,因之复又转身来,向朱柳风微微一鞠躬,然后出门而去。当时受了这番羞辱,把新愁旧恨,一齐兜上心来,心想,正合了表少爷那一句话,跪在地下,还是不矮。我这样大年岁的人,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为什么动不动就要我罚跪?我若有一天认识了大总统,必定和他建议,把拐匪都定成死罪,买丫头的人家,都要受罚。但是我怎样会认识大总统?这也奇怪,做官的人,怎么也就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层。哦!是了,做官的人家,哪个不买丫头,他们怎么又会反对呢?自己把这样不相干的思想,只管放在心里,事情是照样做,饭也不想吃,茶也不想喝,做完了事,便是坐在屋子里呆想。
这一天晚上,直到头靠了枕头,还依然想着,糊里糊涂地思索,也不知如何就天亮了。自己提了菜篮,又去上街买菜,还走不到胡同口,就碰到了那个江秋鹜迎面而来,彼此似乎是极熟了,他抢上前一步,执着落霞的手道:“你怎么还在赵家?我不是寄了一封信给你,约你逃走的吗?”
落霞一阵害羞,不觉低了头,这话可答不出来。江秋鹜见她不说话,拖了落霞的手便走。落霞也情不自禁,只管跟了他走。
约莫走了好几个胡同,走到一个似乎宫殿的大屋子,一进门,便看到有几十层台阶,在台阶最上层,有人在那里招手。落霞看时,便是江秋鹜,不知他是什么时候,跑到那最上一层去了。自己慢慢地向上爬,好容易爬了上去,出了一身大汗。走到那上面一看,原来是个很平坦的地方,遍地铺着大石板,光滑平整,像镜子一般。上面正屋,八根红柱落地,四角飞檐的一所大殿。
落霞正这样想着,姓江的怎么把我引到这个庙里来了。这句话不曾出口,秋鹜笑道:“这不是庙,这是侠客家里,专门和天下可怜的孩子们报仇雪恨。你看,你的仇人也捉来了。”
只这一声,门边拥出七八个人,将一个穿灰衣的短装汉子,拖了出来。那人在地上滚着,大叫饶命。落霞认得那个人,正是十年前,拿着一块糖,哄了自己,抱着跑的。那些人都说,这种拐匪,一个个要把他治死。说着,几个人抬了他的手脚,就向平台的下面一丢。
那平台下面,是个万丈深坑,只听扑通一声,那个拐匪就抛沉到水里去了。那些人鼓着掌大叫痛快,落霞也不觉地鼓起掌来。秋鹜喊道:“诸位慢着鼓掌,还有那个姓赵的妇人,没有处治她。”
那些人说,打死她,打死她。于是几个人跑到屋旁边,七手八脚,果然将赵太太拖了出来。
那赵太太一见落霞,跪到她面前,双手抱了她的脚道:“落霞,落霞,你救我一救。你从小在我家长大,你就不念我一点抚育之恩吗?”
说时,又哭又喊,拖了落霞的脚,死也不放。落霞见她说得可怜,也不免坠下两点泪。两只脚又让她拖得累死,难受极了,自己撑持不住,也向地下一倒,这一倒,自己一惊,睁眼一看,不是倒在地上,是倒在床上,原来做了一个梦。
赵家下屋子里,是没有电灯的,只有一盏点一根灯草的,小煤油灯,屋子里昏暗无光,真也有些像梦境。于是坐了起来,将灯芯扭着大了一些,坐起来一想道:“梦境真算是痛快,然而天下哪会真有这样一个地方?但是这话也难说,江秋鹜这种人,无缘无故,能把许多钱相助,而且官厅又要捉他,这不是侠客是什么?也许他们做侠客的,真有这样一个,那就好了。”
就是这样不断地想着,猛一抬头,窗户翻作白色,原来天真大亮了。
落霞心里想着,这和梦境差不多,不要江秋鹜真在门外等着我,赶忙披衣下床,开了大门,就向胡同里走,这时天色刚亮不多时,哪里有什么人走路,走在胡同中间一望,空荡荡的,只有那砭人肌肤的寒风,带着地上的黄沙石子,刮起来四五尺高,向人身上乱扑。风吹在脸上,已是冷如刀割,再加上石子打在脸上,痛上加痛,更不可当了。落霞连忙向大门里面一缩,心想道:我这人太傻了,怎么把梦境当真事呢?这才回转屋子里去了。正是:
欲平积恨除非梦,醒后还思入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