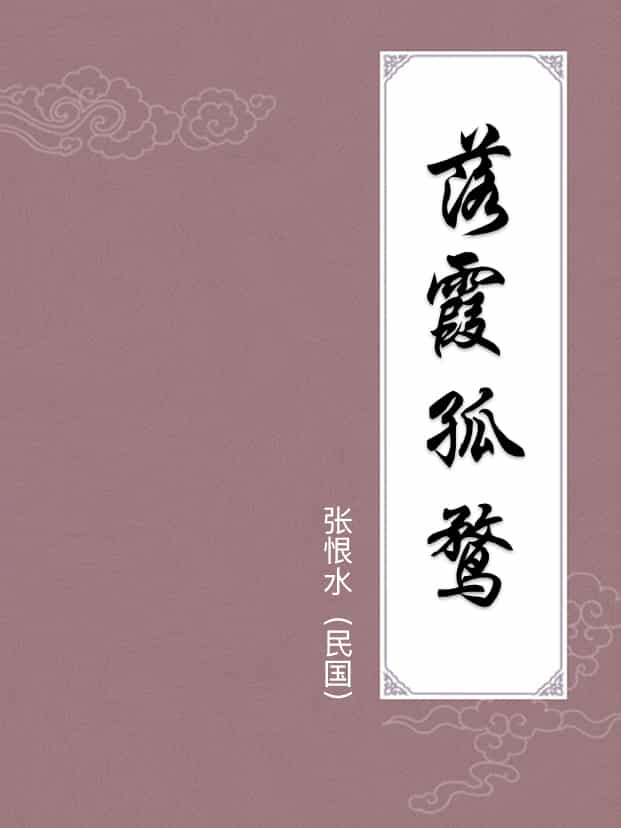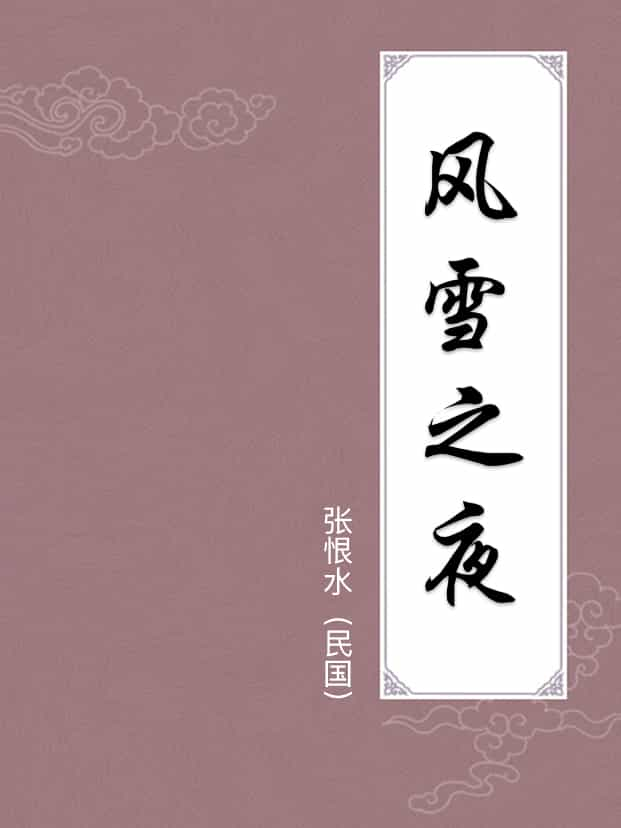却说落霞正在调弄香粉,想到了自己的年岁与身份问题,只管出神,不觉把玻璃瓶落在地板上了。连忙弯腰一看,所幸瓶子是装满香粉的,虽然跌落下来,还只跌了一道纵的裂痕,未曾破开,连忙捡了起来,匆匆忙忙,换个玻璃瓶装了。这个玻璃瓶子,不能让大小姐看见,便揣在衣兜里,以便等到出门时,丢到大街上去。大小姐也因为她的表弟朱柳风要来,将小书房里检点了一番,拿了一本新出版的翻译小说,坐在沙发上看,落霞慢说是打碎了一只小玻璃瓶子,就是打碎了她再大些的东西,她也来不及过问了。
过了一会儿,大门外按着电铃响,婉芳连忙喊道:“落霞落霞,开门去,开门去。”
她一面说着,一面跑进来找人。落霞听到她那样急促的呼声叫去开门,便知道是朱家表少爷来了。因为这样两种暗号,可以识别,第一是那铃声响得非常长久。第二是婉芳来叫去开门,因为若是别人来了,小姐是绝对不去注意的。
落霞抢着去开门,婉芳也抢着到书房里去。刚坐下,拿起那本小说,便听到外面皮鞋响声,是表弟到了。分明听到他拉着门,已是进来了,却把两只眼睛,死命盯住在书本上,似乎一点也不知道有客进来似的。柳风道:“真用功呀,人进来了都不知道。”
婉芳一抬头,“哟”了一声道:“这真对不住,我看书看糊涂了。”
一面说着,一面站起身来,将书向沙发上一扔,伸了一个懒腰,向着柳风笑道:“外面大雪停了没有?天气冷得很,我怕你不会来的呢。”
柳风笑道:“我从来不肯失信的,说了来我准来。”
婉芳道:“那么,可以奖励一下子,就在我这里吃午饭吧。我叫他们给你蒸上一腿南京鸭子,再扇上一个火锅,好不好?”
柳风沉吟着道:“照说是极优待了,但是我十二点多钟,还约会了一个朋友,恐怕来不及在这里吃饭了。”
婉芳道:“你既然有事,那就不敢强留了。”
一面说着,一面坐下来,懒懒地把那本书又捧起来看。柳风笑了一笑,便道:“我去看看姑母去。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她老人家起来没有。”
他说着,自向上房里走。
赵太太坐在堂屋里,围了炉子坐着,看到玻璃窗外院子里的雪,已经慢慢衰微下来,落得不是那样大,便道:“咳!可惜一场雪,只下了七八成,再下一两个钟头大的,这雪就好看了。”
柳风一推门进来,赵太太见他穿了格子花呢大衣,脖子上围了一条白绒绳围巾,便道:“你不是到书房里去了吗?怎么大衣也没有脱?”
柳风道:“我就要走的,由门口经过,顺便进来看看。”
赵太太道:“下雪的天,在家里烤烤火多好,就不必到处乱跑了。”
柳风笑道:“做男子的,哪里能够像太太小姐一样,可以平平安安在家里烤火?”
说到这里,杨妈进来了,笑道:“表少爷,这样冷天,还是穿中国衣服好,西装受不了呀。”
柳风道:“我穿了西装,也就不觉得冷了。”
杨妈抿嘴笑道:“既是不觉得冷,为什么不脱大衣呢?”
柳风道:“我就要走的。”
杨妈道:“那不好,你要吃了午饭去。小姐给你预备了咸鸭子,又预备下了火锅,你不吃了去,太对不住人了。”
柳风道:“落霞怎不来说话,她一开门,就不见了。”
再要说时,婉芳进来了,对杨妈微微瞪了一眼道:“你知道什么?乱留客。你想想是吃火锅咸鸭要紧呢,还是去做事要紧呢?表少爷很忙,你拼命地留住人家,他就是吃了饭,心里也是挂记着他的事,吃得一点不舒服。”
柳风笑道:“表姐越来越会说,叫我真没有法子分辩。”
一面说着,一面脱大衣。
大衣脱下来,杨妈接过来了,他就除下围巾,随手要交给杨妈。婉芳道:“杨妈,你可别接着表少爷的大衣,人家真有事呢。你瞧,帽子都忘了摘了。”
柳风取下帽子,向婉芳拱了一拱手道:“得!表姐,你包涵一点,我认错了。”
赵太太先只坐在一边微笑,见柳风有一种讨饶的样子,这才道:“婉芳是怕你不吃饭,所以拿话气你,你不要信她。我也是无聊得很,你就在这屋子里烤火,陪着我谈谈吧。”
杨妈见表少爷已经留下来了,用不着站在这里,就把大衣和帽子,一齐送到婉芳卧室里去。一个人自言自语地道:“饭都预备好了,又要添菜,死冷的天,只管找了事给人家做。”
落霞在屋子里拿东西,便道:“你骂哪个?听到了可是祸。不是你在堂里留客吗?背后又说别人,谁叫你作那本人情账?”
杨妈道:“我才管不着呢。我在表少爷头上做什么人情?我是话匣子,替人家说的,不说也得成啦。”
落霞有一句话正待要说,婉芳却匆匆忙忙地跑来了,接过大衣,在大衣上几个袋里都搜索了一遍,在里面袋里,掏出了一封信,半张电影院的戏票,都仔细地看了一看。看过之后,似乎没有得着什么成绩,将票子和信,依然向袋里揣进去。这才回转头来一看,杨妈走了,落霞还在这里。因问道:“刚才你们两个人说些什么?”
落霞道:“我没有说什么,杨妈说这大衣的呢子很好。”
婉芳笑道:“朱少爷的东西,哪里有坏的,他是一个最爱美的人呢。你看,他比秋天长得更清秀不是?”
落霞虽没有仔细去看表少爷的风采,但是小姐肯和自己谈话,那就是极端高兴的时候,一个月也难碰一次的,这个可以见好的机会,不可错过了,便笑道:“可不是,他穿西装最好看。”
婉芳很高兴,就复身到堂屋里来,望着柳风笑。柳风道:“表姐望着我笑什么?”
婉芳道:“你们男子爱说女人俏皮不怕冻,现在看看你们男子怎么样?不也是只要俏,冻得跳吗?”
赵太太道:“冷倒罢了,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我也要劝柳风暂时不穿西装为妙。”
柳风道:“还有一件什么事呢?”
赵太太道:“现在军警机关,捉革命党捉得很厉害,穿西装在满街跑的人,都要受一点嫌疑。”
柳风笑道:“捉革命党?不要笑死鬼了。你们这附近,就有个革命党窠子,军警机关可曾正眼看人家一看?”
赵太太瞪了眼,呀了一,声道:“什么?我们这里有革命党窠子,在什么地方?”
柳风道:“就是这胡同前面的求仁中学。”
婉芳道:“这可见得你是瞎说了。那学校只办了一两个学期,学生全是些小孩子。他们哪里会做革命党?”
柳风道:“学生不革命,教员不能革命吗?本校教员,不许借这地方做机关吗?”
婉芳道:“只要你不混进去冒那个危险就是了,管他怎样闹。”
朱柳风听了这话,却望着婉芳微笑。婉芳虽不知道他笑的用意何在,反正是对着自己笑,不由得心里一阵痒,也向柳风笑起来。可是一看母亲在这里,这笑笑得有点尴尬,连忙将笑容收了,就对他道:“你看你口袋里那条手绢,脏得那样,我给你洗一洗吧。”
柳风听说,便笑着、道了一声“劳驾”,将上下口袋里两条手绢都交给了婉芳。
婉芳笑着接了,就问还有没有,柳风笑道:“有是还有两条,放在大衣袋里,劳你的驾,在大衣袋里给我拿一拿。”
婉芳笑道:“那不好,你袋里恐怕有我不能看的东西,若是我掏了你的衣袋,很犯嫌疑的。”
柳风道:“没有关系,我袋里绝对没有什么秘密。就是有的,对于姑丈家里,也没有不能公开的。”
婉芳笑道:“你这话说得真大方,那么,我不能不一齐拿去洗了。”
说着走出堂屋来,将落霞叫到自己屋子里来,拿出四条手绢,交给她道:“用我的香胰子,使劲把这手绢擦一擦,回头我对表少爷说是我洗的,你可不许多嘴!”
落霞答应,就在屋子里洗,婉芳自在一边看守着,洗得干净,她就接过,带上堂屋,放在炉子边烤。
落霞随后跟到堂屋,只见柳风尽管向婉芳道谢。眼光可不住地向落霞射来,落霞以为他或者知道内容,也不理会有别意。婉芳道:“这又谢什么?哪回你脱下的衬衫,送一件来,我给你洗洗看,包是不亚于洗衣房里出来的东西。”
落霞在一边听见,心想,这倒好,四条手绢刚洗得,又给我下了一件衬衫的定钱了。但是这四条手绢的魔力,果然不小,柳风已是欢欢喜喜地在姑母一处吃饭。
吃饭的时候,赵太太又说:“姑丈这几天很忙,老是不能回家来吃饭。总长很听他的话,有升任司长的希望,那个时候,我一定给你姑丈说,你也在部里找个位置,不要在洋行里混那三四十块钱的小事了。”
婉芳便插嘴道:“那是的。我想一个一等科员,表弟总可以担任,父亲名下,有自己一个亲信的人办事,也可以放心些,妈,你说是不是?”
赵太太点头道:“那是当然。你父亲的事情发表了,我一定对他说,要把这事办成功的。”
柳风听她母女两人,谈来谈去,都是对自己一番好意,陪着吃过了饭,就不好意思再说要走的话,就陪了她母女俩,有一句没一句地向下谈着。
在他们自己当事人,却也无所谓,落霞在一边看见,心里便添上了一个疙瘩。我们小姐真有本事,表少爷进门之后,大衣也没有脱,本来马上就要走的,不料她三言两语,就把客留下了。不但留下了,而且还把他留下了这样久。这样看起来,男子究竟是容易软化的,就看女子的手段如何罢了。表少爷虽不是什么美少年,总比我们小姐高上一两个码子,然而他一见着了她,就加倍地迷恋,可见得女子在颜色以外,另外还有一种制男子的手腕。心里这样地想着,对于婉芳的行动,也就不住地注意。日里看见了,晚上睡到床上去,就情不自禁地,把这些男女问题,慢慢想了起来。然而转身想到自己,一个当丫头的,哪里有男女问题可谈,连身家性命,完全都是缥缈的,还去想这些闲风情做什么?因此,每每想到半夜,又把想了大半夜的心事,完全推翻了。脑筋里,从来没有留过男人的影子,有之,便是最近那个帮助一回钱的少年。对于他虽没有情字可谈,然而萍水相逢,得了他慨然地帮助我,而且连姓名也不曾说,心里未免过不去,怎能一点影子没有?可是看他那情形,钱并不是交到我手里,当然是无意于我的。我虽是个苦孩子,岂能为着人家这一点小小的帮助,就记在心里?这样说来,彼此却不应有什么痕迹在脑筋里。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钱虽少,人家的情不可忘。你看,小姐只给表少爷洗几条手绢,他就把来的原样子变过来了,那帮助更小了。她自那一天起,只管把自己的事,人家的事、不断地向下想着。为了这样想,每日清晨上街去买菜,经过那少年帮助的地方,便会突然地想起那件事,有时候发了呆,还不免站在那地方,向两边望了几望。
约莫过去了一个礼拜,又是一个大雪的清晨,落霞提了菜篮子,在雪里走着,又在发呆,猛然一抬头,那个帮助钱的少年,又夹了一个皮包,又由这胡同穿过。他头戴着一顶盆式帽子,罩到眉毛边。大衣的领子,又高高支起,将两边脸都挡住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有人站在路边。落霞见着人家觉得未便置之不理,连忙和他点了一个头。但是在她点头时,人家已走远了。这时忽然想起,冯家姥姥说了,怎么不问问人家的姓名,今天遇到了,就该问一声才好。于是跟着走下去,就要问他。无如这人只是一味低头地走,却不曾理会到身后有人问他。
落霞轻轻地叫了一声“先生”,那人不知道是叫他的,脚也不曾停上一停,只管向前走。落霞一声叫不应,一股子勇气,就挫下一半去了。在他身后,伸手招了一招,一句先生,好久不曾出口。那人到了胡同尽头,身子一转,落霞怕他要回转身来,这第二句先生,待要喊出,又忍回去了。只在她这样不住地犹豫,那人已经走远了。
这转弯的所在,是个冷胡同,这样大早上,还不曾有人走过,那人由胡同里过去,犹如在白玉板上,留下一道痕迹。落霞追上来,见那皮鞋脚印,深深地印在雪里,试着将自己的脚,补着那脚印,一个一个地踏着,不知不觉地,一步一个脚印踏了去。心里想着,我这样地踏他的脚印,不知道他也有什么感觉没有?但是,我这个思想太怪了,人在他身后叫着先生,他都不知道,留下来的脚印,尽管让人踏,那有什么关系。我正要追人家,怎么想这样不相干的事情?猛然一抬头,这一条短短的冷胡同,已经走完,现在到了大胡同里来了。
这条胡同,是由西往东的要道,来往的人不少,雪地里脚印车辙,很是杂乱,哪里追踪去?附近原有转弯的胡同,那人已转到哪里去,也不可知了。胡同转角处,有一支电线杆子,落霞将身靠了电线杆子,看到脚下堆了一堆雪,将穿的一双破皮鞋,踢着雪团,向胡同中间乱飞。心里想着事,脚不住地将雪向路中间踢。
忽然之间,也有一块雪,冰冷地直扑到脸上来。抬头一看时,只见两个上十岁的孩子,一个人拿了一块雪向自己打来。落霞停了脚,笑道:“小兄弟,你为什么拿雪打我?”
那两个孩子,各人身上,背着一个书包,分明是两个小学生。有一个小些的道:“你用雪踢我们,你倒反问我们啦。”
落霞忽然省悟过来,低头一看,见自己皮鞋口里还积了许多雪没化,便走上前,给那个孩子身上,拍了一拍雪。笑道:“小兄弟,真对不住你,我是踢着雪好玩,可就没有看到你两个人。你两个人在哪个学校读书?”
大孩子道:“我在求仁中学附小读书。你是上菜市去,你走我们学校过去,也不绕道,我们一块儿走,好不好?”
落霞刚才把这两个孩子得罪了,也极愿敷衍敷衍他们,于是将菜篮挽在手臂上,一只手牵了一个孩子,自向前走。转过两个胡同,便是求仁中学的大门口。落霞老远地看见,停了脚,不禁失声“呵呀”了一声。这一声呵呀,却大有缘故,正是:
失色易传心上事,惊呼莫是意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