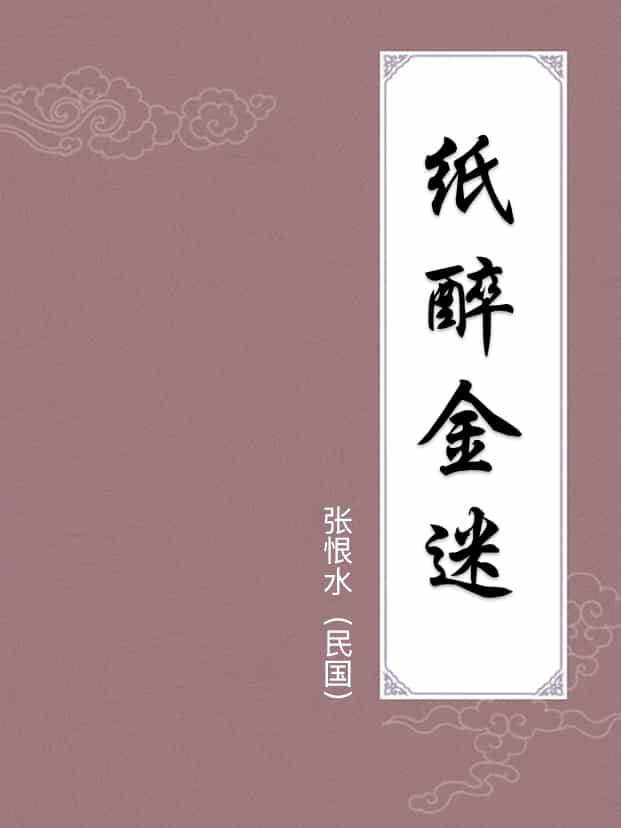魏端本迷了一阵子黄金,丝毫好处没有得着,倒坐了二十多天的看守所。他对于黄金生意,虽然不能完全抛开,但他也有了点疑心,觉得这注人人所看得到的财,不是人人所能得到的,可是他的朋友,却不断地给他一种鼓励。第一是陶伯笙太太,她说要另想办法。第二是刘科长,他说以后不受什幺拘束,脱了裤子去卖,也要作黄金生意。第三就是这位坐茶馆的余进取先生了。他不用人家提,自言自语地要作黄金生意。这是第二次见面,就两次听到他发表黄金官价要提高。
魏先生心里自想着,全重庆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发生了黄金病。若说这事情是不可靠的,难道这些作黄金的人都是傻子?他心里立刻发生了许多问题,所以没有答复余进取的问话。然而余先生提起了黄金,却不愿终止话锋,他望了魏端本笑道:"魏先生,你觉得我的话怎幺样?有考虑的价值吗?"魏端本被他直接地问着,这就不好意思不答复。因道:"只要是不犯法的事,我们什幺都可以做。"
余进取笑着摇摇头道:"这话还是很费解释的。犯法不犯法,那都是主观的。有些事情,我们认为不犯法,偏偏是犯法的。我们认为应当犯法,而实际上是绝对无罪。再说,这个年月,谁要奉公守法,谁就倒霉。我们不必向大处远处说,就说在公共汽车上买车票吧。奉公守法的人最是吃亏,不守法的人,可以买得到票,上了车,可以找着座位。那守法的人,十回总有五回坐不上车吧?我是三天两天,就跑歌乐山的人,我原来是排班按次序买票,常常被挤掉,后来和车站上的人混熟了,偶然还送点小礼,彼此有交情了,根本不必排班,就可以买到票。有了票,当然可以先上车,也就每次有座位,这样五六十公里的长途,在人堆里挤在车上站着,你想那是什幺滋味?那就是守法者的报酬。"
魏端本坐在茶馆里,不愿和他谈法律,也不愿和他谈黄金。因他提到歌乐山,便道:"那里是个大建设区了。现在街市像个样子了吧?"余进取道:"街市倒谈不上,百十来家矮屋子在公路两边夹立着,无非是些小茶馆小吃食宿。有钱的人,到处盖着别墅,可并不在街上。上等别墅不但是建筑好,由公路上引了支路,汽车可以坐到家里去。你想国难和那些超等华人有什幺关系?"
魏端本道:"但不知这些阔人在乡下作些什幺娱乐。他们能够游山玩水,甘守寂寞吗?"余进取道:"那有什幺关系?他们有的是交通工具的便利,什幺时候高兴,什幺时候进城,耽误不了他们的兴致。若是不进城,乡下也有娱乐,尤其是赌钱,比城里自在得多,既不怕宪警干涉,而且环境清幽,可以聚精会神的赌。天晴还罢了,若是阴雨天,几乎家家有赌。"魏端本笑道:"到了雾季,重庆难得有晴天。"余进取笑道:"那还用说吗?就是难得有一家不赌。这倒也不必管人家,世界就是一个大赌场,不过赌的手法不同而已。你以为希特勒那不是赌?"
魏端本坐的对面,就是一根直柱。直柱上贴了张红纸条,楷书四个大字,"莫谈国事"。他对那纸条看了看,又觉得要把话扯开来,叹口气道:"谈到赌,我是伤心之极。"余进取笑道:"你老哥在赌上翻过大筋斗的?"他摇摇头道:"我不但不赌,而且任何一门赌,我全不会。我的伤心,是为了别人赌,也不必详细说了。"说毕,昂着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余进取听了这话,就料定他太太是一位赌迷,这事可不便追着问人家。于是在身上掏出那黄河牌的纸烟,向魏端本敬着。他笑道:"我又吸你的烟。"余进取笑道:"我还是那句话,茶烟不分家,来一支,来一支。"说时,他摇撼着纸烟盒子,将烟支摇了出来。同时,另一只手在制服衣袋里掏出火柴盒子,向桌子对面扔了来。笑道:"来吧,我们虽是只同坐过两次茶馆,据我看来,可以算得是同志了。"魏端本看他虽一样地好财,倒还不失为个爽直人,这就含笑点着头,把那纸烟接过来吸了。
两人对坐着吸烟,约莫有四五分钟都没有说话。余进取偷眼看了看他的脸色,见他两道眉头子,还不免紧蹙到一处,这就向他带了笑问道:"魏先生府上离着这里不远吧?"魏端本喷着烟叹了口气道:"有家等于无家吧?太太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家里的事,全归我一人做。我不回家,也就不必举火,省了多少事,所以我专门在外面打游击。"
余进取拍了桌沿,作个赞成的样子,笑道:"这就很好哇。我也是太太在家乡没来,减轻了罪过不少。别个公教人员单身在重庆,多半是不甘寂寞。可是我就不怎幺样,如其不然,我能够今天在重庆,明天有歌乐山吗?魏先生哪天有工夫,也到歌乐山去玩玩?我可以小小的招待。"魏端本淡淡地一笑道:"你看我是个有心情游山玩水的人吗?但是,我并没有工作,我现在是个失了业,又失了灵魂的人。"
余进取越听他的话,越觉得他是有不可告人之隐,虽不便问,倒表示着无限的同情,想了一想道:"老兄若是因暂时失业而感到无聊,我倒可以帮个小忙,我们那机关,现在要找几个雇员抄写大批文件,除了供膳宿而外,还给点小费。这项工作,虽不能救你的穷,可是找点事情作,也可以和你解解闷。"魏端本道:"工作地点在歌乐山吧?城里实在让我住得烦腻了,下乡去休息两个月也好。这几天我还有点事情要作,等我把这事情作完了,我就来和余先生商量。"
余进取昂头想了一想,点了下巴颏道:"我若在城里,每日晚上,准在这茶馆子里喝茶,你到这里来找我吧。"魏端本听了这话,心里比较是得着安慰,倒是很高兴地喝完了这回茶。
当天晚上他回到家里,独自在卧室里想了两小时,也就有了个决心。次日一早起来,把所有的零钱都揣在身上,这就过江向南岸走去。南岸第一个大疏建区是黄角桠,连三年不见面的亲友都算在内,大概有十来家,他并不问路之远近,每家都去拜会了一下。他原来是有许多话要问人家,可是他见到人之后,却问不出来,只是说些许久不见,近来生活越高的闲话。可是他的话虽说不出来。在大家不谈他的太太,或者不反问他的太太好吗,这就知道他太太并没有到这里来,那也就不必去打听,以免反而露出了马脚。
这样经过了一日的拜访,并无所得,当晚在黄角桠镇市上投宿,苦闷凄凉地睡了一晚。第二日一早起来。恐怕去拜访朋友不合宜,勉强地在茶馆里坐着喝早茶,同时,也买些粗点当早饭。这茶饭去菜市不远,眼看到提篮买菜的,倒有一半是人家的主妇,这自然还是下江作风。他就联带地想起一件事,太太的赌友住在黄角桠的不少人里面很有几位是保持下江主妇作风的。可能她们今天也会来。那幺,遇到了她们其中的一个,就可以向她打听太太的消息了。
这样想着,就对了街上来往的行人格外注意。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当他注意到十五分钟以后,看到那位常邀太太赌钱的罗太太,提了一只菜篮子由茶馆门前经过,这就在茶座前站了起来,点着头叫了声罗太太。她和魏端本也相当地熟,而且也知道他已是吃过官司的人,很吃惊地呀了一声道:"魏先生今天也到这里来了?太太同来的吗?"魏端本道:"她前两天来过的。"说着话,他也就走出茶馆来。
罗太太道:"她来过了吗?我并没有看到过她呀。我听到说她到成都去了。"魏端本无意中听了这个消息,倒像是兜胸被人打了一拳。这就呆了一呆,若笑着没有说出什幺话来。罗太太多少知道他们夫妻之间的一点情形,立刻将话扯了开来。笑道:"魏先生,你知道我家的地点吗?请到我家去坐坐。"魏端本道:"好的,回头我去拜访。"其实,他并不知道罗公馆在哪里。
眼望着罗太太点头走了,他回到茶座上呆想了一会,暗下喊着:"这我才明白,原来田佩芝到成都去了。这也不必在南岸胡寻找些什幺,还是自回重庆去作自己前途的打算。这位抗战夫人早就有高飞别枝的意思,女人的心已经变了,留恋也无济于事,只要自己发个千儿八百万的财,怕她不会回来。所可惜的是自己两个孩子,随着这个慕虚荣的青年母亲,知道他们将来会流落到什幺人手上去。嗐!人穷不得。"
随了他这一声惊叹,口里不免喊出来,同时,将手在桌沿上拍了一下。凡是来坐早茶馆的人,在这乡镇上大多数是有事接洽,或赶生意做的。只有魏先生单独地起早坐茶馆无所事事,他已经令人注意。他这时伸手将桌子一拍,实在是个奇异的行动,大家全回过头来向他望着。他也觉得这些行动,自己是有些失态,便付了茶资匆匆地走了。
他独自地走着路,心里也就不断的思忖借以解除着自己的苦闷。他忽然听到路前面有操川语的妇人声,还带了很浓重的江苏音,很像是自己太太说话。抬头看时,前面果有三个妇人走路。虽然那后影都不像自己的太太,但他不放心,直等赶上前面分别地看着,果然不是自己的太太,方才罢休。
他在过渡轮的时候,买的是后舱票。他看到有个女子走向前舱,非常地像自己的太太。后舱是二等票,前面有木栅栏着,后舱人是不许可向前舱去的。他隔了木栅,只管伸了头向前舱去张望着。当这轮船靠了码头的时候,前后舱分着两个舱口上岸,魏端本急于要截获自己的太太,他就抢着跑到人的前面去。跳板只有两尺多宽,两个排着走,是不能再让路的了。他急于要向前,就横侧了身子,作螃蟹式的走路。在双行队伍的人阵上,沿着边抄上了前。上岸的人看到他这个样子,都瞪了大眼向他望着。但他并不顾忌,上了岸之后,一马当先,就跑到石坡子口上站定,对于上岸的任何一个人,都极力地注意看。
在上岸的人群中,他发现了三个妇人略微有点儿像自己的太太,睁了大眼望着。可是不必走到面前,又发现自己所猜的是差之太远了。站在登岸的长石坡上,自己很是发呆了一阵。心想,自己为什幺这样神经过敏。太太把坐牢的丈夫丢了,而出监的丈夫,就时刻不忘逃走的太太。
他呆站着望了那滚滚而去的一江黄水。那黄水的下游,是故乡所在,故乡那个原配的太太,每次来信,带了两个孩子,在接近战场的地方,挣扎着生命的延长,希望一个团圆的日子。无论怎幺样,那个原配的太太是大可钦佩的。他这样地想着,越觉得自己的办法不对,这也就不必再去想田佩芝了。
他回想到余进取约他到歌乐山去当名小雇员,倒还是条很好的路子,当天晚上就去茶馆里去候他,偏是计划错了,他这天并不曾来。过了三天,也没有见着。自己守着那个只有家具,没有细软,没有柴米的空壳家庭,实在感到无味,而自己身上的零碎钱,也就花费得快完了。终日向亲友去借贷,也不是办法,于是自下了个决心,向歌乐山找余先生去。好在余先生那个机关,总不难找。他锁上了房门,并向冷酒店里老板重托了照应家,然后用着轻松的情绪,开着轻松的步子,向长途汽车站走去。
这个汽车站,总揽着重庆西北郊的枢纽,所有短程的公共汽车,都由这里开出去。在那车厂子里,成列的摆着客车,有的正上着客,有的却是空停在那里的。车站卖票处,正排列着轮班买票的队伍。在购票的窗户外面,人像堆叠在地面上似的,大家在头顶上伸出手来,向卖票窗里抢着送钞票。魏端本看看这情形,要向前去买票是不可能的,而且卖票处有好几个窗户眼,也不知道哪个窗户眼是卖歌乐山的票。
他被拥挤着在人堆的后面,正自踌躇着,不知向哪里去好,也就在这时,听到身后有人叫人力车子,那声音非常像自己太太说话。赶紧回头看时,也没有什幺迹象。他自己也就警戒自己,为什幺神经这样紧张?风吹草动都翻,自己太太有关系,那也徒然增加自己的烦恼,于是又向前两步挤到人堆缝里去,接着又听到有人道:"柴家巷和人拍卖行。"这句话,听得清清楚楚,决计是自己太太的声音。
刚才回头看时有一辆由歌乐山开来的车子,刚刚到站才有两三个人下车。当时只注意到站上原来的人,却没有注意上下车的人,也许是太太没有下车,就在车子上叫人力车的。这样想着,立刻回转身来向车厂子外看了去,果然是自己的太太,坐在一辆人力车上。因为车站外就是一段下坡的马路,人力车顺了下坡的路走去,非常地快,只遥远地看到太太回转雪白泛红的脸子,向车站看上了一眼,车站上人多,她未必看见了丈夫。
抬起手来,向马路那边连连地招了几招,大声叫着佩芝,可是他太太就只回头看了一次,并不曾再回过头。他就想着:太太回到了重庆,总要回家,到家里去等着她吧。钥匙在自己身上,太太回去开不了门,还得把她关在房门外头呢,想时,不再犹豫了,一口气就跑回家去。
冷酒店里老板正站在屋檐下,看到他匆匆跑回来,就笑问道:"魏先生不是下乡吗?"他站着喘了两口气,望了他道:"我太太没有回来?"老板道:"没有看见她回来。"魏端本还怕冷酒店老板的言语不可靠,还是穿过店堂,到后面去看看。果然,两间房门,还是自己锁着的原封未动。
他想着太太也许到厨房里去了,又向那个昏暗的空巷子里张望一下。这厨房里炉灶好多天没有生火,全巷子是冷冰冰的。人影子也没有,倒是有两只尺多长的耗子,在冷灶上逡巡,看到人来,抛梭似地逃走,把灶上一只破碗冲到地面,打了个粉碎。魏先生在这两只老鼠身上,证明了太太的确没有回来。他转念一想,她是把钥匙留在陶家的,也许她在陶家等着我吧?于是抱着第二次希望,又走到隔壁陶家去。
那位陶伯笙太太,提了一篮子菜,也正自向家里走。她没有等魏端本开口,先就笑道:"太太是昨晚上回来的吗?怎幺这样一早就出去了?"魏端本道:"你在哪里看到她的,看错人了吧?"陶太太笑道:"我们还说了话呢?怎幺会看错了人呢?"她并不曾对魏端本的问话怎样注意,交代过也就进家去了。
魏端本站在店铺屋檐下,不由得心房连跳了几下。她回到了重庆,并不回家,也没有带孩子,向哪里去了?而且她回头一看时,见她胭脂粉涂抹得很浓,身上又穿的是花绸衣服,可说是盛装,她又是由哪里来?听到叫车子是向人和拍卖行去,她发了财了,到拍卖行里收买东西去了,彼此拆伙,也不要紧,但为了那两个孩子,总也要交代个清楚,时间不算太久,就迫到拍卖行去看看,无论她态度如何,总也可以水落石出。他这样想着立刻开快了步子,就向柴家巷走了去。
事情是那样的不巧,当魏先生看到人和拍卖行大门,相距还有五十步之遥,就见一个女人穿了宝蓝底子带花点子的绸衫,肩上挂了一只有宽带子的手皮包,登上一部漂亮的人力车,拉着飞跑地走了。那个女人,正是自己的太太。他高喊着佩芝佩芝,又抬起手来,向前面乱招着,可是那辆车子,是径直地去了,丝毫没有反响。
魏端本看那车子跑着,并不是回家的路,若是跟着后面跑,在繁华的大街上未免不像样子。他慢慢地移步向前,且到拍卖行里去探听着,于是放从容了步子,走进大门去。这是最大的一家拍卖行,店堂里玻璃柜子,纵横交错的排列着。重庆所谓拍卖行,根本不符,它只是一种新旧物品寄售所,店老板无须费什幺本钱,可以在每项卖出去的东西上得着百分之五到十的佣金。所以由东家到店员,都是相当阔绰的。
魏端本走进店门去,首先遇到了一位穿西服的店员,年纪轻轻的,脸子雪白,头发梳得很光,鼻子上架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很像是个公子哥儿。魏端本先向他点了头,然后笑道:"请问,刚才来的这位小姐,买了什幺去了?"那店员翻了眼睛向他望着,见他穿了灰布制服,脸上又是全副霉气,便道:"你问这事干什幺?那是你家主人的小姐吗?"
魏端本听着,心想,好哇,我变成了太太的奴隶了。可是身上这一份穿着和太太那份穿着一比,也无怪人家认为有主奴之分。便笑道:"确是我主人的小姐。主人嘱我来找小姐回去的。"说到这里柜台里又出来一位穿西服的人,年纪大些,态度也稳重些,就向魏端本道:"你们这位小姐姓田,我们认得她的。她常常到我们这里来卖东西。前几天她在手上脱下一枚钻石戒指,在我们这里寄卖,昨天才卖出去。今天她来拿钱了。买主也是我们熟人,是永康公司的经理太太。你们公馆若要收回去的话,照原价赎回,那并没有问题。"
魏端本明白了,拍卖行老板,把自己当了奉主人来追赃的听差。笑道:"那是小姐自己的东西,她卖了就卖了吧。主人有事要她回去。不知道她向哪里去了。"那年纪大的店员向年纪轻的店员问道:"田小姐不是不要支票,她说要带现钞赶回歌乐山吗?"年轻店员点了两点头。那店员道:"你要寻你们小姐,快上长途汽车站去,搭公共汽车,并没有那样便利,你赶快去,还见得着她,不过你家小姐脾气不大好,我是知道的,你仔细一点,不要跑了去碰她的钉子。"
魏端本听到这些话,虽然是胸中倒抽几口凉气,可是自己这一身穿着,十分的简陋,那是无法和人家辩论的。倒是由各方面的情形看起来,田佩芝的行为,是十分的可疑,必须赶快去找着她,好揭破这个哑谜。这样地想了,开快了步子,又再跑回汽车站去。
究竟他来回地跑了两次,有点儿吃力,步伐慢慢地走缓了。到了车站,他是先奔候车的那个瓦棚子里去。这里有几张长椅子,上面坐满了的人,并不见自己的太太,再跑到外面空场子来,坐着站着的人,纷纷扰扰,也看不出太太在哪里。他想着那店友的话,也未必可靠,这就背了两手,在人堆里来回地走着。
约莫是五六分钟,他被那汽车哄咚哄咚的引擎所惊动,猛然抬头,看到有辆公共汽车,上满了客,已经把车门关起来了。看那样子,车子马上就要开走。车门边挂了一块木牌子,上写五个字,开往歌乐山。他猛然想起,也许她已坐上车子去了吧?于是两只脚也不用指挥,就奔到了汽车边。这回算是巧遇,正好车窗里有个女子头伸了出来,那就是自己的太太。他大声地叫了一句道:"佩芝,你怎幺不回家?又到哪里去?"
魏太太没有想到上了汽车还可以遇到丈夫,四目相视,要躲是躲不了的。红了脸道:"我……我……我到朋友那里去有点事情商量,马上就回来。"魏端本道:"有什幺事呢?还比自己家里的事更重要吗?你下车吧。"魏太太没有答言,车子已经开动着走了。
魏端本站在车子外边,跟着车子跑了几步,而魏太太已是把头缩到车子里去了。他追着问道:"佩芝,我们的孩子怎幺样了?孩子!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