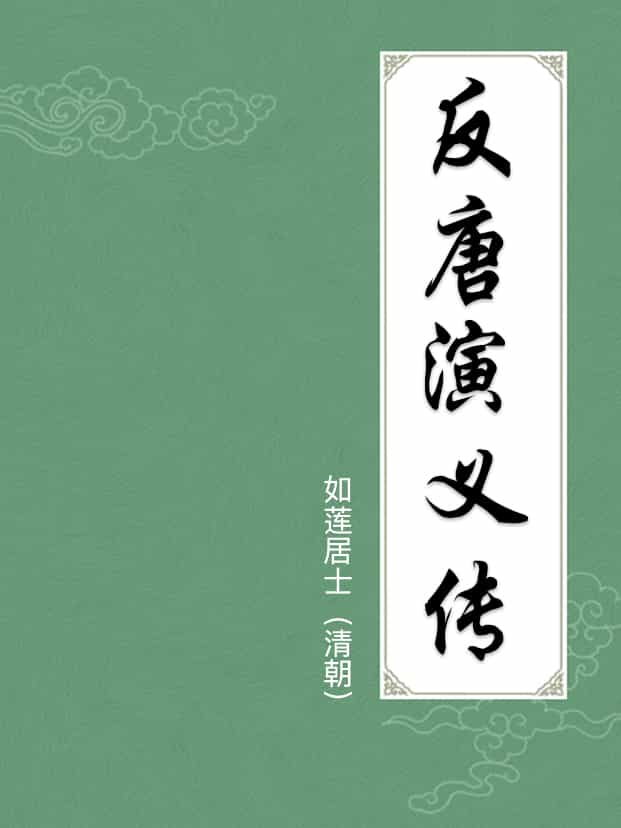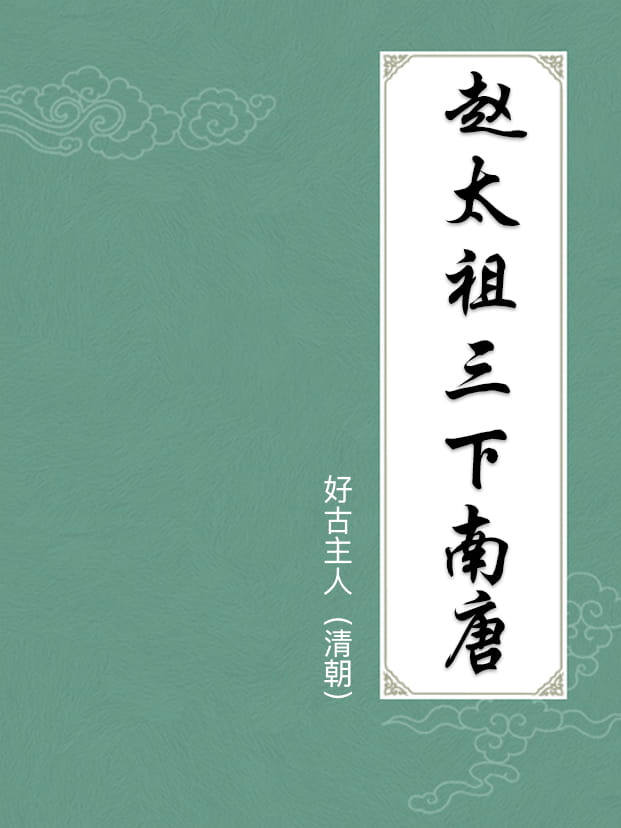第一部初恋有一年的夏天,夕阳红得像鲜血般的在地平线上流淌。何本从一个小镇的市梢出来,急忙忙地向那不远的村子走去。他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在这暑假中天天出外顽耍,好像野马出了笼子似的;他的父母也漫不管他,任他所作所为的。他走近这村子了,于是沿着田陌,绕到村子的后面。这里一片草原上,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农家女儿,看守住一头绵羊,口里在唱歌;何本在她的背后轻轻的走上,她没有觉察,何本将她的辫儿拉了一拉。
“是谁?”她回转头来,“你吓死我了。口哀,口哀,我要告诉妈妈的。”她举起右手,掩住眼儿装做哭的样子。
“毛大,毛大,你别要哭!你哭我不和你要好了。”何本说了,心里有点惊慌;像石像似的动也不动,凝视看她。过了一歇,她放下了手,嘻嘻地笑了;他才放心,便一同坐在草地上说话。毛大对他说:“何本,你总是骗我的!你说有个痧药瓶送给我,你带来了没有?”
“我带来了。”
“放在哪儿呢?”
“在我的袋里。”
“那么你送给我呀!”
“不,在这儿不送你,到一块地方去送你。”
“那一块地方呢?”
“那边竹园里。”
“那么教我的羊怎样呢?”
“我先去等在竹园里。你把你的羊牵了回去,马上就来。”
毛大动身,把她的羊牵走了;何本跟她进一个村子的后门。
天光渐渐地暗了,在几间破屋的后面,一处丛竹插满的林中,飒飒地摇出凉快的晚风,何本一个人,偷耽耽地穿过林子进去,找到一处乱柴堆;他就躺下,二足靠在二株竹上,口里咻……咻地叫着。一忽儿毛大来了,走近何本,他就拉着她说:“你也坐下罢!”
她靠近何本的左边坐下,和他睡的姿态侧对着,她微笑地问他:“你允许给我的那个痧药瓶呢?”
“因为你不和我要好,我不送给你了!”
“我和你要好的。”
“那么你和我一同睡在这里。”
——她便并着他的肩儿睡下,于是何本从袋里摸出一个方的小瓶授给她;她把这小瓶两手捧到眼前,借了日光已尽的余辉,注视了一下;好像得了什么奇珍似的抚弄着。这时何本抱住她许久许久了。
“毛大,你为甚还穿的开裆裤呢?”
“呀,呀,你别要摸我呢!人家怕痒的。”
“你痒不关我呢。”
“呀,呀,我要喊了。”
“好了,好了。”
“你还不放手吗?”
天光更加黑了,远远地有种声音在喊着:
“阿毛大!阿毛大!”他们俩吓得一声也不做,静静地听着;毛大推了何本的肩儿说:“妈妈在喊我了,我要回去呢。”
“我也要回去了,门口有狗的,你送我到门外罢。”
隔了两三天,何本在街头又遇见毛大了。她提了一个筐子回去。何本跟在她的后面,渐渐离去市街。这是一个下午,太阳热烈地晒在他们俩的身上,汗流满面;他把右手的衣袖,一面揩汗,一面问她说:“你们那边的田间,有白娘瓜吗?”
“有的。”
“那也有像买来的甜吗?”
“比买来的还甜呢。”
“我们同去采罢?”
“不,要被人家骂的。”
“不要被人家知道就是了。”
毛大走近自己的村子了,就不作声响;何本有点着急,便低低地问她:“你不和我一同去吗?”
“我要把筐子放到家里才得去呢。”
“那么我等在这儿。”
“是的。”
何本找到一处有树荫的,靠在篱笆上发呆,他看她从侧门里出来,站住了转了一个身子,像在找寻他。
“在这里!”何本说了,毛大便走近他;指着向西北的一条田陌上走去,不多时光,他们俩站住了,毛大忸着他说:“这里王家伯伯的瓜田,定会有好东西呢!”说了指着不远的瓜棚给他看。
“去采罢!”他说了拉着毛大跨到田间,毛大还瑟缩地向四面望了一望,才一同走进;到了瓜棚的旁边,便一同蹲下去采拾。
他们俩的衣砊里,兜满了白娘瓜,露出惊慌的样子,踏上了一条小路,向着不远的别一个村子走去;踉跄跄地背后像有人追袭他们,他们也不敢回视。
村子的近旁,有许多成荫的大树;把银矢似的阳光遮盖住了。凉风吹到左面的一片河沟里,清清的水儿在微笑。他们就在这河边歇息,把白娘瓜堆在草地上;何本选拣了二个,走下河滩洗净了一下,用一双手捧住,大嚼了一阵。毛大也照他这们办了。一忽儿,八九个白娘瓜都到他们俩的肚子里了。
何本脱去了一双鞋儿,赤着足,坐在河滩上;二足升到水里,搅个不住。毛大站在他的旁边呆望着。
“喂!毛大,我们洗一个冷水浴罢?”
“那是不行的,要沉死在河里的呢。”
“没有这种事的,你看这里很浅,我一双足伸下去,就有泥浆泛上来。”
“你不怕落水鬼吗?”
“这里没有的,有了落水鬼它会变一双红鞋,或是一朵鲜花浮在河面的。你看这里没有这种东西。”他说完了,就把他的上衣下衣一齐解掉,跨下河去;他托出一双小小的腕臂,像翅膀似的泳上去,于是河水浸到他的颈项;他得意地对她说:“毛大你也来吗?”
“不,不!”她站在河滩上,发出一种惊奇的神情观望他;又像替他耽忧时时发着寒颤。过了一歇,他泳回到河滩来“喔”的一声,他一滑足半身横在泥土上,半身浸在水里。毛大忙的用了全力拉他的手,才上到滩来:一个赤裸裸的身子,背上和臂儿上腰里,都涂着泥土了;他不由得呱呱地哭起来了。
“教你不要下河去,你偏不听!”毛大带着怨声羞涩地说了,便解去自己污秽的一袭上衣,把他的泥涂处揩试干净;又柔顺地将何本的下衣,交给他穿上;而且替他穿上那件上衣。于是她赤露了上身,挟着自己污秽的上衣,催促他回去。
这时阳光渐变得很微弱,和他们俩同样显出扫兴的神气。
第二天早上,何本牵了他的母亲的衣角,站在大门前,候那副糖糕担。那些上市的人们,过了不少,却瞧不见一个卖糖糕的。有一个中年的农人,提了菜筐,慢慢儿走近他们了;他先和何本的母亲招呼了一声,然后从筐中拿出二块糖糕,含笑地送给何本。
“小弟弟,昨天你在洗冷水浴。这是动不得的,下次别要这么做!”他把糖糕送给后,劝告他这样说。
“真的吗,在哪儿?”他的母亲发出惊问。
“我的阿毛大的衣服,弄得一身污泥;但是,师母他不懂事的,不要去责备他。”他说了便辞别他们回去,这人就是毛大的父亲李正常,他历年替何本家里做工时,总带着毛大到何本家去吃饭的;他们二家是很熟很熟的宾主了。
自从这一次,何本被李正常揭破了罪状后,他的母亲便天天看管他,不许他一个人出门,他像犯了什么大的罪过,和住在监禁里一样。
第二部不可思议的魔术何本从小学校卒业后,考进了中学;他离去家乡,寄宿到上海快有五年了。今年他长到十六岁了,混在这个烦热的虚荣之市里,也不觉得甚么有异。有时他随着同学们在几个著名的女学校前,徘徊不已;但他的心中还忘不掉毛大。
他想到近二三年来,暑假回去,偶然看见毛大,也一年长大一年了;就是在中途遇见,二人都含着羞涩的神气,过路人似的不招呼了;李正常虽是还来做工,可是不带她来吃饭了。
他又忘不掉的,遇见她时,她总不敢正视;而一双水汪汪的眼儿,流转得非常神秘,使他的心情也流荡不息。
她的一双水汪汪的眼儿,套上了一副椭圆形的面架;如果加以美丽的装饰,穿了贵重的衣服,也是一个繁华场中的尤物,何致委在蓬蒿之间呢。
春天张着她的催眠的罗网,处处使人疲惫,无力;他对于学校里的功课,漠不关心,整天的发些无谓的空想。
有一天,他和几位同学,在四马路的一带书店里闲逛;他们买了许多新出的杂志小说,何本也无意之间买了一册《秘术一百种》。这一天是星期日,他回到学校的寄宿舍里,坐在床上把那本《秘术一百种》翻看。
他突然注意在目录上的一条:“梦中与所思人相会”。
于是他认了页数,平心静气地躺下去,随后翻到这一页上,这里说:
“用四方的白纸一方,将天竹枝的根,和自己剪下的头发,包拢来藏在枕边;不使别人知道。夜间就会与所思人在梦中相会。”
他看了这一段话,便反覆沉思;他以为这个方法并不烦难的,心中跃跃欲试了。于是他乘着他们晚饭的时候,一个人到校长室前面的花坛上,掘了些天竹枝的根;忙的归到寄宿舍,照书上的一个方法弄妥了。他虽是牺牲了一顿晚饭,觉得毫没有损失的样子。
他心里怀着一种欢喜,又躁急,又不安,弄得坐也不好,立也不好;甚至像手足无所措的样子。睡眠的钟声响了,他才安闲,好像解去了一件重大的心事;他忙的摊了被褥,垂下帐子;他在帐中还注意同室的人觊觎他没有?像是帐中藏了一件无价的奇珍。灯光熄了以后,他稍稍清净一点;轻轻的在枕边探索一下,那个纸包没有逃去。于是他的头搁在枕上,动也不动,心里一刻不停的默念着:“今夜梦中与毛大相会!”念了又念,念了又念,差不多快念过五更了。
这时他觉得有些疲倦了,便朦胧地睡去。忽然他好像在故乡的一处庙宇的广场上玩,看见毛大在前面走过,他忙的喊她:“毛大,毛大!”
“哦,你几时回来的?”她回转身来走近他。
“前天回来的。”
他觉得毛大一点没有变更,还是五六年前的样子;于是他拉了她的手,进到一所高大的殿堂里;又走到里天井,进一间藏柴槁的小屋子;他们俩坐在柴槁上,发现了许多吃的东西:什么饼干呀,蜜糕呀,什么水梨呀,苹果呀,堆了一大堆。他们俩欢喜极了,不管是谁的东西,拿来任意大嚼。
这时他的一双眼儿,红赤赤的痴望着毛大;显露出一种性的饥荒,生理上的机能也突然奋发了。他一看对面的毛大,眉儿眼儿什么多美;她像会到何本的意思,也露出种种的媚态,于是他像奔牛似的扑上去。……磟的一声,把他惊醒了,他依旧在寄宿舍里;日光浸到窗上了,他忙的换了衣服起身。
他到洗漱处去,几个同寝室的人,正在谈论他昨夜怎样梦呓,怎样呼喊。他像负了重病似的,没有气力和他们争论;心里只是藏着一个秘密,始终惊异那本秘术书上的神奇。
以后他的早熟的心情中,生起了一种无名的烦闷,把他的胸坎圆满地占据住了;他昏昏然醉酒般的不能自主,他的纤细的神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第三部死与热病何本在上海的一个中学里毕业后,他又考取了北京的N大学。在北京混过了五年,好像昨天的事。今年在N大学毕业了,他的年纪也长到二十一岁了。自从他到北京去后,这回暑假毕业回来,算是第一次归到故乡。
天气烦热,他也不想往外,只是在家中看书消遣;就是亲戚朋友们来问候他,他也觉得乏味极了。他虽是二十一岁的年青人,但是几年来经过都会的豪华,一切希望尽付乌有了;回想起来只有些悲欢离合的薄影,现在的情怀,较中年人都平淡,几乎成枯寂的老僧了。他觉得在家乡住在与市声隔绝的老屋里,非常称意呢!
一天下午,他挟了一册外国文的杂志:在走廊里赤着足,靠在藤椅上休息。历年替他家里做工的那位李正常来了,走近他招呼了一声,手里提着什么东西似的,往内室去;一忽儿他回出来,欣欣然问何本说:“小先生,你才回来的吗?”
“是的。”
“多年不见了,你长得这样大,我听说你要做官了?”
“那有这样话。”
“你别瞒我,你小时候我常常抱你买糕饼给你吃的;现今你做了官,你要荐我做一个管门人呢。”
“像我这不懂事的人,那会做官呢!”
“不,你看那方言馆出身的人,都做官了;你别客气。”
“小先生,我听说你的妈妈选了H乡桂翰林的小姐,给你订婚了。”
“不,不,……不!”
他一句话答不出来,他的胸中千情万绪,乱丝般的缠扰着;李正常看他没有神思,便辞别退下。他稍稍镇静了一点,他想到李正常的额上,刻着一条条深刻的皱纹,露出他的劳苦一年年增进的特征;不由得起了深的同情。他的话多少带些应酬味,然而对于何本的热爱,期望,一种纯朴而深厚的高谊,使何本感激无地了。
这几天来,何本每天听得像李正常那样的话;尤其今天他起了一种特异的感情,自言自语的说:“忠厚的长者们哟!像我这样一件废弃的东西,不配你们的厚爱,也不配你们的期望。啊,啊,我恨不得把十年来的无聊,放浪,尽情的告诉了你们,你们定会拍案大呼,把我骂得鲜血淋漓。然而我那有勇气来告诉你们,惊动你们纯朴的精神;使你们为我抱着失望,愤恨,不平,怜惜。我也没有这个忍心,你们也不要挂记我这无益于你们,也无益于世的破东西哟。”
他说完了,又要到订婚的话,立刻联想起,那位李正常的女儿毛大好像站在他的前面,一双水汪汪的眼儿,对他凝望着;他昏醉得不成样子,像是浑身汨没在她的一双水汪汪的眼儿里了。拍的一声。他手里拿的一本外国杂志落下了,惊醒了他的一刹那间的迷幻;他觉得仍是一个人坐在藤椅上。
这时他的母亲移了一个凳子来,坐在他近旁;他装做没有事的样子接待她。她是一个中年的仁慈妇人,对他望了一望,心里觉得异常欢喜;便问他说:
“本本,你身体舒服吗?”
“我觉得回来了很好。”
“一个人第一件幸福,是没有毛病。”
“是呀!”
“你回来的半个月以前,这里时疫毛病流行得很厉害。”
“没有人家遭难吗?”
“有的,邻近的王伯章也死了,张师父也死了;西村的杨阿二也死了;就是刚才来的李正常的女儿也死了。”
“那个女儿也死了吗?”他听到这里,非常紧张,像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
“是的,也是死在时疫里的。”她的母亲说完了,就有仆人来喊他们去晚饭,把这个谈话折断了。
他一个人,睡在一间空旷的寝室里,明月照在对床的纸窗上,银灰色的,惨白色的,好像幻了一双水汪汪的眼儿对他望。窗外的夏虫声,唧唧地,哜哜地,好像幽魂的哭泣。他想到死去了的毛大,不由得悲感并来。
“唉,你这活泼泼的处女,暝目长眠了!你这无罪的处女,竟会瞑目长眠了!啊,啊,举世都是行尸走肉们,扮出了男女老少,热闹地演那怪丑的喜剧。天啊!天啊!你还留着我做旁观者吗?可是我看厌了,听厌了;你快来引导我到所爱的人前。……”他默默地自语了一回,左右转侧,通夜没有睡觉。
第二天清早,他穿了衣服,一直踱到门外,沿着市梢西往;走了二百步的光景,西村——毛大的村子涌在他的眼前了。他十年前时时和她在这条路上来往的;道路没有改变,他的伴侣已成陈死人了。他站在路旁神经迟钝,忘记到这儿来干什么事了。离他不远有两三处新封土的坟墓,送到他的眼前;他才想到来找一个毛大的坟墓。他想:这两三处的新坟,不知道那一个是毛大的?满贮着一腔眼泪,洒到何处?他忍不住了,一滴滴的落下来,顺了风儿,低低的说道:“像你那样的人会死吗?真是天道逆行,无所忌惮,怎不令人切齿痛恨呢!”你死了,我才觉得有许多对不起你的地方;我在这里对你忏悔罢。我自从离去故乡,起初几年我还把你的影儿藏在心坎里;刻刻不忘;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渐渐的淡下去了。我在一个大都会里,一时被妖艳的妇人戏弄玩狎的时候,你定在空房哭泣啊,我还有怎样的面目来见你呢?
“如果我不离去故乡,不进学校,我想我现在也是一个少年农人;我娶了你,何等美满,何等甜蜜,你也不会死,我也不会漂流到这样田地。啊,学问有何用?徒然扩大了人的空虚的奢望,把一切美好机缘投在枯井里了。
“求你饶恕我罢!求你饶恕我罢!……”他说到这里,有几个上市的人,在这路上经过。他止住了声息,欠伸了一回,装做深呼吸的样子;村子的矮屋浓荫,背后衬托着一片无涯的田野,一丝丝的田陌网罗般的呈在他的眼前;他喝了一服自然的清凉剂,似乎清醒了一大半。远处一个年青的女人,慢慢地走来;穿的素色的上衣,乌黑的裙子;她一双圆活的眼儿,上下莫定,时时注望他;走近了他,便低倒头看在她自己一双高高的乳房上,害羞地绕道过去,进这村子的前门。他呆呆的目送她进去,至于不见;他发着寒颤又是自言自语的说:“依旧一双水汪汪的眼儿!……她是毛大;……是了,她没有死。……她明明死了,除非……除非我见鬼了。……不,不,白天里那会……”他断断续续地说了一番,交着二腕抱住什么东西似的,一双脚也笨重不灵;他心里起了一层无名的恐怖,鼓出残余的勇气,走回家去。
他的母亲正是候在门外,教他去吃早饭;看见他这副神情,有点奇异,便问他:“老清早你到什么地方去的?”
“我去散步的。”
“你觉得冷吗?”
“不,不,我今天见鬼了!那个李正常的毛大,在我面前走过。”
“那里是鬼呢?”
“我昨天说她死了。”
“不,毛大没有死,毛大的妹子死了。”
“她没有妹子的罢?”
“你出门了多年,当然不知道她有妹子的;毛大今年春天出嫁的,她的妹子也有六岁了,恐怕你完全不知道呢。”
“是吗,是吗?”
你听得这番话,心里放宽了一些;但是神经麻木,只是发出不自然的干笑声。一忽儿全身的血液,都聚在他的脑髓里,一步紧一步的震荡着;他的眼前暗了。
当夜他发了热病,直挺挺的躺在床上;闭了眼儿,任那急促的呼吸,安排他的腹部运动。他的深红的嘴唇,半开半闭地时时颤动着。在这模模糊糊的灯光里,他只见眼前,周围,充满了无数的小的大的水汪汪的眼儿;那些水汪汪的眼儿,又像变变地飞来飞去,无孔不入。他在静候着这一场妖异的究竟。
十二年八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