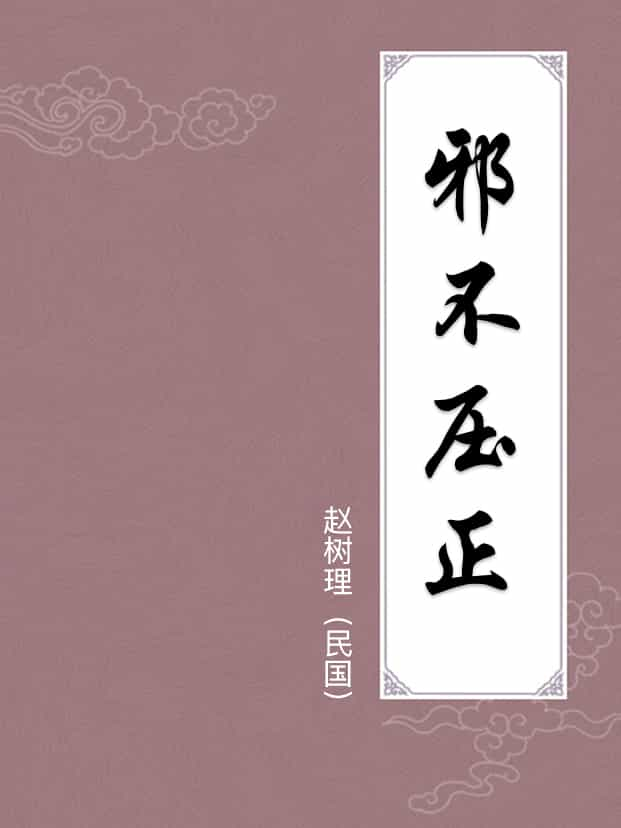聚财本来从刘家强要娶软英那一年就气下了病,三天两天不断肚疼,被斗以后这年把工夫,因为又生了点气,伙食也不好,犯的次数更多一点。到了这年(一九四七)十一月,政府公布了土地法,村里来了工作团,他摸不着底,只说是又要斗争他,就又加了病——除肚疼以外,常半夜半夜睡不着觉,十来天就没有起床,赶到划过阶级,把他划成中农,整党时候干部们又明明白白说是斗错了他,他的病又一天一天好起来。赶到腊月实行抽补时候又赔补了他十亩好地,他就又好得和平常差不多了。
他还有一宗不了的心事,就是软英的婚姻问题。从工作团才来时候,小宝就常来找软英,说非把这件事弄个明白不行。他哩,还是他那老思想,不想太得罪人。他想:斗错了咱,人家认了错,赔补了地,虽说没有补够自己原有的数目,却也够自己种了,何必再去多事?小旦小昌那些人都不是好惹的,这会就算能说倒他们,以后他们要报复起来仍是麻烦。他常用这些话劝软英,软英不听他的。有一次,他翻来覆去跟软英讲了半夜这个道理,软英说:“谁不怕得罪我,我就不怕得罪谁!我看在斗刘家那时候得罪小旦一回,也许后来少些麻烦!”
腊月二十四这天,早饭以后,村支部打发人来找软英,说有个事非她去证不明白。一说有事,聚财和软英两个人都知道是什么事,不过软英是早就想去弄个明白,聚财是只怕她去得罪人,因此当软英去了以后,聚财不放心,随后也溜着去看风色。
自从整党以来,村支部就在上年没收刘家那座前院里东房开会。这座院子,南房里住的是工作团,东房里是支部开整党会的地方,西房是农会办公的地方。到了叫软英这一天,整党抽补都快到结束时候,西房里是农会委员会开会计划调剂房子,东房里是支部开会研究党员与群众几个不一致的意见。
聚财一不是农会委员,二不是党员,三则支部里、农会里也没有人叫过他,因此他不到前院来,只到后院找安发,准备叫安发替他去打听打听。他一进门,安发见他连棍子也不拄了,就向他说:“伙计!这会可算把你那讨吃棍丢了?”聚财笑着说:“只要不把咱算成‘封建’,咱就没有病了!”安发说:“还要把你算成‘封建’的话,我阁外那五亩好地轮得上你种?”聚财说:“你也是个农会委员啦,斗了咱十五亩地只补了十亩,你也不给咱争一争?既然说是错斗了我,为什么不把我原来的地退回来?”安发说:“算了算了!提起补地这事情,你还不知道大家作的啥难!工作团和农代会、农会委员会整整研究了十几天,才研究出这个办法来!你想:斗地主的地,有好多是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多占了,错斗中农的地又都是贫雇农分了。如今把干部积极分子多占的退出来,补给中农和安置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全村连抽带补只动五十多户;要是叫贫雇农把分了中农的地退出来,再来分干部积极分子退出来的多占土地,就得动一百五十多户。一共二百来家人一个村子,要动一百五十多户,不是要弄个全村大乱吗?我觉着这回做得还算不错,只是大家的土地转了个圈子。像去年斗你那十五亩地,还分给了我三亩,今年小昌退出阁外边我那五亩又补了你。那地是刘锡元从我手讹诈去的,斗罢刘锡元归了小昌,小昌退出来又补了你,你的可是分给了我;这不是转了个大圈子吗?”聚财说:“小昌他要不多占,把你阁外那地早早分给你,这个圈子就可以不转,也省得叫我当这一年‘封建’?”安发说:“这个他们都已经检讨过了。就是因为他们多占了,窟窿多没有补丁,才去中农身上打主意,连累得你也当了一年‘封建’。这次比哪次也公道:除了没动过的中农以外,每口人按亩数该着二亩七,按产量该着五石一,多十分之一不抽,少十分之一不补;太好太坏的也换了一换,差不多的也就算了。你不是嫌补的你亩数少吗?照原产量,给你换二十亩也行,只要你不嫌坏!”聚财说:“我是跟你说笑!这回补我那个觉着很满意!咱又不是想当地主啦,不论吃亏便宜,能过日子就好!——伙计!你不是委员吗?你怎么不去开会?”安发说:“今天讨论调剂房子,去村里登记农会房子的人还没有回来。”聚财说:“人家支部里打发人把软英叫去了。这孩子,我怕她说话不知轻重,再得罪了人家谁。咱才没有了事,不要再找出事来!你要去前院西房里开会,给我留心听一听她说些什么妨碍话没有!”安发说:“不用管她吧!我看人家孩子们都比咱们强。咱们一辈子光怕得罪人,也光好出些事,因为咱越怕得罪人,人家就越不怕得罪咱!”聚财觉着他这话也有道理。
正说着,老拐进来了。他和聚财打过招呼,就坐下跟安发说:“你是咱贫农组组长,这次调剂房子,可得替我提个意见调剂个住处。”安发说:“上次你不是在小组会上提过了吗?已经给你转到农会了。”聚财说:“老拐!今年可以吧?”老拐说:“可以!有几亩地,吃穿就都有了,就是缺个住处,打几颗粮食也漏上水了。”……
小旦也来找安发。他说:“安发!抽补也快完了,我这入贫农团算是通过了没有?”安发说:“上级又来了指示,说像咱这些贫农不多的地方,只在农会下边成立贫农小组,不成立贫农团了。”小旦说:“就说贫农小组吧,也不管是贫农什么吧,反正我是个贫农,为什么不要我?工作团才来的时候,串连贫农我先串连,给干部提意见我先提,为什么组织贫农时候就不要我了?”安发说:“抽补也快结束了,这会你还争那有什么用途?”小旦说:“嘻!叫我说这抽补还差得多啦,工作团都不摸底,干部、党员们多得的浮财跟没有退一样,只靠各人的反省退了点鸡毛蒜皮就能算了事吗?听工作团说,就只补这一回了,咱们这贫农要再不追一追,就凭现在农会存的那点浮财,除照顾了扫地出门的户口,哪里还分得到咱们名下?”安发说:“咱也不想发那洋财。那天开群众大会你没有听工作团的组长讲,‘平又不是说一针一线都要平,只是叫大家都能生产、都能过日子就行了。’我看把土地抽补了把房子调剂了,还不能过日子的就是那些扫地出门的户,农会存的东西补了人家也就正对,咱又不是真不能过日子的家,以后慢慢生产着过吧!”小旦听着话头不对,就抽身往外走,临走还说:“不管怎样吧,反正我也还愿意入组,遇着你们组里开会也可以再给我提提!”说着连回话也不听就走出去,看样子入组的劲头也不大了。他走远了,聚财低低地说:“他妈的!他又想来出好主意!”安发说:“工作团一来,人家又跑去当积极分子,还给干部提了好多意见,后来工作团打听清楚他是个什么人,才没有叫他参加贫农小组。照他给干部们提那些意见,把干部们说得比刘锡元还坏啦!”聚财低低地说:“像小昌那些干部吧,也就跟刘锡元差不多,只是小旦说不起人家,他比人家坏得多,不加上他,小昌还许没有那么坏!”安发说:“像小昌那样,干部里边还没有几个。不过就小昌也跟刘锡元不一样:刘锡元那天生是穷人的对头,小昌却也给穷人们办过些好事,像打倒刘锡元,像填平补齐,他都是实实在在出过力的,只是权大了就又蛮干起来。小旦提那意见还不只是说谁好谁坏,他说:‘……一个好的也没有,都是一窝子坏蛋,谁也贪污得不少,不一齐扣起来让群众一个一个追,他们是不会吐出来的!’”老拐说:“他还要追人家别人啦!他就没有说他回回分头等果实,回回是窟窿,分得那些骡子、粮食、衣裳。吃的吃了,卖的卖了,比别人多占好几倍,都还吐不吐?”聚财说:“说干部没有好的那也太冤枉,好的就是好的。我看像人家元孩那些人就不错!”安发说:“那自然!要不群众就选人家当新农会主席啦?”
他们正说着闲话,狗狗在院里喊叫:“妈!二姑来了!”安发老婆听说二姨来了,从套间里跑出来,安发他们也都迎出来。老拐没有别的事,在门边随便跟客人应酬了两句话就走了。
狗狗一边领着二姨进门,一边问:“二姑!你怎么没有骑驴?”
二姨说:“驴叫你姑夫卖了,还骑上狗屁?”
狗狗又笑着说:“二姑!你记得我前几年见了你就跟你要甚来呀?”二姨也笑着说:“狗狗到底大了些,懂事多了!要什么?还不是要花生?今年要也不行,你姑夫因为怕斗争,春天把花生种子也吃了,把驴也卖了!——大姐夫,听说你病了几天,我也没有来看看你!这几天好些?”
聚财说:“这几天好多了!——你们家里后来没有什么事吧?”
二姨说:“倒也没事,就是心慌得不行。听说你们这里来了工作团,有的说是来搞斗争,有的说是来整干部,到底不知道还要弄个甚。我说到这年边了,不得个实信,过着年心也不安,不如来打听打听!”聚财说:“这一回工作做得好!不用怕!……”
接着他和安发两个人,就预备把划阶级、赔补中农、安插地主富农、整党……各项工作,都给二姨介绍了一下。正介绍到半当腰里,忽听得前院争吵起来。
聚财听了听说:“这是小宝说话!安发你给咱去看看是不是吵软英的事?”安发说:“咱们都去看看吧!”聚财说:“我也能去?”
安发说:“可以!这几天开整党会,去看的人多啦!”说着,他们三个人就到前院里来。
这天的整党会挪在院里开,北房门关着,正中间挂着共产党党旗和毛主席像,下面放着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凳子。工作团的同志们坐在阶台上,区长和高工作员也在内,元孩站在桌子后当主席,阶台下前面坐的是十七个党员,软英和小宝虽不是党员,因为是支部叫来的,也坐在前面,后面便是参观的群众。当聚财他们进去的时候,正遇上小昌站着讲话,前边不知道已经讲了些什么,正讲到:“……我跟你什么仇恨也没有!我是个共产党员,不能看着一个同志去跟个有变天思想的人接近!不能看着一个同志去给斗争对象送情报!不能看着一个同志去勾引人家的青年妇女!我们党内不要这种人!况且开除你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主:我提议的,支部通过的,支部书记元孩报上去的,区分委批准的,如今怎么能都算到我账上?”聚财听了这么个半截话,似乎也懂得是说小宝,也懂得“有变天思想”和“斗争对象”是指自己,也懂得“勾引青年妇女”是指小宝跟软英的关系,只是不懂“开除”是什么意思。小昌说了坐下,小宝站起来说:“我说!”软英跟着也站起来说:“我说!”元孩说:“小宝先说!”小宝说:“党开除我我没话说,因为不论错斗不错斗,那时候软英她爹总算是斗争对象,大会决定不许说,我说了是我犯了纪律,应该开除。可是我要问:他既然是共产党员,又是支部委员,又是农会主任,为什么白天斗了人家,晚上就打发小旦去强逼人家的闺女跟他孩子订婚?那就也不是‘斗争对象’了?也没有‘变天思想’了?说我不该‘勾引青年妇女’,‘强逼’就比‘勾引’好一点?我这个党员该开除,他这个党员就还该当支委?”小宝还没有坐下,小昌就又站起来抢着说:“明明是‘自愿’,怎么能说我是‘强迫’?”元孩指着小昌说:“你怎么一直不守规矩?该你说啦?等软英说了你再说!坐下!”小昌又坐下了。聚财悄悄跟安发说:“这个会倒有点规矩!”安发点了点头。软英站起来说:“高工作员在这里常给我们讲‘妇女婚姻要自主’,我跟小宝接近,连我爹我娘都不瞒,主任怎么说人家是‘勾引’我?要是连接近接近也成了犯法的事,那还自主什么?主任又说我自愿嫁给他孩子,我哪有那么傻瓜?我也是二十多的人了,放着年纪相当的人我不嫁,偏看中了他十四五岁个毛孩子?要不是强逼,为什么跟我爹要金镯子?”软英说完了,
小昌又站起来说:“我说吧?我看这事情非叫小旦来不行!你们捏通了,硬说我要金镯子!我叫小旦来说说,看谁跟他提过金镯子?”后边参观的群众有人说:“还用叫小旦?聚财、安发都在这里,不能叫他两个人说说?”
聚财远远地说:“不跟我要金镯子的话我还许少害几天病!还是找小旦来吧!省得人家又说我们是捏通了!”
元孩说:“我看还是去找小旦吧!要金镯子这事也不止谈了一次了,不证明一下恐怕再谈也没结果!”
别的党员们也都主张叫小旦来证明一下,元孩就打发村里的通讯员去找。
这时候,登记农会房子的人也回来了,安发和别的农会委员们都回西房里议论调剂房子的事。元孩是新农会主席,可是因为在整党会上当着主席,只好把西房里的事托给副主席去管。
不多一会,把小旦找来了,整党会又接着开起来。小昌说:“小旦哥!你究竟说说你给我说媒那事是自愿呀是强迫?”小旦想把自己洗个干净,因此就说:“我是有甚说甚,不偏谁不害谁!主任有错,我也提过意见,不过这件事可不是人家主任强迫她。如今行自主,主任托我去的时候,我是亲自跟软英说的。那时候,她给我倒了一盅水,跟我说……”接着就把软英给他倒上水以后的那些话,详详细细实实在在说了一遍,然后说:“我说这没有半句瞎话,大家不信可以问安发。”
软英说:“不用问我舅舅了,这话半句也不差,可惜没有从头说起,让我补一补吧:就是斗争了我爹那天晚上,小旦叔,不,小旦!我再不叫他叔叔了!小旦叫上我舅舅到了我家,先叫我舅舅跟我爹说人家主任要叫你软英嫁给人家孩子。说是要从下还可以要求回几亩地,不从的话,就要说我爹受了人家刘家的金镯子。没收了刘家的金镯子主任拿回去了——后来卖到银行谁不知道?那时候跟我爹要起来,我爹给人家什么?我怕我爹吃亏,才给小旦倒了一盅水,跟他说了那么一大堆诡话,大家说这算不算自愿?他小旦天天哄人啦,也上我一回当吧!”小旦早就想打断她的话,可惜找不住个空子,一听到她说了自己个“天天哄人”,马上跳起来指着软英喊:“把你的嘴收拾干净点!谁天天哄人啦?”高工作员喝住他说:“小旦你捣什么乱?屈说了你?我还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人?”小旦这才算又坐下了。参观的群众有人小声说:“还辩什么?除了小旦谁会办这事?”没有等小昌答话,别的党员们你一句我一句都质问起来:“小昌!你这个党员体面呀?”“小昌!你向支部汇报过这事没有?”“小昌!你这几天反省个啥?”……元孩气得指着问他说:“有你这种党员,咱这党还怎么见人啦?”
小昌眼里含着泪哀求小旦说:“小旦哥!你凭良心话,我托你去说媒,还叫你问人家要过金镯子?”
小旦说:“要说实的咱就彻底说实的,在斗争会上的头一天晚上,你把我叫到你家,托我给你去办这事。你说:‘明天斗争完了,趁这个热盘儿容易办。’我说人家早就要‘自由’给小宝,你说:‘不能想个办法先把小宝撵过一边?’恰巧我那天晚上回去就碰见小宝跟聚财家出来,第二天早上我又跟你商量先斗小宝,你说可以,那天就把小宝也斗了。到了晚上我去叫安发,顺路到你那里问主意。我说:‘不答应怎么办?’你说:‘你看着办吧!对付小宝你还能想出办法来,还怕对付不了个聚财?’你还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人?你叫我看着办,我要不出点坏主意怎么能吓唬住人?要金镯子的主意是我出的,东家可是你当的!”
听小旦这么一说,聚财在后边也说了话。他说:“我活了五十四岁了,才算见小旦说过这么一回老实话!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他说了这么两句话,一肚子闷气都散了,就舒舒服服坐下去休息,也再没有想到怕他们报复。
小宝又站起来说:“主席!这总能证明斗争我是谁布置的吧?这总能证明要过金镯子没有吧?这总能证明是强迫呀还是自愿吧?”
另一个党员说:“主席!只这一件事我也提议开除小昌!”
另有好几个党员都说:“我也附议”,“我也附议”……
元孩向大家说:“我看这件事就算说明了,今天前晌的会就开到这里吧!处分问题,我看还是以后再说,因为小昌的事情还多,不能单以这件事来决定他的处分。以下请组长讲讲话!”
工作团的组长站起来说:“这件事从工作团来到这里,小宝就反映上来了,我们好久不追究,为的是叫小昌自己反省。从今天追究出来的实际情形看,小昌那反省尽是胡扯淡啦!小昌!你想想这是件什么事?为了给自己的孩子订婚,在党内党外布置斗争,打击自己的同志,又利用流氓威胁人家女方,抢了自己同志的恋爱对象。这完全学的是地主的套子,哪里像个党员办的事?最不能原谅的,是你在党内反省了一个多月,一字也没有提着这事的真相,别人一提你就辩护,这哪里像个愿意改过的人?给你个机会叫你反省你还不知道自爱,别人谁还能挽救你?你这种行为应该受到党的处分!此外我还得说说小旦!小旦!我们今天开的是整党会,你不是党员,这个会上自然不好处分你。不过我可以给你先捎个信:你不要以为你能永远当积极分子!在下河村谁也认得你那骨头!土改以后,群众起来了!再不能叫你像以前那样张牙舞爪了,从前得罪过谁,老老实实去找人家赔情认错!人家容了你,是你的便宜;人家不容你,你就跟人家到人民法庭上去,该着坐监就坐监,该着枪毙就枪毙!那是你自作自受,怨不着别人!”
组长讲完了,元孩就宣布散会。大家正站起来要走,软英说:“慢点!我这婚姻问题究竟算能自主不能?”区长说:“整党会上管不着这事!我代表政权答复你:你跟小宝的关系是合法的。你们什么时候想定婚,到区上登记一下就对了,别人都干涉不着。”
散会以后,二姨挤到工作团的组长跟前说:“组长!我是上河人!你们这工作团不能请到我们上河工作工作?”组长说:“明年正月就要去!”
(全文完)
一九四八、一〇、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