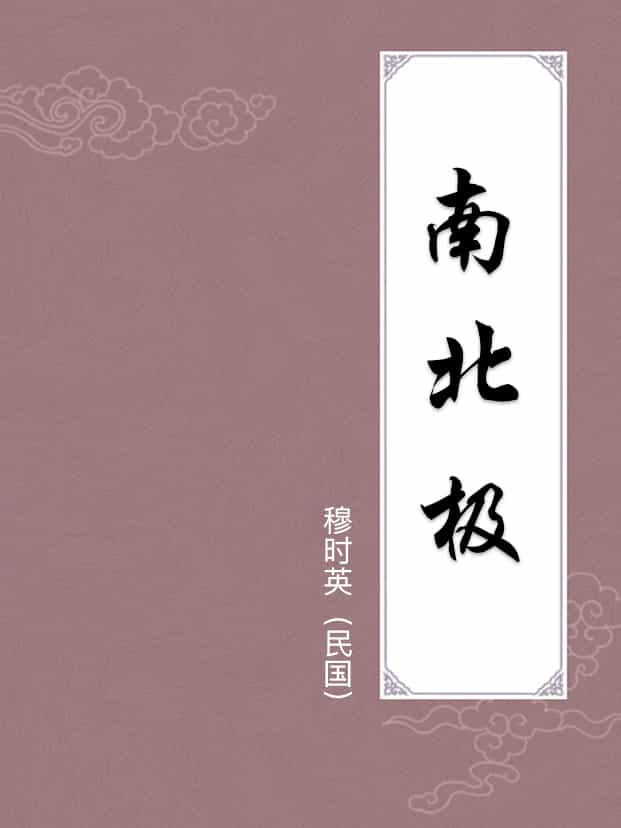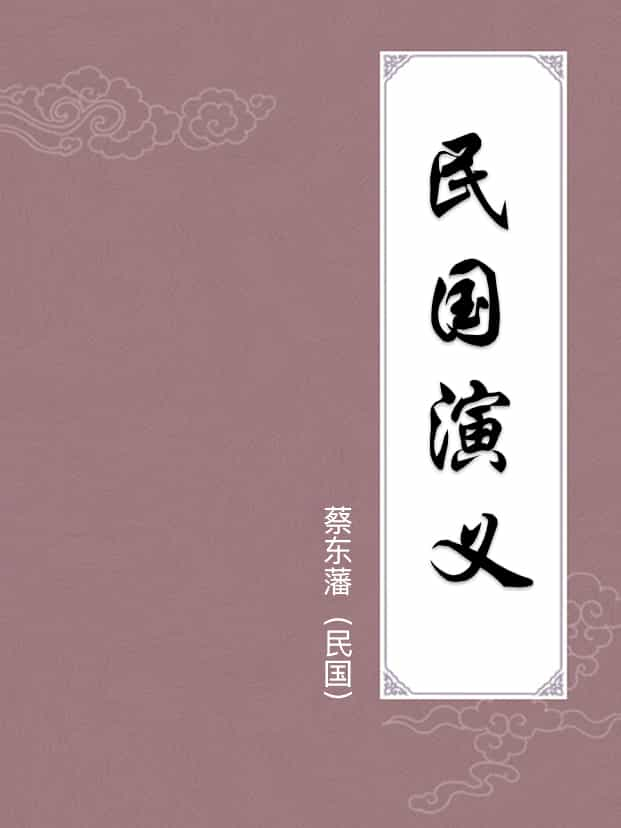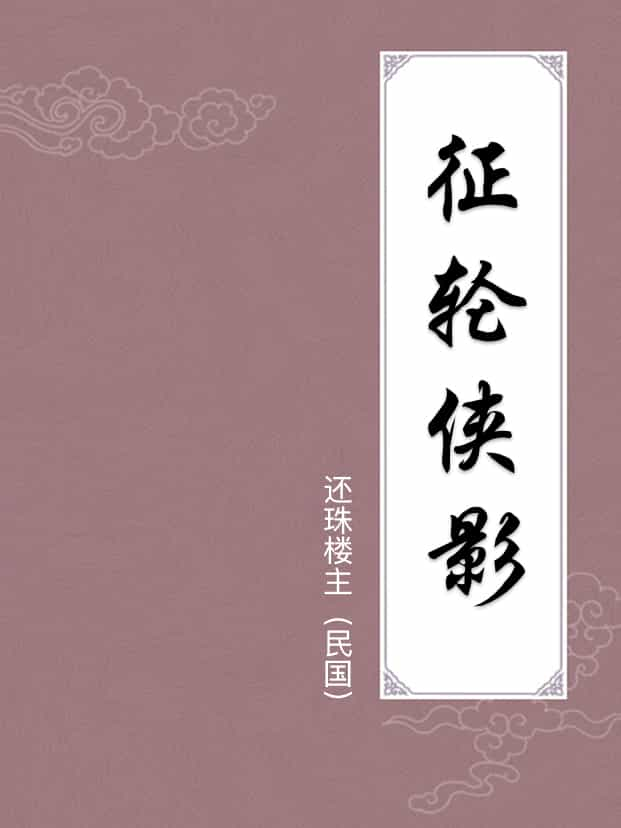孩子病了。
抱在手里,轻极了,一点不费力。孩子的脑袋一天比一天大啦。只干哭,没眼泪。眼珠子隐在眼眶里,瞧爹。他心里急。他听着他的哭声——他的哭声一天显得比一天乏。他自家儿有好几个晚上没好好儿的睡了。
饭是要吃的,钱已经从哥那儿借了不少,姐夫那儿也借了,又没心思做生意,孩子也没人管。成天的想着翠娟,他知道她的左胳膊上是有一颗大黑痣的。可是翠娟没回来。
他带了孩子,走到西摩路,找到那地方儿,是一座很大的洋房,按了下电铃。大铁门上开扇小铁门,小铁门上一扇小铁窗开了,一颗巡捕脑袋露出来。
“对不起,翠娟在不在这儿?”
“没有的,什么翠娟。你找谁呀?”
“新来的一个佣人,不十分高,长脸蛋的。”
“可是在二少爷房里的?”
“对啦!”
那巡捕开了门让他进去,叫他等一回儿。他暗地里叫了声天,觉得腿也跑乏了,胳膊也抱酸了,便靠在墙上歇着。不一回儿那巡捕走了出来,问他道:
“你姓什么?”
“姓林。”
“翠娟说他没丈夫的。”
“我就是他的丈夫嘛!”
“你弄错人了。这里的翠娟没有丈夫的。走吧!”
他只得跑了出来,站在路上。他等着。他想等她出来。
“爹,妈呀!”孩子的声音像蚊子的那么细。
“别哭,妈就来的。”
直等到天晚,他走了回去。没吃饭,望着孩子发愁。孩子不会哭了。他踱着,踱到半晚上,孩子眼皮一阖。
“宝贝!宝贝!”
孩子不作声,也不动。
他再叫了声儿:“宝贝!”
孩子不作声,也不动。
他一声儿不言语,抱着孩子,踱到那边儿看见褪了漆的门,踱到这边儿,看到纸糊的格子窗,窗外静悄悄的。
他一声儿不言语,抱着孩子,踱到那边儿,看见褪了漆的门,门里边那间屋子从天窗那儿漏下一块模模糊糊的光来,踱到这边儿,看到那纸糊的格子窗,窗前的地板上也有了一扇格子窗。
猛的,他坐到床上,放了孩子,用他那条又酸又麻的胳臂托着脑袋,揪着头发,哭了。
他尽坐在那儿,泥塑的似的。傍晚儿,他把孩子装蒲包里边,拎了出去。回来时走过那家绸缎铺子,那家饽饽铺子,那家老虎灶,拐弯,进了胡同,第一家,第二家……胡同里有人打牌,有人滚铜子……第八家,门上斗大的财字,第九家,格子窗破了个窟窿,跨到自家儿家里——空的,只有他一个人。门也不带上,又跑去了。
半晚上,他回来啦,红着眼珠子,扶着墙,呕着,摸到自家儿门口,推开门跨进去,绊在门槛上,一交跌下去,就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嘴犄角儿喷着沫,嘴啃在地上,臭的香的全吐了出来,便打起鼾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