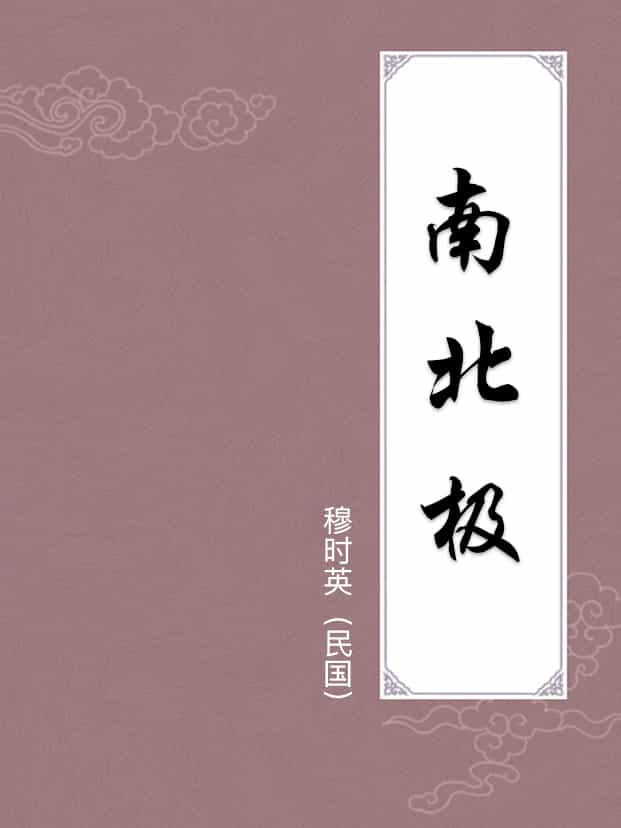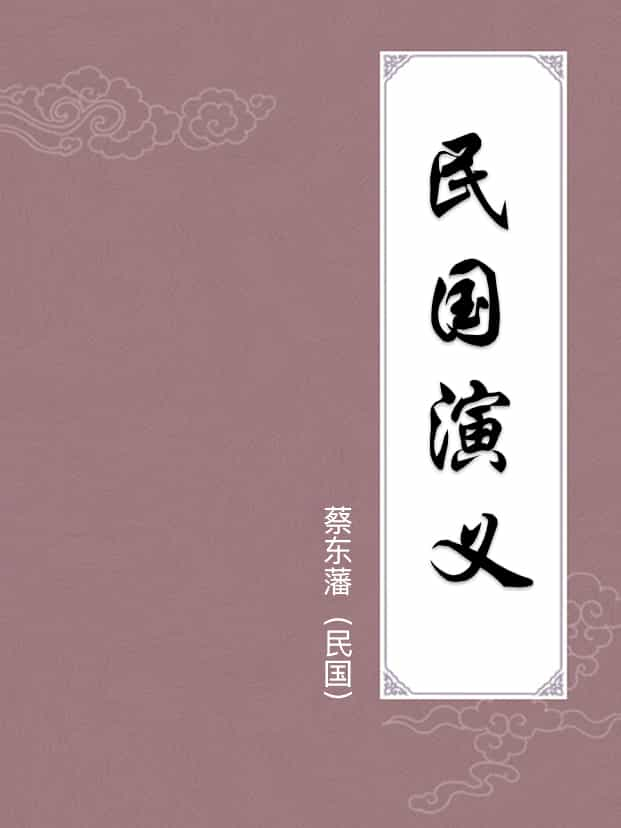第二天醒来,匆匆地洗了脸,在睡着的孩子的脸上亲了一下,就往门外跑。街上站岗的巡捕还没来,冷清清的没一辆汽车,只有拉车的揉着眼,拉着空车在懒懒地走,穿红马夹的清道夫却已经在那儿扫马路了,一群群穿蓝大褂的,手里拿着刚买的早餐站在电车站在那儿等车。
坐在拖车里,打呵欠的人,打盹的人,揉着眼的人他全没瞧见,他只想着他的掉了漆的板壁,没虎牙的孩子和翠娟。望着窗外,街上慢慢儿地热闹了起来。还是时候不早了呢?还是车从冷静的地方儿驶到热闹的地方儿来了呢?他全不管。他有一个家,一个媳妇和一个孩子!
进了机器间他不敢再想了。他留神着那大轮子,他瞧见过许多人给它的牙齿咬断了腿,咬断了胳膊,咬断了脖子的。他不能叫它沾到他的身子。要是他给它咬断了什么的话?——他不会忘记他有一个孩子和一个媳妇。可是真的他断了一条胳膊呢?大轮子隆隆地闹着,雪亮的牙齿露着,望着他。他瞧见它喀的一声儿,他倒了下去,血直冒,胳膊掉在一边……他喘了口气,不能往下想。
断了条胳膊的人是怎么的?不能做工,不能赚钱,可是肚子还是要吃饭的,孩子还是要生下来的,房钱还是要出的,天还是要下雪的——
“要是有这么一天给大轮子咬断了什么呢!”——见到大轮子就这么地想着,跑到家里,见到那掉了漆的墙,见到那低低的天花板,也会这么地想起了的。想着想着,往后自家儿也慢慢儿的相信总有一天会闹出什么来了。老梦着自家儿断了条腿,成天的傻在家里,梦着媳妇跟他哭着闹,梦着孩子饿坏了,死啦,梦着……梦着许多事。在梦里他也知道是梦,急得一身冷汗,巴不得马上醒回来,一醒回来又心寒。可是心寒有吗用呢?他是成天的和大轮子在一块儿混的。
吃了晚饭,他们坐着说话。他尽瞧着翠娟。
“要是我给机器轧坏了,不能养家了,那你怎么办?”
“别放屁!开口就没好话,那有的事——”
“譬如有这么一回事。”
“没有的事!”
“我是说譬如有这回事——说说不相干的。”
他盯住了她的眼珠子瞧,想瞧出什么来似的。
“譬如吗?”停了一回儿。“那你说我该怎么呢?”
“你说呀!我要问你怎么办。”
“我吗?我还有怎么呢?去帮人,去做工来养活你们。”
他不作声。想。过了回儿说:“真的吗?”
“难道骗你?”
他不说话,笑了笑,摇了摇头。
“那么,你说怎么呢?”
“我说,你去嫁人——”
“屁!”
“我抱了孩子要饭去。”
“为什么说我去嫁人呢?你要我去嫁人吗?”
“你受不了艰穷。”
“屁!别再瞎说霸道,我不爱听。”
他不说话,又笑了笑,摇了摇头。
晚上他睡不着。他瞧见自家儿撑着拐杖,抱着孩子,从这条街拐到那条街。
孩子哭了。翠娟含含糊糊的哼着,“宝贝睡啦宝贝睡……妈妈疼宝贝——”轻轻儿的拍着他;不一回儿娘儿俩都没声了。
他瞧见自家儿撑着拐杖,抱着孩子,从这条街拐到那条街。他听见孩子哭。他瞧见孩子死在他怀里。他瞧见自家儿坐在街沿上,捧着脑袋揪头发,拐杖靠在墙上。
猛的,他醒了回来。天亮了。他笑自家儿:“怯什么呀?”
他天天壮着胆笑自家儿:“怯什么呀?”逗着孩子过日子,日子很快的过去了。
是六月,闷热得厉害。晚上没好好的睡,叫蚊子咬狠了,有点儿头昏脑涨的。他瞧着大轮子一动,那雪亮的钢刀,喀的砍下来,一下子就把那挺厚的砖切成两半。皮带隆隆的在半空中转,要转出火来似的。他瞧见一个金苍蝇尽在眼前飞。拿袖子抹抹汗。他听见许多的苍蝇在他脑袋里边直闹。眼前一阵花。身子往前一冲,瞧见那把刀直砍下来,他叫了一声儿,倒啦。
迷迷忽忽地想:“我抱了孩子要饭去。”便醒了回来。有人哭,那是翠娟,红肿着眼皮儿望他。他笑了一笑。
“哭什么?还没死呢!”
“全是你平日里胡说霸道,现在可应了。”
“你怎么跑来了?孩子扔在家里没人管!”
“你睡了两天,不会说话。你说,怎不急死我!”
“我说,你怎么跑来了,把孩子扔在家里——”
“我说呀,你怎么一下子会把胳膊伸到那里边去了?”
“真累赘,你怎么专跟我抢说话,不回我的话呀?我问你,孩子交给谁管着。”
“大姑在家里管着他。”
“姐姐吗?”
“对。姑丈和大伯伯上厂里要钱去了,这里医院要钱呢。”
“家里零用还有吧,我记得还有二十多块钱在那儿。”
她低下了脑袋去抹泪。
“可是,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再说吧,还有一条胳膊咧。”
他望着她,心里想:“我抱着孩子要饭去吧。”一面就催她回去看孩子。她又坐了好久,也没话说,尽抹泪,一条手帕全湿了。
他又催她,她才走。她走了,他就想起了拐角那儿的西乐队,饽饽铺子的铁杓敲在锅沿上的声音……老虎灶里的那个胖子还是把铜杓子竖在灶上站在那儿吧!接着便是那条小胡同,熟悉的小胡同,斗大的财字……他是躺在这儿,右胳膊剩了半段,从胳膊肘那儿齐齐地切断了,像砖那么平,那么光滑。
第二天,姐姐,哥,和姐夫全来了。他们先问他怎么会闹出那么的事来的,往后又讲孩子在家里要爹,他们给缠得没法,又讲到昨儿上厂里去要钱的事,说好容易才见着厂长,求了半天,才承他赏了五十元钱,说厂里没这规矩,是他瞧你平日做人勤谨,他份外赏的,还叫工头给抽去了五元,多的全交给翠娟了。
“往后怎么过呢?”
听了这话,他闭着嘴望他们。他们全叫他瞧得把脑袋移了开去。他说:“我也不知道,可是活总是要过的。”过了回儿又说:
“我想稍微好了些,搬到家里养去,医院里住不起。”
“究竟身子要紧,钱是有限的,我们总能替你想法。”
“不。现在是一个铜子要当一个铜子用了。”
在医院里住了两个礼拜。头几天翠娟天天来,坐在一旁抹泪,一条手帕全湿了才回去。往后倒也不哭了,只跟他谈谈孩子,谈谈以后的日子。她也从不说起钱,可是他从她的话里边听得出钱是快完了。那天她走进来时,还喘着气,满头的细汗珠子,脊梁盖儿全湿啦。
“怎么热得这个模样儿?”
“好远的路呢!”
“走来的吗?”
“不——是的,我嫌电车里挤得闷,又没多少路,反正没事,所以就走来了。”
“别哄我。是钱不够了,是不是?”
她不说话。
“是不是?”
猛的两颗泪珠掉下来啦,拿手帕掩着鼻子点了点头。
“还剩多少?”
“十五。可是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厂里拿来的五十元钱呢?全用在医院里了吗?”
她哭得抽抽咽咽的。
“怎么啦?你用了吗?”
“大伯伯骗你的,怕你着急。厂里只争到三十元,这里用的全是他和姑丈去借来的。我们的二十多,我没让他们知道。”
“哦!”想了想。“我明天搬回家去吧。”
“可是你伤口还没全好哪。”
“还是搬回去吧。”
他催着她回去了。明天早上,他哥来接他,坐了黄包车回去。
他走过那家绸缎铺子,那家饽饽铺子,胡同还是和从前一样。走到胡同里边,邻舍们全望着他,望着他那条断了的胳膊。门那儿翠娟抱着孩子在那儿等着。孩子伸着胳膊叫爹。他把孩子抱了过来,才觉得自家儿是真的少了一条胳膊了。亲着孩子的脸,走到屋子里边,还是那掉了漆的墙壁,什么都没动,只是地板脏了些,天花板那儿挂着蛛网。他懂得翠娟没心思收拾屋子。孩子挣下地来,睁大着眼瞧他的胳膊。
“爹!”指着自家儿的胳膊给爹看。
“乖孩子!”
孩子的脑门下长满了痱子。只要孩子在,就是断了条胳膊还是要活下去的!这时候有些人跑进来问候他,他向他们道了谢。等他们走了,身子也觉得有点乏,便躺在床上。哥走的时候儿,还跟他说:“你要钱用,尽管跟我要。”他只想等伤再稍微好了些,就到厂里去看看。他还是可以做工的,只是不能再像别人那么又快又好罢咧。翠娟忽然叹了口气道:
“你真瘦狠咧。”
“拿面镜子我照一下。”
镜子里是一张长满了胡髭的瘦脸,他不认识了。扔了镜子——“我还是要活下去的!”
“现在我可真得去帮人了。”
“真的吗?”
“要不然,怎么着呢?咱们又不能一辈子靠别人,大伯伯和姑丈也不是有钱的,咱们不能牵累他们。”
“真的吗?”
“你等着瞧。”
他笑了笑,摇了摇头,瞧见自家儿用一条胳膊抱着孩子从这条街跑到那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