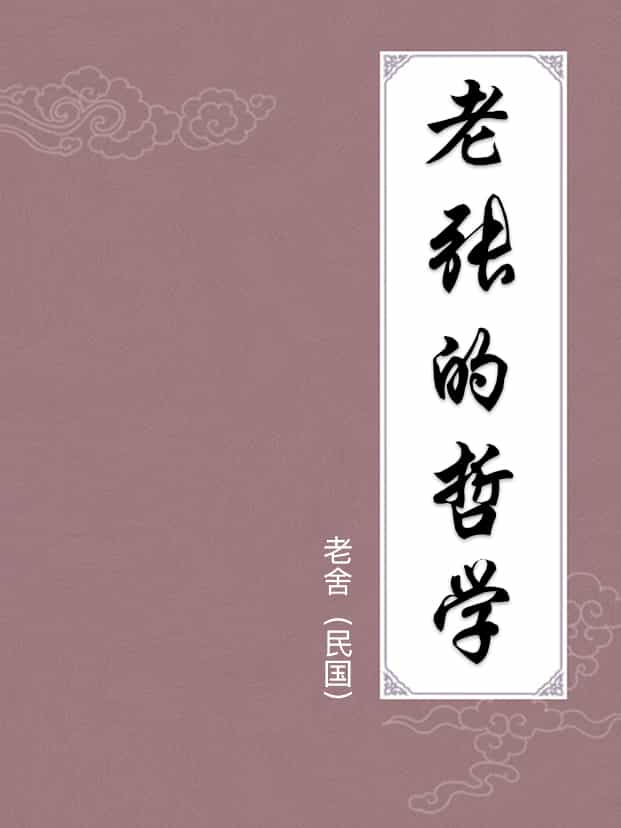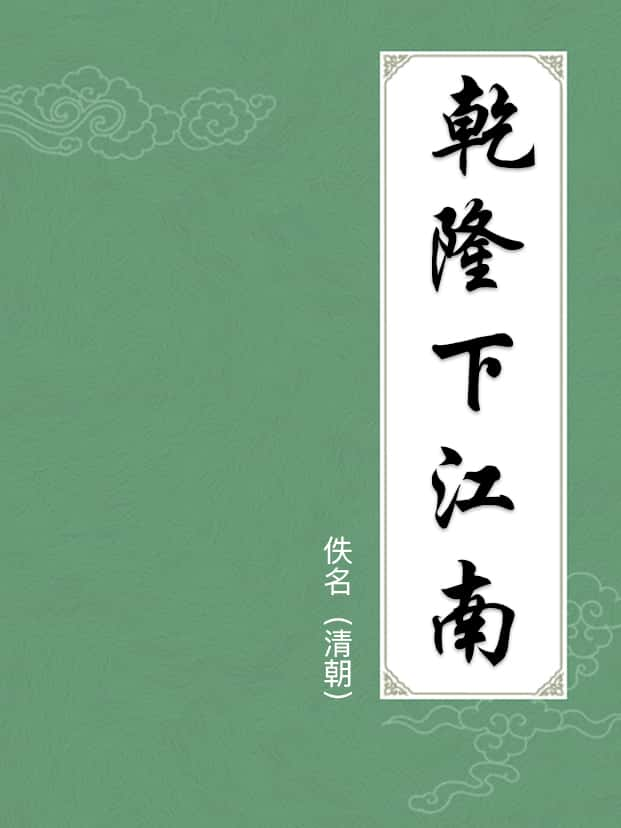李静昏昏沉沉的进了德胜门,风是小了,可是泪比来的时候被风吹出来的更多了!
过了德胜桥,街上的人往前指着说:“看!董善人!”一个老妇人急切的向一个要饭的小姑娘说:“还不快去,董善人在那里,去!”
李静也停住看:一位老先生穿着一件蓝布棉袍盖到脚面,头上一顶僧帽,手中一挂串珠。圆圆的脸,长满银灰的胡子,慈眉善目的。叫花子把他围住,他从僧帽内慢慢掏,掏出一卷钱票,给叫花子每人一张。然后狂笑了一阵,高朗朗的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李静心中一动,可是不敢走上前去,慢慢的随着那位老先生往南走。走过了蒋养房东口,那位先生忽然又狂笑了一阵,转过身来往回走,进了到银锭桥去的那条小巷。李静看着他进了小巷,才开始往姑母家走。
她低着头走,到了护国寺街东口。
“静姐!你回来了!”
王德立在一个铺子的外面,脸冻的通红。
“静姐!我的事成功了!”他像小孩子见着亲姐姐一样的亲热。
“是吗?”她说。
“是!给大强报校对稿子,访新闻。二年之后,凭我的才力,就是主笔。姐姐!你知道主笔都是文豪!”
“王德!”
“在!”
“姑母在家没有?”
“上铺子和姑父要钱去了。”
“快走,到家我告诉你要紧的事。”
“得令!”
王德随着赵姑父在天桥戏棚听过一次文武带打的戏。颇觉得戏剧的文学,有短峭明了的好处,每逢高兴,不知不觉的用出来。
两个人到了家,李静急切的对王德说:“王德!你去给我办一件事,行不行?”
“行!可是等我说完我的事。”
“王德!”李静急得要哭,“我求你立刻给我办事去!”
“不!我要不先告诉明白你我的事,我心里好像藏着一条大蟒,一节一节的往外爬,那是这么一件事,我今天……”
“王德!你太自私了!你不爱我?”
“我不爱你,我是个没长犄角的小黄牛!”
“那么我求你作事,为什么不注意听?”
“说!姑娘!我听!说完你的再说我的!”
“你知道北城有一位董善人?你去给我打听他的住址。”
“你打听他作什么?”
“你要是爱我,请不必细问!”
“今天的事有些玄妙!不准问,不准说!好!不问就不问,王德去也!”
王德扯腿往外跑,邦的一声开开街门,随着“哎哟”了一声。李静跟着跑出来,看见王德一手遮着头,一手往起竖门闩。
“王德!打着没有?”
“没有!除了头上添了一个鹅峰。”王德说罢又飞跑去了。
不到十分钟,王德跑回来。
“王德,你的头疼不疼?”她摸了摸他的头依然是滚热的。
“不疼!静姐!我跑到街上,心生一计:与其到北城打听,不如去问巡警。果然巡警告诉我那位善人的住址,是在银锭桥门牌九十八号,你的事完了,该我说了罢?”
“说罢。”
“姐姐!你有什么心事?‘说罢’两个字不像你平日的口气。”
“没有心事,你的事怎样?”
“作访员,将来作主笔!这绝不是平庸的事业!你看,开导民智,还不是顶好的事?”
“你要作文章,写稿子,报馆要是收你的稿件才怪!”
“静姐,你怎么拿我取笑!”王德真不高兴了。
“你不信我的话,等姑父回来问他,听他说什么!”
“一定!问了姑父,大概就可以证明你的话不对!”王德撅了嘴,心里想:怎样作稿子,怎样登在报上,怎样把有自己的稿子的报,偷偷放在她的屋里,叫她看了,她得怎样的佩服。……
李静想她自己的事,他想他自己的事,谁也不觉寂寞的彼此看着不说话。
李应回来了。
“李应!好几年没见!”王德好容易找到一个爱听他的事情的,因为李静是不愿听的。
“王德,怎么永远说费话?今天早晨还见着,怎就好几年?”李应又对他姐姐说:“叔叔说什么来着?”
“对,姐弟说罢!今天没我说话的地方!”
“王德!别瞎吵!”李应依旧问她:“叔父怎样?”
“叔父身体照常,只嘱咐你好好作事。”李静把别的事都掩饰住。
“王德你的事情?”李应怕王德心里不愿意,赶快的问。
“你问我?这可是你爱听?好!你听着!”王德可得着个机会。“今天我出城,遇见一位亲戚,把我介绍到大强报报馆,一半作访员,一半作校对。校对是天天作,月薪十元;访稿是不定的,稿子采用,另有酬金。明天就去上工试手。李应,学好了校对和编稿子,就算明白了报馆的一大部分,三二年后我自己也许开个报馆。我决不为赚钱,是为开通民智,这是地道的好事。”
王德说完,专等李应的夸奖。
“错是不错。”李应慢慢的说:“只是世界上的事,在亲自经验过以前,先不用说好说坏。”
“好!又一个闷雷!在学堂的时候我就说你像八十岁的老人。你说话真像我老祖!”王德并没缺了笑容。
“事实如此!并不是说我有经验,你没有。”
“我到底不信!世界上的事就真是好坏不能预料的吗?”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王德!等有工夫咱们细说,现在我要想一想我自己的事。”
李应说完走到自己的屋去,李静去到厨房作晚饭,只剩下王德自言自语的说:
“对!咱也想咱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