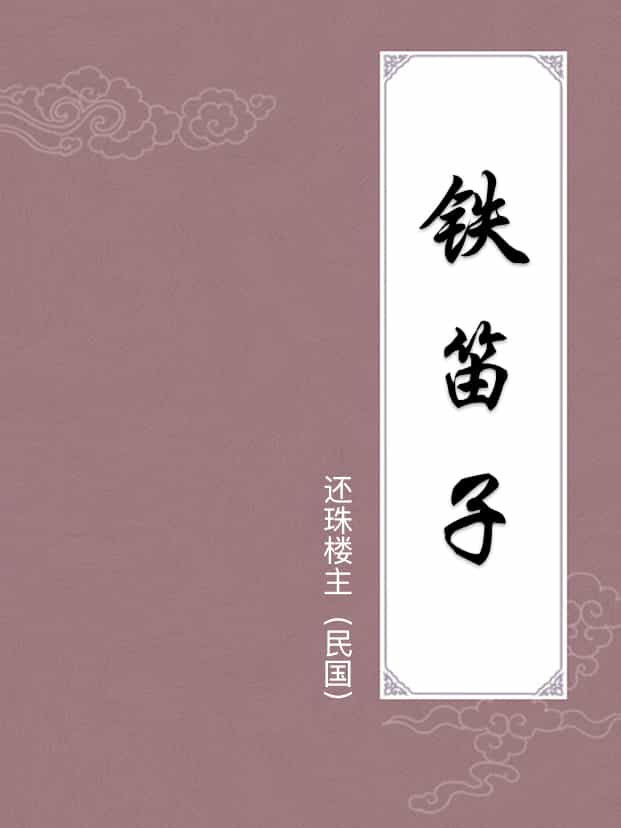旺子早就认出那两只山鸡正是被擒遗失林内,后在山口看见瘦子提在手上之物,先颇惊奇,当此性命关头,饥渴交加之际,也就不去管它,随口应答了几句,便说:"自己只要一只,加上蒸馍麦饼足够一饱,下余请众分吃。"一面暗中留神,见拿鸡的二童虽和众人一样,赤着双脚,穿着一身补了巴的旧衣,看去人颇灵巧。众人只两个年长的稍微干净,也是大人旧衣改制,比外面那些穷苦村童好不多少,方觉恶人家里的奴才高低也大不同,怪不得他们心好,原来和我们一样,也是终年做着牛马,干看别人享福的人,比起日里那些驴日的恶奴,一个个如狼似虎,真个相差天地。忽然瞥见内一幼竟暗使眼色,想起送鸡的人,心中一动,正想探询,另一幼童忽说:"那人说,今夜大概不会过堂,也许少时还有人来,我们最好走开,把他给的钱各人分上一二百,再把这只鸡吃掉,免得被人看破。"
众幼童的父兄虽在园中做事,都是当地土人,终年劳苦,勉强度日,这些幼童第一次得到许多钱,全都喜出望外。年幼无知,只管围在门外乱吵,一经提醒全都害怕,连那喂鸡与旺子吃的一个也忙着想走。二幼童乘机接过,笑说:"我弟兄年纪小,我婶子年轻,又是老太太身边的人,有点情面,不会乱打。钱你们分,只装不知,闯出祸来,由我二人拼着挨打挡这一阵,由我来喂他吃好了。"众幼童已不得有人承当,又急于分钱吃鸡,一声招呼便纷纷散去。
旺子也吃了大半饱,因恐人来,边问边吃。二童便说,"那位老大伯说,你今夜非被打死不可,全仗他出力解救才得无事。他要救你出去,张家再加十倍的人也拦他不住,随时均可下手。因我不信,他还做给我看,巴斗大一块山石,被他一拍便成粉碎。后角门外大树,被他指头一触,就是三个两寸来深的洞眼。本来这时就可救你出去,只为你日里有眼无珠,心眼太死,救你不救还不一定,要看心意如何,叫我转问一声。如肯拜他为师,今夜必可将你救走,做了他的徒弟,从此不受人欺,吃好的,穿好的,钱随便用,永无用完之时。如其不愿,守定你那叫花师父,也不勉强,但他只请你吃这两只鸡,底下他只顾自己的事,任凭恶人打死便不管了。"
说时旺子业已吃完,见二幼童一个忙着说话,一个便去台下望风,神色甚是张皇。
一问那人形貌,正是叫老五的瘦长子。料这两人必是王老汉所说飞贼大盗一流,并还是师父的死对头,不禁气道:"你对他说,我旺子情愿被人打死,也决不拜他这样人为师。
本来这两只鸡我不应该吃人家的,一则此鸡乃我途中所失,被他拾去,只算物归原主,并且我还请他们吃过两只,他为我跑这一趟只当还情,也不冤枉。从此双方抵消,谁也不该谁。休说我旺子有师父,决不做他徒弟,便是以后他有什好意,我也不会再领。他二人如是英雄好汉,决不以大欺小,借此害人。我一个没有本领的贫苦孤儿,因我不肯听他的话,不再管我闲事,我决不恨,只请他不要在我危急之时暗算作梗就是好汉了。
我有本领自会想法逃出,如果该遭毒手,被小狗打死,师父一来自会代我报仇。他和恶人作对是他的事,不与我相干,请他不要管我的事。你两个弟娃真好,叫什么名字,肯对我说么?"
二幼童大的一个年已十龄,看去甚是机警,边听边收拾鸡骨和地上的饼屑,原受指教而来,本意旺子闻言定必惊喜,一听这等说法不由气往上撞,还未听完,刚把小眼一瞪,说:"旺子你怎不知好歹,这位老人家我想拜师还不知答应不呢。想收你做徒弟,你倒不要。我叫钟大娃,那是我兄弟二娃,好心好意送你吃的,说话这等气人。这高本领的师父你不要,却想做小叫花子!"旺子暗忖,瘦长子虽非好人,这几个小娃都还不差,何苦叫他生气,刚笑说:"弟娃不必生气,我已有了师父,人又极好,你将来一见自会知道。"忽听头上有人接口道:"这娃虽是死心眼,颇有骨头,大娃二娃快回屋去,一会便有人来给他苦吃。他不知好歹,由他去吧。"
二幼童闻声往上一看,天空阴云业已布满,星月无光,洞口昏灯摇曳中,离地数丈高的削壁上面大壁虎也似隐绰绰爬着一条人影,听出口音正是方才在角门外送鸡的瘦长老人。钟大娃兄弟在那伙幼童中年纪最轻,也最聪明,早为瘦长子所动,立意想要拜师,闻声惊喜,连忙应诺。先朝台下一看,方才七八个男女幼童业已拿了钱赶往果林深处,暗中平分,无一在旁。乃弟二娃正由下面跑上,连打手势,口中呼哨,以作警告,料知园中有人要来,忙即仰头低声说道:"老师父快走,他们来了。旺子不知好歹,吃了苦自会知道。"随将外层木门关上,跟着二娃往下逃走。旺子在里面,耳听二童行时又朝上低问:"何处相见?"瘦长子答以"明日夜晚可到园外山崖之后竹林中相待,到时还有话说。"跟着一阵脚步之声顺梯而下,便没了声息。
木门关后石牢越发黑暗,等了一阵不见人来。正想试探着由后面弯手将腰间尖刀拔出,设法割断绑索再想主意,忽听说笑之声,忙装老实,坐在墙跟底下。正在呻吟,来人业已走上,共只两人,为首一个恶奴恶狠狠将门打开,先隔着铁栅怒骂:"狗娃,今日运气,你不该粗心大胆将我家相公撞伤,如今当你刺客,本定今日夜里要你狗命,总算你狗娃运气,庄中出了一点小事,现奉相公之命来些查看,并给你吃点食物,免得明日有气无力,不好挨打。"
旺子心中恨毒,本想骂他几句,后由昏灯中认出来人中有一个年老的以前相识,人也稍微和善,立在一旁并未开口,忽然动念,求告道:"大叔,此事不能怪我,你们也都看见,我几时是在行刺,他从后面跑来撞在我的身上,自家没有气力,我又惊慌太甚,这才无意之中将他碰倒。这点小事如何便要我的性命?"先发话的一个正要开口喝骂,被那年老的劝住,笑说:"他一个无知的放羊娃,孤苦伶仃,连个亲人都没有,何苦与他一般见识。"先发话的忽然惊道:"天快下雨,这里离前面还有好些路。相公今日连吃大亏,怒火头上,我还有事,有劳老大哥,我要先走了。"说罢转身匆匆往下走去。
年老的见同伴一走,悄悄说道:"旺子,方才前庄那些土人见你可怜,均来托我求情。无奈事情太大,这位小爷已恨你入骨,本是凶多吉少,总算运气,方才他由里面走出,正要过堂,不知怎的会跌了一跤,和日里一样,不怪自己疏忽,却说都是你这野种害的。听杨教师说,他受伤甚重,休说坐堂,弄得不好还要残废。也不知怎的,走得好好,无故会跌这一跌,几乎痛晕过去。本来已顾不得打你,方才忽然传话,说你罪魁祸首,万不能容,因我随他多年,将我喊去,命先毒打一阵,又要将你饿个半死,等他好了再打。我深知这位小爷脾气,劝说无用,故意用巧话说了几句,表面劝他自己报仇,实则想你多活两天,免得当时送命。万一五行有救,他这人喜怒无常,过上几天我再暗托那两位教师想好说词,也许能有挽回,想法子恭维他一阵,一下不挨就此放掉都在意中,省得小小年纪冤枉把命送掉,因此赶来送一口信。你千万不要心厌胡打主意。你要记好,一个人只最后一口气未断,便有生机。他们说你性子太烈,千万轻生不得。
"我跟大老爷虽然最早,连大相公也都说我真实可靠,只是我是山东人,不会巴结,出力看摊子的事情向例由我去做,要代人求情说好话多半说不进去。总算一班同事知我是老人,好些有关系的事都由我管。大相公虽不喜欢,却相信我,因此还不十分排挤。
这几日内我必为你尽心。本来叫把喂狗吃的东西与你拿来,叫你做狗,爬在地上咬吃,我把同伴说了几句,拿了一点剩菜蒸馍,你手绑上也不好吃,天又快要落雨,不及等候,等我把你绑绳解开,先舒散一夜,稍微养神,我再托看园的老钟随时留意。如其相公传命带人,再把你绑上。此是私情,你却不可对人说起。"
旺子知道对方人较忠厚,以前那几家农人敢喊自己回来做事,托的便是他,由不得心生感激,连声称谢。那人乃张家老仆张升,已将铁栅开放,亲自把食物送进,代将背后绑绳去掉。后见外面飞沙走石,狂风大作,恐有暴雨,笑说:"你不要害怕伤心,放宽一点,迟早有救,我先去了。"说罢从容走出,将铁锁上好,关门自去。旺子体力健强,又学过武功,先听众幼童说,知道这时下面住家的那些园丁均在园中有事,除照看花木而外还要随时打扫落叶灰尘,掌管各处灯烛,有的还要轮流打更,回来极晚。园门一关,剩下都是妇孺,男的做园丁,没有工钱,全仗妇女帮着种点粮食,照看果树,忙了一天老早都睡。对方一个老年人,同伴恶奴已走,一拳打倒便可由下面角门逃将出去,松绑时节心方一动,抬头望见对方一双老眼望着自己,殷勤劝慰,辞色诚恳,没有一点戒心,暗忖:人家好意,不应恩将仇报,譬如和恶奴一样,骂完一走,绑都不解,又当如何?立将前念停止,决计凭着自己力量设法脱身。心方寻思,张升落锁关门而去,走到梯子上面还在自言自语叹气,意似他也贫苦出身,受过许多不平之气,像今天的事怎样能怪人家,就是误伤,也不应要人性命。未两句相隔已远,听不真切。
风忽然转小,跟着便有雨点打下,晃眼之间越下越大。由门缝外望,雨势甚急,昏灯影里满台皆是雨水,朝下流去。正看之间,忽然一阵风过,暴雨随着狂风由门缝中朝里打进,打了一个寒战,猛然警觉,暗忖:这样狂风大雨正是逃走机会,怎还不打主意?
念头一转,因已吃饱,又不愿吃那残食,便不去看那食物,忙将尖刀拔出,朝外一试,外层木门竟未上闩,一推便开,借着外面那盏气死风灯的余光仔细一看,铁栅建得十分牢固,铁环均钉在外面,另外还有几层铁条,小刀决弄它不动,四面试探毫无办法。
估计天已夜深,幸而雨势甚大,所有园丁均被隔断园中,无人往来。忙了一阵,打不起主意,正在为难,忽然一声迅雷,电光照处,发现牢顶有一漏光之处,因其离地太高,看不真切,看过便罢。后听雷鸣电闪之声渐密,知雨快住,天已深夜,再不想法逃走,天明之后事更艰难。正在暗中摸索,用刀去掘铁门外面钉环,一不留神,用力稍猛,竟将刀尖掘断寸许。手中只此一点脱身之具,再如毁坏,只有等死。同时又探出外面铁环甚多,就能掘掉一两个并无用处。那锁更是重大,休想伤它分毫。
旺子正在情急无计,无意之中摸到腹间暗藏的宽皮带,猛触灵机,想起洞顶一角既漏天光,必可爬出。身边还有七枝钢镖,只要能通外面便有法想。随听园门开响,有人说笑和关园门之声,料是园丁回转,天时少说也在三更左右,再不逃走更无机会,便将腰问皮带中所藏钢镖取出几枝,走往洞角,刚一抬头,便有两个电闪接连打过,这才看出离地两丈左右洞壁靠外一面有一条两尺来长的石缝,电光照处估计不会太窄,侧耳静听,下面的人业已踏水回去,风狂雨大,谁也不曾留意上面。恐人看破,先伸手出去将外层木门轻轻关好,内里越发黑暗,伸手不辨五指,急于脱身,只得暗中乱摸。
总算机缘凑巧,当地原是一座石洞,改成囚牢,四面石壁多不平整,还有好些石包石角凸出,可以攀附。靠外一面有的地方并有大小裂缝,如换旁人自然无法上去,旺子力大身轻,人更强毅,不畏艰难,先用手把下半石壁形势摸过,想好主意,再将钢镖用力插向石缝之中,拿钢镖当梯子,手脚并用,一面攀着石角踏将上去,上下倒换,居然上了一半。后来试出那镖纯钢打就,便是无缝之处也可用刀柄打穿插将进去,主意想得又巧,上来便作之字形上援,中间还遇到两处石角,约有一二尺大小,尽可落脚,越往后越容易。不消片刻手便搭到石缝出口。一试宽窄,最宽之处竟有七八寸,深约三四尺,中间上下均有锐角,幸而身子瘦小,足可蛇行而出,心中狂喜。外面那盏昏灯还未熄灭,由暗入明自更容易,便把钢镖收起,由石缝中连挤带蹭钻了出去。外面便是木台,离地虽有两丈多高,估计还不艰难,仔细想好形势,正要下去,刚把身子调转,好容易把两只脚顺向外面,腿骨在石齿上擦得生疼,裤子也撕裂了一口。
脚正悬下,忽见白光一闪,电闪也似,耳听沧的一声,好似有人在铁锁上用铁器打了一下,心中一惊,知道缩退回去被敌人知道只更吃苦,事已至此,不如硬着头皮溜将下去,和他一拼死活,来人不多仍可逃走。心中寻思,终恐敌人看破,人由上面逃出,头在里面还未钻出,被他猛下毒手,连躲避都办不到,忙把手脚放轻,悄悄乘势把全身挂了下去,双手攀着上面崖石,头刚退出,一面把手缓缓放落,一面用脚试探壁上有无垫脚之处,忽想起铁栅在内木门已关,有人开锁,木门必已开放,正好就势垫脚,只是踏空不得。又想,这大风雨,来人手中应有灯火,如何未见,也无别的声息?偏头一看,昏灯残焰明灭之下,门果往外开了半扇,只不见人,觉着方才锁响之声甚重,怎只响了一下便罢?心中奇怪,猛觉脚底好似有一突出的石块,有了落脚之处,稍微一垫便可踏到门上,轻轻跳落。忙把双手一松,身子往下一沉,因那木门无故自开,铁锁又响,心疑人已入内,只管抢先逃走,全神贯注门缝以内,别的均未留意。惊慌忙乱中似觉脚踏之处比预计低得多,并似往下沉了一沉,目光到处,再隔两三尺便是木门的上面,照此形势无须再借木门势脚便可纵落。人本机警,一见离地不高,立时变计,身子往侧一偏,便即纵落台上。觉着风雨甚大,残焰荧荧,洞口那盏昏灯已快熄灭,木门以内静悄悄的,铁栅始终未听开动。忍不住探头往里一看,铁栅上那么重大的铁锁连那寸许粗的铁环竟会被人斩断,但未打开,断锁尚挂上面,人却不见。先疑王老汉来此解救,但又不应不和自己见面。忙往四外一看,到处黑沉沉的,果林和角门旁边所住人家早已入睡,不见一丝灯光,木台上面也是空无一人。
忽想起方才由上纵落,中间接脚的崖石好似随同下沉,不像石头。借着残灯余光一照,刚看出那片石壁上下如削,并朝里缩,崖顶上面的雨水正和瀑布长绳一般大大小小朝下飞坠,因那崖顶越往上越朝前突,大量积流多未落向台上,就有几根也在离身三丈以外,打得台板发发乱响,时断时续。狂风过处,电闪明灭之中,宛如一列大小银蛇凌空飞舞,蜿蜒而下。台下积水甚深,壁上又光又滑,从出口到底哪有丝毫落脚之处!正在惊奇,疑有神助,忽又想起那瘦长子曾有答应拜师便救他出去之言,想起前事和这两人的奸狡神情,忍不住自言自语道:"这是我自家逃出,你虽将锁斩断,与我无干,说什么也不能拜你这样恶人为师!"话刚出口,隐闻黑暗中有人接口,笑说了一个"对"
字,听去不像日间所遇两人口音,忙即循声注视,昏灯已灭,天更黑暗,低呼了两声:
"你是哪个?"未听回音,知其有心相避。暗忖:天已不早,赶紧逃走还来得及,寻到王老汉求教,必能问出来历。
旺子念头一转,刚由黑暗中顺梯而下,忽听园中隐隐哭喊之声随风传来。那一面本是大片灯光,连夜不断,哭喊之声听去愈远,心疑狗子伤重,家人担心,在彼哭喊。恐老贼夫妇派人拿他出气,慌不迭纵到下面,掩往角门一看,门竟大开,容容易易逃了出去。知道此时路上不会有人,回顾对头庄中灯光隐隐,吃雨中水气一映,直成了暗赤颜色。隐闻人语喧哗,十分热闹。暗忖,这些驴日的真会享受,天已深夜,还不肯睡,不知闹些什么。人家一年苦到头没吃没穿,辛辛苦苦种成的庄稼,要被你们拿去八九成,动不动还要打骂送官,私刑拷逼关入石牢受罪。你们一点气力不出,白拿人家那许多,天天享福,还不安分,这叫什么世界!等我学成本领专和你们这些人作对,非叫你们把重利盘剥多收来的租谷全吐出来救人不可。
旺子边想边走,所穿衣服虽然单薄,又被仇敌和自己前后撕碎,一条条一片片披在身上,到处水泥杂沓,路滑难行,好些地方积水深达一两尺,仗着年轻力健,逃命心切,地理又熟,一路跳高蹿矮加急奔驰,不消多时便冒着狂风大雨赶到山口。刚一走进,遥望前途风雨中露出一点灯光,一看地势正是王老汉酒店。暗忖:此时必已四更左近,他家向来俭省,睡得又早,此时怎会有灯,分明才赶往相救,见我业已脱险,故意现身。
心正寻思,忽想起逃时匆忙,内有两只钢镖钉在壁上,离手太远,不及拔取,此镖头上有他当年暗记,传我时再三嘱咐,此镖紧藏身旁,不要被外人看出,万一有人查问,可说爹爹二十年前山东好友所赠,死后无心寻出,用来打猎,不知原主姓名,也未见过。
可见此老隐居在此,怕人知道。昔年名望又大,如被对头手下得去,查问根底,生出枝节,如何对得起人?心想:离天明还有些时,王老汉尚不知道,不如及早赶回,乘着风雨夜深将镖取回,免得惹事。略一停顿,又想前面几步就到有灯之处,好似自己住的那一间,有灯定必有人,身上又冷,还是回去换好衣服,披上一件蓑衣,朝家人招呼几句,并托向隔壁老师送上一信,再往取镖,索性逃往山中,免得连累他家。匆匆赶到一看,灯光正是自己屋内,门也虚掩,里面静悄悄的。刚冲进门,目光到处,瞥见桌上正放着那两只钢镖,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上写"孺子可嘉"四字,底下并未具名,只斜横着一条像根短棍的黑道,房中一人皆无。
旺子虽受王老汉照应,事前却曾商计,作为旺子看中当地,自立家屋,用木板树干在酒铺旁边盖了一间小木板房,上铺茅草。旺子人缘好,当地土人都说他孤苦可怜,年轻能干,有志气,谁都乐意帮忙,七手八脚,只两三天便盖成功。王老汉只在暗中相助,对外丝毫不露,作为旺子以力自给,打猎采药之余抽空读书,只在王家搭伙食,以便风雨冰雪无法人山时有个方便,省钱省事。王家在当地又是第一个好人缘,肯帮人忙,不以为奇,均料旺子沾他的光。因是有人经管,樵采所得可获善价,不致吃亏。共总一个小人,只打到两件好皮,采得一些珍药,便可过上三两月。因此粗布衣服和铺盖用具逐渐增加起来。当地民风淳朴,最喜这类勤健有为而肯积蓄的人,何况又是一个未成年的孤儿。立家之后人家见他日子过得渐好,越发同声称赞,连以前逞强欺他的药夫子在众口同声称赞之下也都另眼相看,谁也不知这老少二人的隐情。
旺子心怀大志,又得王老汉全家暗助,不是读书就是练武,真正打猎采药虽比以前减少,仗着年纪渐长,学会武功,人又聪明耐劳,不畏艰险,每出必有所获,从不空回。
王老汉再张大其词,不是旺子最恨人娶童养媳,和比丈夫年长讨来专供劳役的等夫嫂,连想娶亲都是一说即成,双方只管亲如家人,旺子日前并还背人拜了王老汉做义父,表面却是各归各,两不相干。
初意房中有人等候,及见室中只有失去的两只钢镖和一纸条,知王老汉写不出这好的字,心中奇怪。先疑瘦子所为,正拿着纸条出神,不知走好是不走好。张家哭喊喧哗之声,好似发生变故,是否与此有关也是难料。王家就在紧邻,探头一看,都是黑洞洞的,分明人已睡熟,打算换好衣服,打了包裹,喊醒王老汉,商量再走。心想今日之事义父不会不知,照他为人和本领,决不至于袖手。猛瞥见镖已插入皮带,纸条还在桌上,恐落别人手中,刚刚拿起,看那上面黑道是何用意,忽想起师父腰间铁笛子与此相似,当时醒悟,心中狂喜,脱口喊了声"师父",刚关好的房门忽然无故自开,跟着人影一闪,对面一看,不由大怒,原来那人正是玉泉崖上所遇叫老三的中年人,左手还用麻线穿了一串人耳走将进来。
旺子虽然料定当夜之事与这两个对头有关,因已悟出先失钢镖下面所压纸条所画黑道乃师父铁笛子所留暗记,心便有了把握。再见来人面带诡笑,神情鬼祟,手上人耳约有六七只,鲜血淋漓,还未被雨水冲净,点点下滴,分明这一会的功夫被这两个恶贼杀死多人。就算所杀乃是张家父子,自己的对头,这等残忍凶恶的行为也是头次看到。又料来人决无好意,忍不住气愤愤问道:"深更半夜,我共总这一问小屋,向不空留外人,素不相识,寻我作什?"旺子早看出对方本领比他高得多,真要有什恶意,非吃他亏不可。偏巧回来晚了一步,师父业已离去,途中未遇,不知走往何方。
先想王老汉全家均是极好武功,一呼即至,故意高声喝问,还有一点仗恃。话刚出口,瞥见来人一脸狞恶、狡诈神情,一双贼眼正望着自己的的放光,猛想起王老汉翁媳最是义气,新来伙计表面老实,实则是他义父老友之子,为避仇家来此隐身,本领也非弱者。就算日里被擒走过时他们不曾看见,见我到夜不归,也必寻人探询。山口内外居民十九眼见,到处传说,王家断无不知之理。照他为人和平日口气,不应置之度外,如何他里外两旁房舍这样又黑又静,不见一点灯光,若无其事,于理不合。这两个对头十分凶狡,日里相遇又曾探询过他翁媳的姓名来历,语多可疑,莫要这两人便他平日所说的那些对头,心有顾忌,虽在暗中相助,自家却不出面,也许师父就他请来都不一定。
事情哪有这样巧法,终日苦盼,渺无音信,刚被恶人擒去,快要打死,人便赶到。
再一想,由崖洞上面逃出时似有东西把脚托了一下,如是师父,崖壁又凹又滑,刀切也似,没有附身之处,师父人矮,其势不能凌空而立,决够不到。既来救我,定必见面,不会连喊不应。义父身材高大,定他所为。本意救我,因恐对头知道,又见人已出险,恐我泄漏机密,先自避去。照此形势,义父必有深意,连这盏灯都未必是他所点,否则我由外逃回不会不知,如何不来相见?本来对头还不知他来历,我一喊人,反而泄漏他的机密,怎么对得起人?本来人如非真个厉害,凭义父那样人,我这样高声说话,也必有人赶来,还是谨慎些好。心中一惊,生出顾忌,越发有些胆怯,无奈话已出口,只得把心沉隐,口中说话,一面留意对方动作,手叉腰问,看好房中地势,准备对方动武便先下手为强,与之一拼。
旺子正在暗中发慌,硬着头皮发话,来人乃是北直隶有名的恶贼李文玉,因其眉心有一黑痣,外号三眼花狼,人最凶狡,进得门来听旺子发话拒绝,直如未闻,先把那串人耳往桌上一甩,回手脱下身穿油绸子雨衣雨靠,还算客气,未在旺子房中糟蹋,自己拿向门口连抖两抖,把上面所积一点雨水抖去,拧了一拧再行抖开,呼呼两声便复原状,把雨帽歪带头上,雨衣靠往左腕上一搭,大模大洋走向桌前,把桌上茶壶拿起,用碗斟满,一饮而干,再回转身,一屁股坐在桌旁炕上,取出怀中一枝头尾都是上等翡翠镶金的象牙小烟袋,装上烟丝,就油灯上点燃,也不答理旺子,一口气连吸了两袋。旺子见他反客为主,目中无人,那等狂傲自大模样,越发有气,又知对方不是好惹,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问了两次全都不理,不敢伸手硬拉,估计先后两次大声说话,就义父未回,王家二嫂也必惊动,便新来伙计丁十二也应听见,怎会全无动静?自己由张家逃出已有不少时候,想和王家翁媳商量,探询师父人在何处,以便寻访,又在房中耽搁,幸而离明尚早,风雨未住,如在平日,若被仇敌发现,早就追来。天明以前不问寻到师父下落与否,均须逃往山中。这厮偏这样赖皮,不打发他先走决不放心,又不知他是何来意,不禁又气又急。想起王老汉平日警告,不敢发作。
正在无计可施,打算用话激将,试探来意,李文玉把两袋烟吃完,把金烟袋斗上烟灰磕去,从容放好,揣入怀中,望着旺子,嘻着一张贼口,冷冷地笑道:"你这孩子讨厌我么?如不是我和你五大爷,你虽逃回也难安身。天光一亮,你那张家对头必要寻来,这房子暂时虽是你的,你准住得成么?我们好心好意想要救你,怎的不知好歹?本来你这类野孩子我看不上,只为你五太爷爱才,见你小小年纪这样胆大机警,真有骨头,居然不要人帮忙,自家逃走出来,总算难得,彼时我正将张家父子连他手下那些王八蛋一齐制住,本不容他活命,五太爷心软,因张家狗种虽然得罪咱们弟兄,老的还好,以前并且帮过咱们的忙,被五太爷无心认出,这才由他出面做好。如今事还未完,正和张老头商计,因知你已逃走,风雨太大,恐你年轻胆小,逃命心慌,半夜入山遇见危险,托我先来把你喊住,就便问你几句。五太爷说,你果然自己脱身,没有靠人,虽然另外有人把铁锁斩断,你已由上面洞中逃出,这个忙并未帮上,你肯不肯拜他做师父由你的便,非但不会勉强,就你将来知道好歹,回心转意,想要拜师,他也未必容易答应,这都不提。我李三大爷一向看不起人,何况你这样一个又穷又脏的野孩子,全因你五大爷跟你不知哪世里的缘法,会看得你太好。我也觉着小小年纪,居然会这样有骨头,才活了心。
我问你话,这是格外赏脸,必须恭恭敬敬实话实说,再像方才那样口出不逊,你三太爷一有气,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旺子听出二贼果在张家大闹,那许多恶人爪牙均被制住,还割了好几个人耳带走,本领之高不言可知,照此口气似未存有什么恶意,素无仇怨,自己年小,本身或许无事,甚而连张家对头也被吓退,就是天明发现人已逃走,都不致赶来作对,才会这等说法。
不过所问的话决非寻常,必与师父和王家有关,一答不好便要使人受害,看神气既不会伤害自己,怕他作什?心中寻思,一面静想,一面静听,听完之后,因气愤对方无理,也把板凳往门旁一拉,对面坐下,一面把草鞋脱下,用手搓着脚指头,故示傲慢,冷笑答道:"你这人好无道理,素不相识,共只见过一面,还是我请的客,一不该,二不欠,大风大雨深更半夜无故闯入人家问三问四,仿佛你比主人还要随便。开口不是三太爷,就是五大爷,便你真个年高有德,也要人家自己对你恭敬才有意思,这等自言自语,自尊自大,我认得你是谁?不错,那叫老五的老汉曾叫两个小娃把我失去的鸡送还,并想收我为徒,我不愿意。后来他在外面崖上偷听,我已说好,逃不出去是我该死,与他无干,宁死也不要他帮助。无故派你来此是什意思?如说张家那些恶人被你们制住,不会再来害我,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又不曾托付,事前并还言明,真是这样也不承情,何况张家有财有势;当时打不过你们,明日报官,到底如何还拿不定,岂能以此居功?你两个既然自命英雄,比谁都高,想必不会倚仗凶威势力,欺负一个比你们年纪小两三倍的小娃。真要气我不过,是好的不必等我多久,只等个三年五载,我年纪稍长,学成本领,照你今夜所为,比那老五还要可恶,你不寻我,我也寻你,到时我打你不过,被你杀死,决不皱眉。如在此时欺人,只不怕脸皮厚,或杀或打也由你便。我旺子从小孤苦,能够长大全仗自己手脚和心思,你刀架在我头上也吓不退。我嘴太刻薄,你越发狂我越气你,这是何苦?
"本来人在世上,原应彼此互助,不论穷富都是一样。有钱人仰仗我们苦人的地方只有更多。谁都有个不便时候,休说问问人,问什事情均应直言无隐,尽自己的力气去帮为难的人,那才叫是好汉。问几句话有什相干?换了别人,这样风雨深夜无处投奔,望见灯光寻来,人之常情。我旺子虽穷,向不小气。家中别的没有,多少还剩两块麦饼冷馍,一点盐菜,水更现成。这炕不大,睡上三四个人足能挤下。休说问话,便请你吃,请你住,也必好好待承。像这类半夜里望门来投的人,十九都是没有什么钱的出门人,光景就比我好也都有限。真有钱的老客早住店去了,怎会投我?算起来都是我的同等弟兄、叔伯大爷,我一个人独居无聊,来了外客只更高兴,请还请不到呢。像你们两个,老五虽是老奸巨猾,说话还极和气,居然看得起我,更是难得。像你第一次见面,我先恭恭敬敬当你好人叔伯看待,你先欺我人穷年幼,骂了我的师父,还要骂我,样样蛮不讲理。
"实不相瞒,日里玉泉崖上直到现在两次相见,如非人小力弱打你不过,早就和你一拼高下了。就你日里可恶,方才进门时稍微客气一点,来者是客,我也不会有气。照你这等行为口气,实看不惯,我已恨极。无奈我是小娃,你是大人,硬要赖在我的炕上不去,还闹了我一地的雨水烟灰,真太气人。我这叫恨在心里,无可如何。我这人虽不会说假话,但最恨你这样凶狂的人。随便问我什话,我决不高兴回答。再说,我又没有应该回答的道理。我做的事不问乱子多大,也有我自己抵挡,不必你们费心。算我怕你是个瘟神,你那一串人耳朵吓不倒我,看去只有讨厌,最好请走。你如走往门外不再扰我,有什话问也许凭我心愿回答一两句。再如扰闹不去,我拿你无法,看了你又心烦,情愿让你。总算你是英雄好汉,会以大欺小,把人家房子霸占了去,逼得主人这大雨天连自己家都不能住,你真要不怕人笑话我马上就走。要想倚老卖老,行凶逼人,休看我一个孤苦无依的幼童,一句也不会听你的。"
旺子人甚聪明,早留心对方神色,见他始而浓眉倒竖,似要发火,眉心一粒黑痣也在颤动,以为要糟。因听隔壁没有丝毫动静,越料王家顾忌来人,不敢出面,对头所问的话也必与他有关。本就情急负气,见状不由激发刚直天性,怒火往上一撞,话更难听,满拟对方必要恼羞成怒,事已至此,怕也无用,又从心里起发生厌恨,怎么也忍不住,边说边在暗中准备,假装抓痒,手插腰袋夹缝之中,以防万一动手,乘着坐近门口,又有桌凳阻隔,稍见不妙,下面抬腿把桌子踢飞,朝炕上敌人打去,同时上面右手三枝连珠钢镖,左手抄起板凳横扫过去,再乘忙乱中出其不意身子一侧一挺便可夺门冲出,好逃向外面。敌人在张家杀伤多人,如能将其打死,正好以毒攻毒,非但本身可以无事,还可为民间除去一个大害。如其打他不到,这等下手多少也必负伤,等他追出必有一点耽搁。这大风雨,对方路径又生,黑暗之中多大本事也使不开。主意打定,话更刻薄。
正说得起劲,忽见敌人浓眉放平,二目凶光尽敛,回复原状,二次掏出镶金翡翠象牙烟袋,重又从容就灯点吸,面上笑容也与方才不同,目注自己,将头微点,身子靠在被褥上面,脚登炕沿,搭上一条二郎腿,神态比前更加安静,一任嘲骂,若无其事,看出不像激怒。前凶后和,用意难测,正觉奇怪,李文玉又连吸了两袋烟丝,口吊翡翠烟嘴,似想什事神气。先是一言不发,直到听完,略停了停,方始笑道:"我真作兴你一个小孩会有这大胆子,如说无知也还罢了,你偏什么都知道。从见面起一个大人未遇,也无一个指点,竟会看出我们本领。表面说话气人,句句先把我僵住,使我干生气,不能与你一般见识。我和五太爷曾向多人打听,均说你从小孤苦,独居在此,从未有什师父,也未见人教过武艺,只有一个教书的穷酸,你跟他学认点字,铁笛子三字更无一人晓得。这厮一向形踪隐秘,不知怎会被你看出,想拜他为师。据你说只见一面,所说也似不假,竟会断定他要收你做徒弟,不谈出一点意思不会这样拿稳,此已奇怪。最难得是你想拜他为师,以及平日背人学武,山口内外这许多人都夸你人好聪明,能干耐劳,有志气,你的心事竟无一人知道。
"我三太爷三眼花狼李文玉向来杀人不眨眼,竟会被你僵住,挖苦了我一大顿,无法出气。这样刁钻古怪、有心眼、还有主意、不大点年纪的孩子从未见过,无怪五太爷见了直说可惜来迟,事前不曾发现,被对头得去,此时连我三太爷也对了心思,何况别人!休看骂我,因你狡猾口巧,反觉对我脾气,我已决计不再伤你。照你这样人,我料铁笛子必肯收你为徒,可惜他至多活到重阳节前,也许就这几天便要送命,辜负你一番苦心罢了。我情愿向你认错,以前不该当你穷苦野小孩看待。你师父虽是咱们对头,我和你总算没有过节,借你这地方歇歇腿,喝碗茶,抽两袋烟。好在你那张家对头因五太爷一说,更不敢寻你晦气,无须逃避。咱们聊上几句,谈上一会,总可以吧。"
说时,旺子听那人忽改和王老汉差不多的北方口音,与日里所闻杂音不同,便留了心。先料十九翻脸,及见说完无事,反倒转了口风。因对方神态举动始终狂傲,头枕在自己所堆被褥上面,脚登炕沿,二郎腿跷起,辞色虽转平和,还是那么自高自大,旁若无人。心想,这厮头倚被褥,背朝窗槅,此时无论何人,只由窗外一伸手便可要他性命,他却大模大样,口发狂言,说师父不久死他手内,照这样粗心骄狂决无此理。猛瞥见破窗格上有一人手微摇,定睛一看,正是义父王老汉,似在窗外窥听了好些时候,正朝自己摇手示意,立时警觉。暗忖,对头如无本领,怎会发此狂言?义父平日说得师父简直飞仙剑侠一流,这两贼却如此看轻,他翁媳那高本领,竟不肯出来相见,必有原因。我如何这样大意?因恐对方警觉,不敢多看,借着拔鞋把头微点。抬头再看,窗外人已不见,知道老汉意思,不令得罪来人,也不令逃入山内,心越放定,立转口风,笑道:
"你这样说法,便算来客,我怎会说不好听的话?只我知道,你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