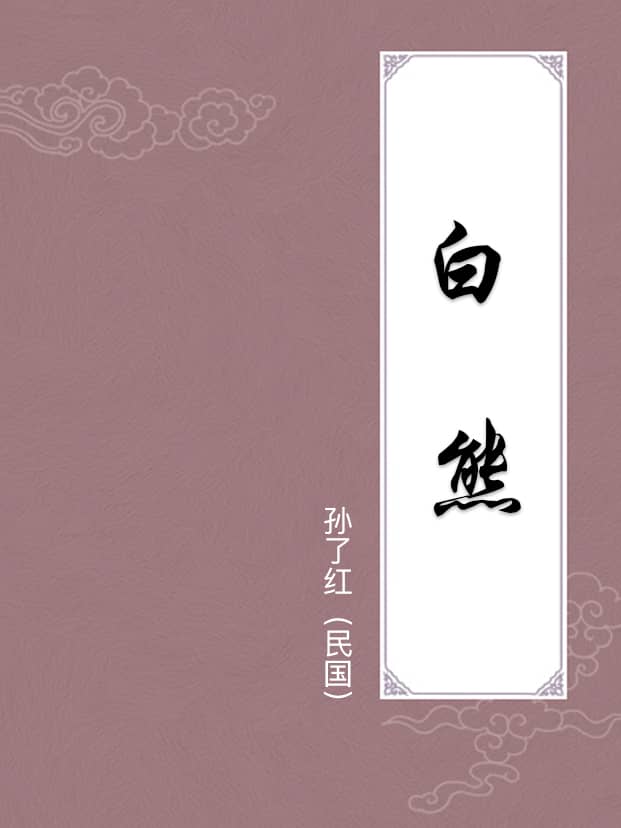在这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时代,那神妖鬼怪的说数,久已不成了问题。因此,我对于黄叶路博物院的白熊案,始终非常怀疑。
当时,我被好奇的欲望行动着,觉得不打破这疑团,心里终有些介介。
一天,我专诚到黄叶路去,访那博物院的管理人,要求他把失去白熊标本的情形,细述一遍。预备在那管理人口中,寻些线索出来,然后再设法,剖解这一件不可思议的奇事。
博物院的管理人,年近五十,从外表上看起来,却是个很诚朴的人。他一听我提起“白熊”二字,面上顿时添了一重惊怖的颜色,嗫嚅道:“此事发现以后,就有许多新闻记者,接连不断的来问我。我已把详细经过,据实向他们说过,你不妨随意买一份报纸看看,便可知道……那件事真是可怕得很,一想起就令人战栗,我委实不愿意再提一字咧!”
我道:“报上的记载,我都已看过;不过我以为你亲口的演述,比较的终详细可靠一些,因此我想要求你再说一遍啊!”
管理人被我逼迫着,很不愿意的点了点头道:“再说一遍,也无不可,只是事情太奇怪了,说出来时,恐怕你也未必见信啊。”
我道:“决不如此。”说着,便燃了支烟,一壁吸,一壁静待他发言。
管理人道:“这奇事最初的发现,在三个月以前。其实这白熊标本,陈列在本院,还不满二星期。我素患失眠症,往往通宵不能入梦。有一夜,两点钟以后,猛听得楼上发生重大的声响,好像有重物坠地。我非常奇怪。暗想楼上只陈列着些标本古物,并无人住,这是哪里来的声浪呢?于是我就披了衣服,取了怀中电炬,上楼查看。
“开门进陈列室,四面看了看,一时也找不出什么变动。我还放心不下,仔细看时,却看出破绽来了。原来,这白熊的标本,本来是和一只猩猩,面对面陈列着的。此时不知何故,那白熊变成背向猩猩了。当时我虽觉有些奇怪,不过还以为偶然被人移动。所以并不十分注意。后来我就锁了门,下楼安睡。
“谁知距离此事二星期以后,半夜里楼上忽又发生地二次的响声。我照旧拿了电炬,上楼查看。这一次走到半楼梯上,忽听得有一种琐琐碎碎的声音,在陈列白熊标本的那间屋里发出来。我情知里面一定有特殊的变故,上楼时,急忙开了电火的总机钮,一壁匍匐着身子,在锁眼中张望。哪知不看忧可,看时,吓得我毛发都竖……先生,你试猜猜,那时我看见里边,是什么情形?老实说,直到现在,那可怕的印象,还深印在我脑海里,一闭眼就能想像出来……”
管理人说到这里,顿时露出一种惊悸不安的样子。
我催他道:“看见什么可怕得情形呢?快说啊,是不是那白熊……”
管理人接口道:“不错,那白熊……原来已离了原有的木座,直立在室中央,张着血盆似的嘴,在那里舞蹈。”
我听到这里,方知报上的记载,并不是过甚其辞。暗想:“难道世界上真有这种怪事吗。”想着,不免也有些惊异,于是就问道:“这事情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见过吗?”
管理人道:“没有,因为一到晚上,院中只有我一个人啊。”
我道:“以前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人家呢?”
管理人道:“这种神秘的事情,告诉人家,谁肯相信!况且第二天,那白熊依旧站在木座上,并无变动的痕迹。就是要告诉人家,却用什么证据,证实我的说话呢?”
我一听,觉得不错,便问:“以后如何?”
管理人道:“从此以后,并不曾再发生特殊的事情。不过六天之前,这白熊的标本,突然不见,失去的时候,当然在前一夜的晚上。不过那夜并无声响,到第二天早上,方才觉察。另外又失去一柄古代匕首,却是放在一架锁着的玻璃橱里的。事后,我们四处检查着,毫无迹象可寻,你想可怪不可怪?
“据说,我们院中失去白熊的那天晚上,黄叶路口,有个岗警,偶然回头,却见距离他二三丈远近的电杆木旁,有一个遍体雪白的怪物。借着路灯的光线,仔细看时,却是一只高大如人的白熊,形状十分可怕。
“那警士正待惊喊,蓦地脑后被重物猛击一下,顿时晕去。后来幸亏有走夜路的看见,连夜把他送进医院,伤势虽然无碍,却因受惊过度,神经上已有些错乱。听说现在尚未出院咧!这一节事情,报上记载得非常详细,你大概总看见过,只不知你对于这种不可究诘的怪事,究竟作何见解啊?”
管理人说完了一席话,忒愣愣地望着我,好像要等我发表些对于此事的理解。
其实我当时脑海里,愈弄愈乱,简直毫无头绪,只索很扫兴的从博物院里走了出来。
一路上想:“我自己脑筋太简单,万万不能透解这种神秘的问题,不如去问吾友鲁平。鲁平思想既好,又有惊人的观察力。他不遇见难题便罢,遇见了是无有不打破的,不知他对于此事,是否注意?倘使也注意着,那末,内容如何终不愁没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因此我回家之后,忙打电话给鲁平,预备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告诉他。
谁知鲁平刚听了几句,就在电话中扬声大笑道:“得了……徐震……别再往下说吧,这种三分钟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值得大惊小怪,改日等我替你剖解,现在实在忙得很,请你恕我不多谈咧……”
说毕这几句,不等我在再问下去,电话已经摇断。铃声一阵大响,好像把我送进了五里雾中。细味鲁平那种轻描淡写的语调,似乎黑幕里的事情,他都知道,这真是不可思议中的不可思议了。
从此以后,我便不再把白熊的事情,挂在心中,专等见了鲁平,问他详细。可是鲁平为人,行踪飘忽无定,我一连等了好几日,终没有遇见他的机会。
其时社会上对于白熊一事,沸腾的声浪,已逐渐低减,我脑筋里的疑团,差不多也要自然消灭了。
一天晚上,时候大概在十二点左右,我在朋友家里,玩罢了纸牌,回转秋云街的寓所。这条街白天也很冷僻,晚上更是幽静,半里路内,简直找不出一个人影。
我回家之后,觉得卧室里很沉闷,急忙开了靠街的楼窗,预备容纳些新鲜的空气。此时,自然界中,什么都沉寂了。仰望长天,黑得像涂了重墨,几颗孤星,却是闪闪烁烁的,发着半明不灭的光。
我一瞧对面的楼窗里,电火还没有熄去,光线射在洁白的窗帏上,分外觉得耀眼。
其时我伏在窗口上,很无意识的望了一回,便想关窗安睡。陡然见对街楼窗的窗帏上,倏的闪出一个影子。那影子既不像人,又不像兽,不住的晃动着,好像在那里跳舞。再看那怪影,手里还握着一件东西,又好像是一柄短刀。
我一见这短刀,顿时联想起那不可思议的白熊案来了。
我一壁凝想着博物院管理人的一席话,一壁注视对窗的怪影,觉得越看越像是一只熊。正自惊疑着,只见对窗的电火,忽然熄去,一刹那间,什么都不见了。
我定了定神,急忙走到电话机畔,把所见的怪事,一五一十,告诉鲁平。鲁平在听筒里露出很兴奋的口气,道:“有这种事吗?这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现在你且守望着对窗,看他再有什么动静,我立刻就来……”
我答应着,鲁平又问道:“对面楼外,有洋台没有?”
我道:“有的,你常到我这里来,难道看不见吗?”
鲁平道:“我的记忆力太坏,想不起来咧。”说完,一阵铃响,电话便摇断了。
我伏在楼窗上,约摸守望了半小时,对窗毫无动静。路上远远里却来了个黑影。那黑影越走越近,一看,好像是一个短衣窄袖的工人,背上还负着个袋。
那人走到我楼下,突然咳了声嗽。
我一听声音,知道是鲁平,忙下楼去开门。
鲁平站在街心,却不进来,问道:“有什么变动没有?”
我摇摇头说:“没有。”
鲁平道:“你把自己的门带上了,快跟我来。”
我道:“做什么呢?”
鲁平沉下面色道:“我们一同打猎去啊。我的料想,倘然不误,管教那作怪的白熊,进我的圈套啊!”
鲁平说着,向街道的两头望了望,只见并无人影。于是放下背上的袋,伸手进去摸出一圈绳子,绳的一头,有一个铁钩。鲁平握着那铁钩,用力向对街洋台上掷去。
这时,我心里很怪他太大意,暗想:“铁钩的声音,惊动了窗中人,可不是玩的。”
哪知钩子掷上去,并无巨大的声音,只一掷,却已挂好在洋台栏杆上了,这种敏捷的手术,真令人不得不佩服。
鲁平挂好了绳,低声问我道:“徐震,上去啊!”
我本来学过绳技,要我上去,并不难,可是想着方才的怪影,不免有些胆怯。
鲁平微笑着,似乎已知道我的心思,便先缘绳而上;随后我也从绳上爬上了洋台。
鲁平把绳子收好,又在袋里取出金刚钻,把那法兰西式长窗的玻璃,割破了一块,打窗框里探手进去,去掉窗闩,顺手一推,那窗便开了一扇。
我在一旁,看着鲁平这种从容不迫的动作,不免暗暗赞叹,他的贼学高明;一壁心里奇怪着:“难道这间屋里,此时竟没有人吗?方才的怪影,又到哪里去了呢?”
我一面想,一面跟着鲁平,进了长窗,顺手把窗推上。只见里边黑漆漆的,一些看不出什么。幸亏鲁平,又在他那包罗万象的袋里,摸索得了手电炬,四面一照,却是一间卧室,陈设简单,并无一人。
鲁平指着室隅一个沙发,低声向我道:“为了这一件很小的事,倒累的满身是汗,我们姑且小坐一回,吸一支烟,休息休息吧!”
说时取出两支烟来,授了支给我,擦了火柴,很自然的吸着,好像坐在自己家里一样。
我忍不住问道:“坐在这里,干什么呢?万一屋主人突然进来,见了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不是要惊喊起来吗?”
鲁平道:“别则声,稍等片刻,便可以满载而归,决不至于白等的。”
其时,我们默默地坐在黑暗里,觉得室中的空气沉寂,以及二人的呼吸声,互相可以听见;壁上的钟摆,却很有程序的响着。如此过了一回,鲁平忽把我的衣角一拉,凑近我耳朵道:“来了!”
我凝神一听,果然觉得有很轻的脚步声,在室外楼梯上,走上来了。脚声渐渐走近,一回儿,好像已进了屋子。
这时我的心房,不由得剧烈的震动起来。同时电火,“刷”的一亮,通室光明。睁眼看时,只见室中已多了一个人,矗立在我们面前。那人身材很长大,也穿着短衣服,手里拎着个黑布包,目光灼灼,一望而知是个很狡猾的人。
他一见我们,惊的倒退了几步,一时竟开不出口。
鲁平冷冷地向那人道:“朋友……回来了吗?辛苦得很,事情大概总很顺手啊!”
此时那人神色渐定,厉声向鲁平道:“你是什么人,半夜三更,到人家里来做什么?”
鲁平学着他的口气,微笑道:“你是什么人,半夜三更,到人家里去,做什么啊?”
那人觉得鲁平的语气不善,不免着了慌,一手徐徐伸进衣袋,似乎要摸什么东西,一时却又摸不出来。
鲁平冷笑道:“朋友……安静些的好,是不是要找一件兵器呢?我倒现成带着,借给你,你要不要?”说时,很迅速地取出一支手枪,指着那个人胸部。
那人见鲁平,态度自然,一时竟猜不出鲁平是何种人物。但是一股勇气,已渐渐消失,差不多要屈服了。
他囁嚅道:“你……你到底是谁啊?”
鲁平不答,在怀中取出一张名刺,授给那人。
那人接去一看,顿时面色大变,一手按着额骨,颓然倒在一只椅子里。看他这种态度,已完全表示服从。
过了一回,那人一壁拭着额上的汗珠,一壁用很柔婉的声气,问鲁平道:“你的来意,要多少呢?”
鲁平道:“这却并无成见。总之,你今天在外边,得到多少,我们均分,好不好呢?”
那人一听,满面露出不愿意的样子,勉强答应着道:“很好!”说着,便在衣袋里摸出一叠纸币,检出一半,交与鲁平。
那时我看着他们这种奇怪交涉,觉得莫名其妙。
鲁平揣知我的意思,指着我向那人道:“我这同伴,今夜特地跟着我,到这里来,参观我们表演这一场活剧。不过他对于剧中的情节,还完全不明了,我想请你把今夜的事情,简单些说一遍,你愿意不愿意呢?你不愿意,我不妨代劳咧!”
鲁平说着,又燃了支烟,吸了几口,继续说道:“二星期前,本部各报,都沸翻扬天的,载着那黄叶路博物院白熊作怪的事情。这事情的内幕,至今社会上还没有人能够揭破。”
鲁平说到这里,把那人的肩膀一拍,续道:“这位先生,便想利用那诡异的神话,实施他那劫掠的手段。今天晚上,他在这里,扮好了白熊,自己先对着镜子,预先试演了一回,觉得成绩很好,于是就熄去电灯,悄悄地从后门出去……中间实行劫掠的一幕,我不曾看见,恕不乱说……以后就是现在这一幕,我们三人一齐在场,也不必细说咧!”
我听到这里,方始恍然大悟道:“嘎……原来我刚才看见的窗中怪影,就是这位先生扮演的大套戏法啊!”
鲁平点点头,随即用吩咐仆役的口气,命那人一同下楼,开了门,送我们出来。
鲁平到了我家里,坐定之后,我问道:“今天的疑问,总算打破了,可是博物院里的白熊不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觉得愈弄愈糊涂咧!”
鲁平笑道:“这个闷葫芦,在你胸中,横梗了好些时了,等我老实告诉你吧……有一天,我带着小平(鲁平之子)到博物院去参观回来时,小平便闹着要那白熊标本。他说我从前许他一个活动木人,不曾给他(事见拙作《东方亚森罗苹案——傀儡剧》),此番非买这白熊给他不可。可是博物院的陈列品,又不肯出卖的,我被小平闹得没法,只好晚上悄悄地去把那白熊偷了回来。”
鲁平说到这里,我笑道:“好,好!你真不愧是个孝子。”
鲁平道:“你别取笑,世间的父母,为了儿女,做贼做强盗的尽多着,不但是我一个啊!”
我道:“照你这样说,白熊不见,是你弄的神通,不足为怪。那末,博物院的管理人,亲眼看见白熊跳舞,却是什么缘故?”
鲁平拍手笑道:“这种无稽之谈,你竟信以为真吗?足见你的脑筋,和社会上许多笨伯一般的简单啊。老实对你说,那管理人因为院中一无动静,突然不见了这么一件笨重的标本,自己也觉得没有交待。恰巧第二天,听见有个警士,半夜里见过这白熊,并且被重物打了一下,于是他就借了这一点因由,造出一番谣言。一回儿说白熊换了方向,一回儿又说白熊居然会跳舞。他的用意,无非想捣一阵鬼,掩饰去管理不周的罪名罢了,自己何曾看见什么呢?”
我道:“那末黄叶路口的岗警,看见白熊,难道也是撒谎?”
鲁平道:“那警士倒并非说谎,原来我在博物院中,负着白熊的标本出来,见这警士,立在路口。我恐怕被他看破,于是把背上的白熊,放了下来,靠在一根电杆上,一面我却抄到这警士背后,趁他回顾,将他打倒在地下。他当时虽然看见这白熊,不过一瞥之间没有看清楚,是死的,是活的,醒后告诉人家,却说得神气活现,听的人自然分外觉得可怪令人……
“还有一柄古代匕首,和白熊同时不见,事后,人家谈论起来,总说是被那白熊摄去的,其实也是我顺便拿的。方才电话里你告诉我说,看见一个怪影,握着短刀。我起先也觉得可怪,后来仔细一想,就疑惑又有人借着白熊作怪的梦话,在那捣鬼了。不过还不敢十分确定。直等到我们守着了那人,见他手里的黑布包内,露出半只白色的兽爪,那时我的料想,方始完全证实了。”
我听完了这一席话,不由笑道:“一场郑重其事的怪事,结果只是如此。”
鲁平道:“世界上的事情,哪一件可以认真?拆穿了,都不过如此如此啊。只是你的笔记,又多了一节新颖的资料咧。”
我道:“资料确乎很新颖,只怕记出来时,要妨碍你的信用。你以前曾经宣言,无论如何,不用手枪;今天为什么拿手枪威吓人家呢?”
鲁平一听,跳起身来,摸出那支手枪,一拆拆作两段,一段向我一掷,狂笑道:“吃手枪吧。”
我一看,原来是一块手枪形的可可糖,外面裹着一层锡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