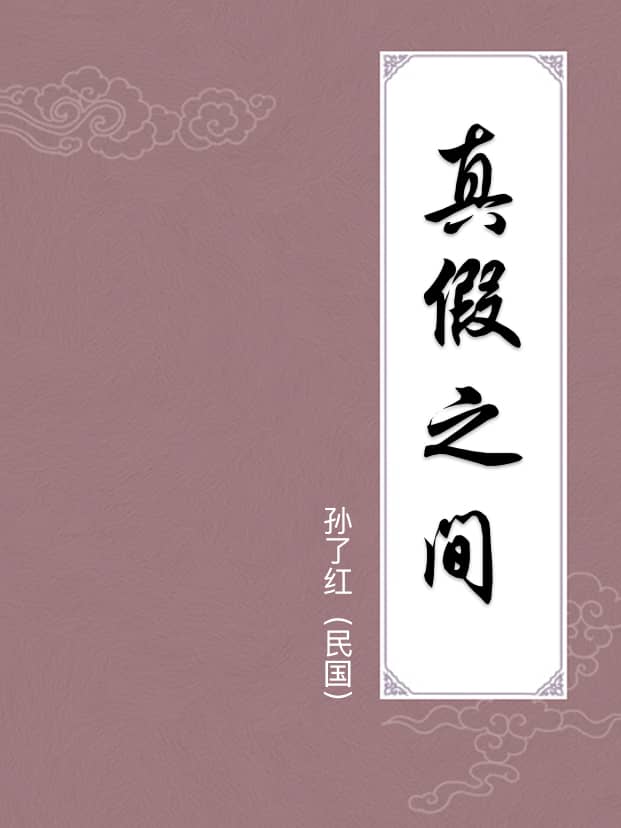去年圣诞之夜,我曾被一个消闲的集会,邀去说故事。他们跟我约定,在今年的同一夜晚,他们仍旧要我担任这个节目。凑巧得很,我在说事的时候却又意外地获得了故事的资料;本来,我预备留下这点资料,以便今年践约;但,我自己知道我的脑子,有个健忘的毛病,我觉得演讲而备一份演讲稿,在气派上比较来得大一点,因此我便提前把它写上了原稿纸。假使今年能有机会,我就预备把后面这段离奇的事情,当着某几个角色的面,亲口再说一遍。
这一年的圣诞之夜,老天爷虽然没有制造雪景,为富人添兴,但是天气特别冷,那些时代的骄子们,血旺,脂肪多,他们在各种暖气设备之下,可以通宵达旦,追求狂欢。但是,无数无数被时代作践着的人,衣不暖,食不饱,眼前缺少希望,心底全无温意,他们无法抵御酷寒,他们也没有那种傻气,希望圣诞老人真的会把白米、煤球装在洋袜子里送上门来。到夜晚,他们只能在叹过了几口无声的冷气之后,缩住脖子,早点到梦乡里去寻求他们所需求的什么。
在同一的银灰色的都市之中,有着不同的两个世界,待在三十三层以上的人,还在挤电梯,想上楼;而在第十八层以下的人,也还被迫地在钻泥洞,往下埋!由于贫富苦乐得太不均匀,毕竟也使这个异国带来的狂欢的日子,显出了异样的萧瑟。
时候快近十一点钟。
一钩下弦月,冻结在大块子的蓝色玻璃上,贫血,消瘦,显得绝无生气。惨白的月色抹上那条寂寞的愚园路,静静地,像是一条冻结的河流。
这时,有一辆小型汽车,在这条僻静的路上轻轻滑过,车子停在愚园路与忆定盘路的转角处,隐没在一带围墙与树叶的黑影里。
小型汽车中坐着两个人,坐在驾驶盘前的一个,是个胖子,西装不太漂亮,样子有点滑稽;另外一个,高高的身材,穿着一件美国式的华贵的大衣,帽子是阔边的,带着一种威武的气概。
这个身材高高的家伙,跳下了汽车之后,取出一支烟,擦上火,斜挂在口角里。他向对街的路灯光里一望,只见对街已预先停着几辆汽车。其中之一辆,是一九四七年的别克,崭新的车身,美丽得耀眼,汽车夫拥着车毯在打盹。
高个子的家伙注意了一下这辆车子号数,脸上透露出一丝满意的笑,他低下头来,向驾驶座上的那个胖子说:“好,真的,小熊猫也来了。光荣得很!”
胖子在车子里把衣领拉拉高,哈着热气,问:“你说的是谁,是一个女人吗?”
“不错,老周,你猜着了。”高个子说:“那个女人很美,跟她握一下手,可以羽化而登仙。”
那个胖子耸耸肩膀,说:“那么,能不能带我进去,让我登一次仙?”
“不,你还是耽在车子里,说不定,一忽儿我就会出来。”
高个子说完,站在冻结的月光之下,整整他的鲜明的领带,把双手插进大衣袋里,匆匆向一带很长的围墙那边走去。
围墙之内,是一片园林,面积看来并不太小。冬季法国梧桐的秃枝,参差地伸展到了墙外,有些高大的长绿树,黑茸茸的树叶,却在墙外的人行道上,组成了大块的暗影。园子的中心,有一宅高大的洋楼,沉浸在寒冷的月光里,格外显得庄严而静美。
西北风在传送着屋子里隐隐的欢笑声。
这座外貌古旧的屋子,过去,它曾有过不太平凡的历史,最早它是俄国人的总会,以后它曾变做豪华的赌窟;沦陷时期,它曾被侏儒们占据而煊赫过一时;胜利初期,这所屋子又被改造成了一处科学食品厂。但在那个时候,美国货正如潮而至,到处冲毁了国产品的堤坝,不久这屋子却又随着厂的倒闭而赋了闲。而在今晚呢,这座屋子里,却有一个有闲者所发起的圣诞集会在举行。
一切热闹的节目在两小时以前已经开始。
主持这个集会的角色共有三个:其中的两个,就是这所厂屋的主人。那是一对弟兄,哥哥名叫庄承一,被称为大庄,老弟名叫庄承三,被称为小庄;另一主角倪明,是一个广告业的巨子,而同时,又是一位驰誉于这银灰都市中的美术家。
这位青年俊秀的美术家,喜欢向人诉说,他生平并无癖嗜,唯一的嗜好就是开派对。他曾自夸,他生平所主持的派对,大小计有三十余次之多,他敢向天盟誓,假如有人参加了他的派对而感觉到并不愉快,他愿意吞服来沙尔,以自罚他的溺职之罪。
的确的,倪先生的自白,并不是真空管里的一只牛,他主持这个圣诞夜的集会,已有三年的历史,今年却是第四次。看来今年的一次,比之往年可能格外够劲,原因是,大众震于派对专家的威名,参加者越来越多。尤其今年的参加者,男的,大半很富有的;女的,大半很浪漫。钱,能够产生闲;闲,能够产生新奇的玩意。有钱,有闲,加上有女人,在这种算式之下,这个集会会不精彩吗?岂有此理!
一切布置都出于我们这位专家先生的大手笔,会场设在一座广厅之内。这座广厅,有三个大穹门,左右方的两个穹门,垂着丝绒的帷幔。中央那个更大的穹形门,通连着一间憩坐室;穹门中间,设置一株辉煌耀眼的圣诞树。广厅内部,因这集会而新加髹漆,浅绯的四壁,点缀着红烛形的壁灯,烛光幽幽地,带着些异国的古典情调。
承尘上面,彩纸球缤纷如雨,小电泡密缀如星,沿着广厅四壁,安放着舒适的沙发,与贴壁的半圆小桌。每只小桌上的名贵瓷瓶内,插上点缀时令的槲寄生,火红的叶子,象征热情,象征喜气,也令人向往昔时御沟中的罗曼史,而忘掉门以外还有吹死人的西北风。
婀娜美丽的姑娘们推动轮架,满场供应可口的果点,大家随意要,随便请,不必客气,不必拘束。
音乐台位置于广厅的那一端,跟大穹门劈对;台后,张挂着一张六尺高的油画,是幅少女的半身像,披着轻纱,胸肩半裸,她的神情真骀荡,好像全世界的春,都是从她一双娇媚的眼内所发源。她睡眼惺忪,盯住了那些忘掉了生辰的人们,像在细声地说:“人生真枯燥呀!快来吻我一下吧!为什么不?”
没有人解释得出,这幅画,跟耶稣的诞辰有什么关系?正同没有人解释得出,那些享乐者的狂欢,为什么一定要拣中这个舶来品的节日一样。
今夜这个会,并不能说最豪华,但是,所有的声色享受,已足够使觳觫于西北风中的人们增加觳觫!这里且把会场的节目说一说,那些节目,也都出于派对专家所订。
节目之中,上半夜是各种杂耍,由参加者分别担任;下半夜,却是全体出动的热闹的化装跳舞。
化装舞将开始于一点以后,参加的人,为了增加会场的兴趣,多半预先化好了装杂坐在会场以内。所化装的人物,自出生于科西嘉岛的炮兵大皇帝起,到平剧《小放牛》中的牧童为止,历史的、戏剧的、小说的,形形色色,什么都有。把古今的时间,浓缩为一瞬;把中外的人物,拉扯成一堆,虽然不伦不类,却也是奇趣横生。
我们的派对专家倪明,今夜始终是全会场中最活跃的一个。
他活跃得像个小孩,穿着红衣,戴着红帽,白发苍苍,白发拂拂,加上一脸的皱纹。原来他所化装的,却是那位贩洋袜的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在圣诞之夜真是特别忙。他是全会场的神经中枢,每一个来客要由他招待,每一个节目要由他报告,每一件事务要由他分配。他拖着那双大皮鞋,蹒跚到东,蹒跚到西;蹒跚到南,又蹒跚到北。他蹒跚到哪里,哪里就添上了欢笑,会场里有句口号:倪明所到的地方总有光明。
他常常被人拦住去路,像阔人们出外常常被人拦住去路一样。
有一位大茶商正从化装室内走上会场,脸上几乎抹了三寸厚的粉。一大阵拍手欢笑包围着这个人。那人名唤谢少卿,扮的是纸头人二百五。
这个二百五,似颇有志于摩登,服装已改变成了时代化,一套有声西装,连领带、衬衫都是纸糊的,走一步,蟋蟀;动一动,蟋蟀。一个顽皮的小女孩拿着一盒火柴,蹑手蹑脚跟踪着他,在跃跃欲试。
这个身材高大的二百五,拦住了那位矮小的圣诞老人,高声地唱着:
“你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的生命!”
“你不要认错灵魂,他是倪太太的生命!”有人马上接口这样唱,这个接唱的人,是个全副戎装的娇小的花木兰。
笑声大作,白胡子在人丛里乱抖。
另外一小堆人在另外一个角隅里,包围着另外一个重心,在制造浓烈的欢笑。那个被包围者是今天全会场里,最美丽而也最有名的一位小姐。在这银灰色都市的交际圈中走走的人,你若不知道景千里小姐,那你真是起码得可怜!
景小姐芳名千里,有人把她的芳名颠倒过来,在背后恭称她为“千里镜”。同时,景小姐另有一个美丽的外号,被称为“熊猫小姐”,也有人叫她为“M i s s U n i t e”。
过去,在这位熊猫小姐身前身后,以旋风式的姿势打转的年轻绅士们,少说点,该以两位以上的数字来计算。但在距今三月之前,那些旋风似的勇士们,忽然集团地大失所望,原来,熊猫小姐虽没有郑重出国,而却以闪电方式跟一个人结了婚。
千里镜是有深远的眼光的,她所挑选的对象真不含糊,她的幸运的外子刘龙,是一位热衷于政治的人物,他的大名,虽然并不十分了不起,但是,他在T V S的幕后,的确是个二等的红人。同时呢,他在从政之余却还经商,在他手内把握着好几种大企业,依仗着某种优势,加上心凶,手辣,会攒,会刮,他的钱囊,永远是在膨胀,膨胀,而再加上膨胀!
景小姐自从被装进了这膨胀的钱袋以后,她的芳踪,不复再见于昔日的交际场。但据传说,她跟几位阔太太们,最近却是赌得非常狂热,快要把五十二张纸片当作食粮。
今天,这头美丽的小熊猫,居然被牵进了这个集会,在我们的派对专家,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
这时,包围着圣诞老人的欢笑声,哄声传到了景小姐的位子边,她赶快高喊:“你们笑些什么?倪明,我的圣诞老人,你不分点光明给我,你忍心看我失明吗?”
“什么?景小姐,你说的是失明还是失恋?”那位大茶商撩起他的纸制的上装,窸窸窣窣地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一只花纸糊成的板烟斗。
“滚开些,二百五!”小熊猫向他娇嗔。
这时小熊猫身边另有一个人轻轻接口说:“真的吗?景小姐,你也失恋了,为了什么!”这个故意插言的人,装扮着一个十九世纪的海盗,实际,他是一个颜料商的儿子,名字叫做徐嵩。过去,他也曾为这熊猫小姐发过精彩的男性神经病,但因钞票的堆积不够高度,结果,他在必然律下失败了,直到如今,他还怀着满腔的幽怨,无处发泄。
于是熊猫小姐向他噘噘红嘴唇,说:“你放心,我永远不曾恋爱过什么人,所以,我也永远不会失恋。”
海盗说:“那么,刘先生有点危险了,你预备放弃他了吗?”
“我为什么要放弃他?至少,他是我的一本靠得住的支票簿,我有什么理由要把支票簿放弃呢?”红嘴唇又一披。
海盗默然无语。
正在这个时候,下一节的节目又开始了。
只见圣诞老人站在会场中心,向大众报告说:“现在请看曹丞相的后代曹志宪先生表演魔术,他今天荣任接收大员,表演接收魔术,请诸位多多捧场,多多送些汽车洋房给他。”
满场掌声如雷。
曹丞相的后代,摇着他的四点一刻,在热烈的掌声中缓步登场,他身上穿着参加鸡尾酒会那样漂亮的夜礼服,头顶着尺许高的礼帽,鼻子上抹着一小块铅粉,额上用铅粉写着一个官字,那种轻骨头的庄严的样子,引得满场大笑。
曹先生在会场中心那张特设的小桌边上放下了他的四点一刻,脱下了白手套,然后向大众鞠躬,把双手撑住桌子说:“兄弟今天初次登台,有大段道白,先要向诸位宣读一番。”
“欢迎!欢迎!”群众向他高喊,其中那个化装成杨贵妃的张三小姐,尤其“欢迎”得起劲。
于是那位魔术大员咳嗽一声,郑重发表说:“戏法人人会变,下官变法不同,官能做得投机,财会发得轻松,笑骂随他笑骂,昏庸由我昏庸,上台中国贵人,下台外国公寓,眼明脚长手快,头尖脸厚心凶,升官而且发财,巧妙都在其中!”
又是一阵如雷的掌声。
有人在偷望景小姐,因为景小姐的那条龙,是这个忽官忽商的两栖动物。但是景小姐也在拍手。
一个扮作梦里想造反的阿Q的人,名字叫做洪蓼,高声向这魔术家说:“大人,小的以老百姓的资格向你请问,有什么大饼之类的东西,从你礼帽里变点出来给我们吗?”
“对不起,没有!”魔术大员沉下脸。“我的戏法,只会变进,不会变出。”他脸向众人。“喂,诸位,有什么东西,要我变走吗?钞票、条子、珠钻,都好,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我都能变走。”
“人,你能变掉吗?”有人在问。
“当然!他能连你的血肉、脂肪、骨髓,变得一点都不剩。”阿Q代魔术家说。
于是有人把大叠钞票丢进了魔术家的帽子,看他如何变掉。
魔术家轻轻把礼帽一摇,眼球不及眨,果然,变掉了,手法真快!随后,他把预先陈列在桌子上的小洋楼,小汽车,等等,同样丢进他的礼帽,同样一摇,一摇,一摇,同样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
他说:“你们有最贵重的东西交给我,我就能变出最新奇的戏法来,让诸位解颐。谁愿意试试?”
大众感到非常有趣,不发声。
魔术家似乎等得不耐烦,他忽然从胸口伸出一只剩余的手来,向大众勒索。
众人大笑。
杨贵妃从手上脱下了一只镶土耳其玉的指环说:“这个,可以变吗?”
“拿来交给我。”魔术家说。
“不,拿来,一切交我,不必交给他!”
突然有个凶锐的语声,发自另一角落,划破了全场欢笑的空气!全场的视线都被这个怪声拉扯了过去。只见,有一个戴着黑色面具的人,严冷地,矗立在左方穹门的帷幔之前,手里,拿着一支小左轮!
全场的人呆住了!
有人想笑而没有笑出来。
拿手枪的那个人,继续在发命令,他的严冷的语声,好像使人心头系下了铅块。他说:
“嘿,很好!你们这一群人,真高兴呐!你们忘却了门外边有西北风,忘却了西北风里还有冻饿而死的人群!很好,来来来!”
他把手枪口一摇一指。“现在,请带钱的绅士们,有饰物的太太小姐们,排好队,走到那边的角落里去,等候我的检查!喂!不许乱动!”
这个新奇的局面不知是真是假,但,整个暂时寂静的广厅里,的确有好多颗心在往下沉,往下沉!
静寂中有一个人在打着轻声的哈哈安慰着身旁的一位女宾说:“你忘却了倪明的话了吗?他说今夜还有意外的刺激,不要慌,那是假的。”
“好,假的!”戴假面的家伙凶视着发声的所在,那支小左轮,像架汤姆生轻机枪那样向四周摇成一个半圆形,他说:“我这支假的左轮枪,装足六颗子弹,足够在六个人的身上制造半打空气洞,谁要试试吗?”
手枪管向前一伸,有一个站在火线里的小姐“啊呀”一声向后直躲,但是,那个手枪口忽然又向上一仰,指着一支烛形的壁灯做了目标。
“砰!”
一支红烛形的壁灯应手熄灭,豁啷啷,玻璃纷纷碎落!
事情看来不像是假的了!
熊猫小姐吓得花容失色!
娇小的花木兰,那是庄澈小姐所扮,预备卸甲而逃!
杨贵妃躲到了一个生人的怀抱里!
男宾之中,谢少卿胆最小,原因是:假如他在他的身上,真的带了一个空气洞回去,他将不好意思再见他的太太吴吟秋女士。因之,窸窣,窸窣,窸窣,那套有声西装抖得厉害响得厉害。
大众慌乱中,那个蒙面人又说:“请识相,快把东西交给我!不吗?再看我的!”
手枪口又向空一指。
“砰!”
“砰!”
随着这“砰”、“砰”两声刺耳的枪声,满场的电灯忽然全部熄灭,一座欢乐的天堂,霎时变成了黑暗的地狱!
女高音在漆黑中尖声怪叫,这一个刺激镜头真够刺激!
可是,这个镜头仅仅维持了几秒钟,电灯在一暗之后立即恢复光明。只见那位圣诞老人,笑嘻嘻地站在会场中心向大众高声说:“诸位,请各归座,不必慌乱,我们这个世界,充满着虚伪、残暴与丑恶!缺少的是真、善、美,而尤其缺少的是三个字中的头一个字,所以,我可以安慰诸位说,方才的场面,完全是场假戏。现在,让我把非真品的侠盗鲁平,介绍给诸位先生跟小姐们。”
圣诞老人说完,那个假强盗,立刻脱下了他的面具,藏起了他的小手枪,走入场心,以演员向观众谢幕的姿态,笑微微,向大众鞠躬。
人丛里有人在失声地说:“该死,原来是他!”
大众不禁吐出了一口气,小姐行列中有人在抹汗。
二百五的有声西装不再发抖。
魔术大员曹志宪,赶紧走上前去,从胸前伸出手来跟这假鲁平握手说:“Y·M,你表演得真不错。”
原来,这个化装为侠盗鲁平的人,真姓名叫做荣猛,跟他认识的人都叫他Y·M。
荣猛回答那个魔术家说:“你也表演得不错,你今天是新官上任。”
“你今天是强盗坯出马。”
“我们都是时代的伟人!哈哈哈。”
那个娇小的花木兰,惊魂初定,扭住了圣诞老人撒娇地在说:“你这个坏东西,为什么要想出这种法子来吓人,嗯,我不来!”
圣诞老人躲闪着说:“请勿碰掉我的胡子!喂,庄小姐,你是花木兰,放些勇气出来呀。”
那边厢,张三小姐却在慌张地寻找她刚脱下的土耳其玉指环。有人在笑,杨贵妃失去了玉环,那倒是桩奇闻。但结果,三小姐的指环找到了,还在她的手指上,不过错戴了一只手。
这一场纷乱,真是又紧张又可笑。
在这一场虚惊之中,那只小熊猫,最先是花容失色,等到听说这个活剧是假的,她定定神,一看,只见那个化装侠盗鲁平的人,胸前果然垂着一条耀眼的红领带,左手戴着一枚鲤鱼形的奇特的大指环,这些都是传闻中的那个真正侠盗的标记。真侠盗的左耳上,应该有颗红痣,他却贴着一小片红绸以作代替。这人身上所穿的西装,显得雍容华贵,他脸上有一种特殊表情,不笑的时候老像在笑,笑的时候却有一种威武逼人的神气。
熊猫小姐对这个人,立刻发生了兴趣。
她向圣诞老人招手,高声说:“倪明,你能把这位神秘人物,给我介绍介绍吗?”
圣诞老人应声而至,掉过头来说:“来来来,次货侠盗先生,听见吗?大名鼎鼎的景小姐,希望见见你,你感到光荣吗?”
“不胜光荣之至!”
那个强盗立即踏着娴雅的绅士步子,走向熊猫小姐的座位之前,跟小熊猫握手。在握手之顷,他感觉到有点飘飘然。
小熊猫指指她身旁的位子说:“侠盗先生,我能不能有这荣幸,请你在这里坐一会,我们谈谈?”
“绝对遵命。”假强盗温柔地回答。
于是,他整整他的红领带,就在熊猫小姐所指示的位子里坐下来。但是,坐下之后立刻有件事情,似乎使他的神经觉得有点局促不宁。原来,在他另一边的一只矮沙发里,有一个人,靠在椅背上,正用一种非常特别的眼光,在注视着他。这个人,把大衣的领子拉得高高地,掩住了半个脸与耳朵,似乎很畏冷看样子,那人站起来时个子一定相当高。他并不认识这个人,以前,在倪明所召集的派对里也从来不曾见过面。
他对这个人的频频注视感觉不安,但他找不出所以不安的原因来。
这边,熊猫小姐笑得像朵仲夏夜的带露的花,她以一种在蜜糖内浸过似的声音在向他说:
“我告诉你,我对那个神秘人物的种种神秘传说,一向最喜欢听。”
“小姐,我以为你应该这样说:我对你的往事,一向很喜欢听。”假鲁平正经地纠正她。
“是的,我说错了。至少在今夜,你挂着红领带,你,就是那个神秘的人,对吗?”小熊猫玩笑地说:“我听说,一向,你专门抢人家、偷人家、骗人家、又恫吓人家,你的行为,十足只是强盗行为,而你,却喜欢接受这个侠盗的美名,这是什么理由呢?”
荣猛笑笑说:“凡是有作为的聪明人,都喜欢找些悦耳悦目的东西,遮掩自己的丑恶,我何独不然。现在既然有人肯以‘侠’的美名遮掩我的‘盗’的丑恶,我为什么不欢迎,小姐,对吗?”
“你很会说。”小熊猫点头微笑说:“ 不过我还听到说,你一向不用手枪,今天,为什么用这小玩具吓人?”
“啊!小姐,人类是在飞速进步呀!在这唯武力主义的世界上,我也希望我能改善过去的缺点,以便适应时代呀!”
假鲁平这样侃侃而谈时,身旁那个拉高衣领的人,耸了耸肩膀,微微冷笑。
正在这个时候,会场之中,忽然又有一个小小的高潮,起于人丛之中。那位食品厂的厂主庄承一,突然在人堆里怪声高叫:
“啊哟,我的手表呢?我的手表不见了!”
曹志宪说:“本大员并未接收。”
大庄的阿弟小庄,却在讥笑他的哥哥说:“据我想,站立在玻璃窗里专门穿衣服样子的木头人,想来也会看顾好他自己的东西的,戴在手腕上的表竟会被窃,笑话!”
假鲁平听到他们的喧闹,故意弯转手臂来看看时间,他高叫说:“啊呀,怎么我的手上会有两只表?谁把手表错戴在我手腕上了!”
曹志宪嬉笑地走过来说:“侠盗先生,你的手法真高呢,比之我的更厉色!”
假鲁平摇头说:“至少我还赶不上你那样伟大。你是一个官,你用魔术手法,掠夺了无数的脂肪,结果拍拍屁股可以绝不负责,而我们这些当强盗小偷的,假如掠夺了一挂香蕉,那或许可能挨到枪毙咧!”
听的人笑了起来。假鲁平把那只暂借的手表归还了原主。
熊猫小姐见这次货鲁平也具有如此惊人的手段,她惊奇得睁大着一双媚眼,说不出话来。可是那个次货鲁平却在暗笑,他想:“小姐,何必大惊小怪,那也是假戏罢了。世上原有无数无数看来像是了不起的人物,其实,也不过像我一样,依靠可爱的配角们,跟他狼狈为奸而已。”
总之,会场上自从这个假的侠盗上了场,欢笑的空气,似乎格外浓厚起来。
这时,会场中的另一节目又在开始,那是两个滑稽人物在仿效北平相声。
但是那位熊猫小姐对于这个假鲁平,越来越有兴趣,她已完全不再注意到会场中的节目。
她添浓了花一样的笑,小酒窝里储满了蜜,她向假鲁平说:“荣先生,你的手段,真的跟那传说中的红领带人物,有些差不多。”
“承蒙嘉奖,愧不敢当。”假鲁平颔首谦逊。
一旁那个拉高衣领的家伙又在冷笑。熊猫小姐当然不会注意,而这假鲁平却是注意的。他憎恶这个人,尤其憎恶这个人的那种深刻的注视。
只听小熊猫继续腻声地在向他说:“荣先生,假如你是那位真的侠盗,那真使我何等高兴呀!”
“那你何妨就把我当作真的侠盗呢?”荣猛说。
“不,我极希望能遇见真的他。”
“有理由吗?”
“我希望那位真的侠盗,能够光顾我家,随意带走点东西。”
“什么?”荣猛抬起了眼珠,感到不胜惊奇。
拉高衣领的家伙,锐利的眼珠在发亮,他在仔细地听下文。
荣猛说:“小姐,你希望那个神秘人物光顾你府上,这是什么意思?”
“你听我说,”小熊猫发出微喟,眼角带点幽怨,她说:“在以前,我的名字是常常被刊到报纸上的。自从跟刘龙结婚之后,报纸上似乎把我完全忘却了。人生活在世上,不论男女,总希望有机会表现自己。而我现在,却感到了被遗忘的寂寞。假如,我家里能让那个拖红领带的人物来渲染一下,那么,那些记者先生,可能又要把我大大描画一番啦。”
荣猛听着好笑,不禁好玩似的说:“那么,小姐,你府上的钱财,一定是非常之多的了。”
“那还用说吗?”小熊猫有点傲然:“同时我也感到奇怪,世上会有那么多的低能儿,忙昏了头,连大饼也找不到。而我家里的钱,却多得快要发霉!”
荣猛追溯半生,在记忆中似乎还找不出这样一个歇斯底里式的女人,竟会因着钱的太多而发愁。于是他又好玩地说:“那真可惜了,可惜我不是真的侠盗鲁平。”
“假如你是真的,我真愿把我那座私房小保险箱的所在地告诉你;甚至,我可以画一张房屋的草图送给你。”
这时,荣猛发现那个拉高衣领的家伙,双目灼灼,透露着更注意的神气。假鲁平在那凶锐的视线之中感到背上有一阵寒凛。他慌忙拿起他的打火机,轻轻碰着玻璃桌面,示意那只小熊猫,不要再那么孩子气;偏偏那只小熊猫,全不注意四周的一切,还在任性地说下去。
她说:她的那座私房保险箱,是在她的卧室之内,在她的床边上,有一只夜灯几,把夜灯几推过一些,那座秘密小保险箱,就会显露出来。她把门户与楼梯的方向地位,描写得相当详尽,最后,甚至她说:“假如你是真的鲁平,我可以把综合锁上的密码,也一并奉告。”
隔座那个拉高衣领的人,有意无意把身子直了些,倾听得更为出神!
荣猛再度焦灼地敲着桌面,他从桌下伸出脚尖,碰着那双高跟鞋。可是,对方那只美丽的话匣,似乎损坏了机件,一开,竟已无法再关。她自顾自天真而又任性地说:
“那么,可要我把最近所用的密码告诉你吗?那就是——U,N,I,T,E,五个字母。”
荣猛偷眼看时,只见隔座那个人,闭上眼,身子又靠到了椅背上。荣猛不安地轻轻嘘了口气,摇摇头,他准备离开这位神经质的小姐,以免引起意外的是非。
可是那只小熊猫却向他娇嗔着说:“怎么啦?你不高兴听我的话?”
“我在恭听呀。”荣猛轻声地说:“你说那个密码是U n i t e,啊M i s s U n i t e,就是你的美丽的外号,我感谢你,把这样的秘密也告诉我。”
小熊猫的眼角里带着一种奇怪的幽怨,她说:“但这秘密,你是不会感兴趣的。否则,我愿意连保险箱上的钥匙,也亲手奉送。”
“我心领盛意。”荣猛耸耸肩膀:“假如我是真的鲁平,那我用不到钥匙;假如我不是真的鲁平,我拿了钥匙也没有用处。”
当他们两人这样密密切切谈心时,四下有许多嫉妒的视线撩拂他们。尤其是那位海盗徐嵩,把过去的悲哀,与跟前的抑郁,交织在一起,都从眼膜内穿出来,成了两道怒火。人生真奇怪,在这样欢娱的场面下,人的情感,竟会表现得如此的不平衡。
这时,忽听圣诞老人在场心高声报告说:“我们的化装跳舞,准备提前开始,请诸位准备。”
他向乐台上招招手,场内的灯光渐渐幽暗,一阵爵士乐声立即随之而起。
那第一只拍子急骤得像是一阵夏雨,象征着人生的匆忙与纷乱,紧张与短促。
假鲁平乘机向熊猫小姐告假,他缓步向另一位小姐走去,那位小姐名叫易红霞,是他昔日的伴侣,他就把第一支舞献给了她。
这里,熊猫小姐遥望着那条鲜红的领带,贴近了一个乱头粗服的渔家女的胸前,旋转进了旋转的圈子。
有人站到小熊猫身前,要求她同舞,小熊猫伸着懒腰,没有起身。
音乐声把人类狂欢的情绪,渐渐吸引到了最高峰!
景小姐是今夜狂欢气氛中的一朵最芬芳悦目的花,但是,花会盛放也会憔悴。她自从那条红领带离开之后,好像已由绚烂的时间,归入于平淡的状态。
第二阕乐曲开始的时候,她以懒洋洋的姿态被那圣诞老人拥进了舞池。她对跳舞似乎不感兴趣,她一直在人丛里流波四盼。
奇怪!此后她在会场里有好多时候不再看见那条红领带。
那条红领带到哪里去了呢?
景小姐的心坎中带着一种空虚的失望,而且她也感到有点惊异。其实,那个垂着红领带的假侠盗,同样的,心里也正带着另一种的讶异。原来,在他跳完第一支舞之后,他忽一眼瞥见刚才那个坐在小熊猫隔座的人,拉拉衣领,悄然离开了这广厅。
这使他感觉可怪!
于是,他也悄然跟随他出外,他感觉到他有悄然跟随他出外看一看的必要。
狂欢笼罩住整个会场,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些事。除了小熊猫以外,也没有人注意到荣猛曾经离开过会场。
一小时后,荣猛方始拥着这只小熊猫,一连舞了好几曲,于是,小熊猫的粉靥,方始重现明朗的浅笑,像蓓蕾初放。
这一夜,会场里的衣香、鬓影,灯光、乐声,气球、彩纸,等等……等等……在每个人的脑壳里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梦,梦里的人,当然不会记起有明天,于是狂欢一直在继续。
而在这个故事里是有明天的。
到明天,一件奇事发生了。奇事发生在刘公馆里。
比较准确地说,这奇事还是发生在上一夜。原来,刘公馆里刘少奶奶的那座秘密保险箱,真的遭遇了偷窃。那只夜灯几,被推到了一边,保险箱门开得笔直,其中全部饰物,尽被那位夜半的贵客带走了。主要的是一串珠项链圈,另加美钞一千元。但这小数目的美钞,比之全部饰物的价值,那真是卑不足道了。
当天的报纸上,当然还来不及刊布这个新闻。可是腿长的记者先生却已三三两两拥进了刘公馆。记者群中有一个高个子,没有人知道他隔夜曾参加过那个盛大的圣诞集会。连熊猫小姐本人,也不曾注意这个人。
小熊猫在应付了记者先生们的无穷的问答之后,感到有点疲倦。她躲进了另一间屋,她在支颐出神,有一条红领带的影子在她眼前晃荡。她在想:
“难道昨夜那条红领带,真的就是……”
电话铃声打断了她的思绪,有一个女佣在喊:“少奶奶电话。”
小熊猫拿起话机来,她立刻听出,对方的声音,就是昨夜那个假扮侠盗鲁平的荣猛。她有点发怔,只听话筒里在说:
“景小姐,我想跟你晤谈一次,行吗?”
“什么时候?”
“今天,即刻。”
“什么地方?”
“杜美公园对面,那家绿色门面的咖啡馆里。”
“这是必要的吗?”小熊猫沉吟了一下而后问。
“当然是必要的。”
熊猫小姐虽然在保险箱里失落了那么多的饰物,但是她在放下话筒而略一凝眸之后,依然满脸透出五月花那样嫣然的笑来。
她匆匆走到镜子之前,把自己装扮成了女神一样。跳上自备汽车,吩咐车夫开到杜美公园。
假如汽车有眼珠,而眼珠又长在车后,那就能看见,有部飞快的跑车,在它身后追逐。可是安坐在汽车内的小熊猫,当然不知道。
在十分钟以后吧,这一对男女,在那家绿色咖啡馆中见面了。他们像一双爱侣那样,在一座贝多芬像下的静僻的位子上坐下来。
四周座客很少,播音器在播送一支西班牙交响曲。
熊猫小姐不说一句话,只向荣猛身上,脸上,细细而又细细地看,最后她说:
“你知道昨夜我家里所发生的事吗?”
对方只以点头代替回答。
“昨夜,我的保险箱真的被人打开了。”
“那么,我该向你道贺,因为这是你的愿望哪。”荣猛微笑。
小熊猫凝视着荣猛的胸前,他胸前依旧垂着昨夜的那条红领带。凝视他的左耳,左耳依旧贴着一小块红绸。于是,她嗫嚅地说:
“那么,你,你真的是……”
荣猛的视线向四周溜了一转,说:“我们不谈这个问题,行不行?”
小熊猫露出一丝笑,说:“那么,我可不可以说,昨夜你的收获不算太少吧?”
荣猛正用小匙调着杯子里的咖啡,似笑非笑地反问:“小姐,你记不记得,昨夜倪明所说的话?他说,在这个世界上,缺少真,缺少善,缺少美,尤其缺少的是三个字中的第一个字,你对这话,有什么感想吗?”
“我不懂你的意思。”
“小姐,”荣猛耸耸肩膀说:“难道你还以为你的许多饰物,包括那串美丽得吓人的珠项圈,都是真的吗?”
小熊猫的两靥,突然红得跟她的嘴唇一样,低下头,不说话。
荣猛喝了一口咖啡而后继续说:“昨夜,我有一种直觉,觉得你的谈话,差不多是在用一种粉红色的请柬,想请人家到你家里去偷窃。一方面,你却把大批美丽不真的宝物,放在你的保险箱里,以等待欣赏者来欣赏。你这样做,当然有理由。今天我约你谈话,就希望你把其中的理由告诉我。”
那朵花上添浓了红晕,依旧低头,不语。
但是荣猛把视线盯住了她,这视线似乎具有一种力,逼迫着她非答不可。
于是,熊猫小姐猛然抬起了头,看看四周,轻声地说:“最近,我赌得大输,不但输光了我所有的钱,也输光了我所有的首饰。为了掩饰我的赌博的惨败,我弄了许多假的饰物,放在我的保险箱里,作为一种烟幕。”
“你提防着谁会检查你的饰物呢?”
“并不一定提防谁,但是,我让任何一人发觉我的全部饰物,已是一无所有,那总不大好吧?”
“听你的语音,好像你对你的刘先生,有点顾忌吧?”荣猛用讥刺的眼光看着她。
“顾忌?我为什么顾忌他。”红嘴唇一撇:“总之,暂时我觉得我还没有理由放弃这本支票簿。”
“但你把这假的饰物代替真的,总有一天,纸包会包不住火的。”
“为此我很着急。”小熊猫微喟说:“我真有一种可笑的幻想,希望有一个知趣的强盗,到我家里来,撬开保险箱,大大掠夺一次,那么,我可以把历次赌输的账,全部记在强盗身上了。”
“小姐,想得真聪明!”荣猛斜睨着她,讥刺地说:“于是,昨夜你就向我提出暗示,希望我来做你的划账户头,是不是?”
小熊猫在那条领带上凝注了片瞬,然后说:“在当时,我并不真的以为你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因之,我的确也并不希望你真会帮我那种不可能的忙,我不过是在玩笑之中,无意透露了我的焦灼的心理而已。”
荣猛耸肩说:“而我这傻瓜呢,由于你的暗示,做了真正的贼,而却偷到了你的假东西。”
小熊猫用媚眼撩着他,轻轻说:“但你也并不是毫无收获的呀!除了那些不值钱的东西之外,保险箱里还有着,还有着……”
“一千元美钞,那总不是假的钞票吧?”
一种阴冷的语声,杂在音乐声里,破空而至,来自荣猛的脑后!
荣猛感到骇然,赶快旋过头去看,只见隔座有个人,坐在他的背后,坐得非常之贴近,那人半个身子斜伏在椅背上,嘴对他的后脑轻轻在说话。
这个人,一望而知就是昨夜那个拉高衣领的人。
荣猛竟未注意,这个人是什么时候走进这咖啡室,而坐在他身后的。
当着一位美丽的小姐的面,荣猛受到这样意外的袭击,他有点发窘,他向那个人问:
“你是什么人?”
“你当然认识我,我们昨夜会过面。”那人傲然地回答。
“我要知道你是谁!”荣猛加重了语气。
那人伏在椅子背上没有动,他只傲然指指自己的胸前,他的胸前同样垂着一条红色的领带。
熊猫小姐呆住了,她在想:“哎呀,那条真的红领带也出现了!”
但是荣猛还在问:“你说你是……”
“不错,我是……”那人向四周张望了一阵之后说:“昨夜你所扮演的人!”
哈哈哈哈哈!
荣猛忽然毫无顾忌地大笑,笑声之中,他的眼珠凝成了两点钢,怒射着对方那个人,他说:“你曾当过舞台演员吗?你的修养不够咧!朋友,你跟我来!”
他把那人引领到另外一个空座上,他们低声谈起来。
小熊猫的花一样的两靥有点失色,她在代荣猛着急,她不知道他将怎样应付这个在夹缝里钻出来的神秘的人。
可是那边两个人的一场交涉,办得非常迅速,几乎可以说是闪电式。
小熊猫用心地注意着这个来得出奇的人的神气,奇怪,他的神气起先像匹狮,继而像只鼠,终于成了一头驯善的绵羊。
她不明白荣猛用了些何等的魔术,会使这个家伙的态度变化得如此之快?
最后,他们从那边的位子上站起来,荣猛把一大卷钞票,丢给那个家伙,用呼叱一条狗的声气向那人说:“我不使你失望,走吧,不要打扰我!”
那人偷眼看看小熊猫,一声不响付掉了咖啡账,悄然而出,鞠躬如也。
看来交涉的胜利是属于荣猛了,景小姐吐出了一口气。
当荣猛坐到老位子上来时,她娇媚地说:“几乎吓坏我,我以为他是……”
“你以为他是……笑话!”荣猛打断她的话。
“那么,他到底是谁?”
“一个高贵的自由职业者。”荣猛冷笑:“他的办公处有时设在电车里,有时设在电影院门口。今天,他在企图改业为敲胡桃专家。但是敲胡桃也要有点艺术,他的气度、修养,都还不够咧。”
“那么,他怎么会知道昨夜的事呢?”小熊猫讶异了。
“他偶然捡到了一张请柬,参加了昨夜的集会,大概在那里想找机会,而无意中却窃听到了你我的话。”
“那么,今天他怎么会插身进来呢?”
“这个吗,我也不很明白哩,好吧,不要再管这些事。”
“你把美钞分给他些了吗?”
“分给他,为什么?那一千美钞,我预备全数奉还给你哩。”荣猛假作慷慨地这样说。
“还给我,为什么?”小熊猫在学舌。
“让你再充一次赌本。”
“不太够哩!”景小姐傲然扬着脸。“老实说,这笔钱原是人家寄存给我的,要不然,我早就把它送给了皇帝与皇后们;而现在呢,一切一切,我都可以向刘先生开账了。”
“可爱而又美丽的支票簿。”荣猛幽默地说。
“所以我愿意把这点小款子,留在你处作一个纪念。因为昨夜的事,你是大大的帮了我的忙了。”
“感谢你的慷慨。”
景小姐看看对方愿意接受她的赠与,她也很感欣慰,她又透露着五月花那样的笑容,说:“在书本上,我常常看到许多英雄们,常常行侠仗义,常常劫富济贫,那么,你对这笔小钱打算怎样支配呢?”
“我吗,我打算从中提出美金一大元,买几双廉价的袜,赠与几个赤足的老乞丐们,以作圣诞老人的礼物,这就算是我的义侠奉功了。”
小熊猫不禁失笑,说:“你这位大慈善家,气派如是之小吗?”
“我怕世上那些有钱的人,十之九,气派不会太大吧?”荣猛撇嘴说:“请看,外国的大富豪,必定要等到身后,才肯在遗嘱上把财产作慈善的施与;而中国的富豪呢,真要等到牯牛身上长不下毛,才肯忍痛拔下一根二根。而这所拔下的一二根,还要作为两种不同的用途:一种,预备吹口气,把它变作进天国的入场券;另一种呢,却预备把它变成慈善家的金字招牌!总之,这个可爱的世界,充满着自私,请你趁早别希望在这个充满自私的世界上,会找到真懂得爱与真能实行所谓善事的人。”
熊猫小姐听了,凝眸痴望着对面的这位出奇的人物,默然无语。
而荣猛却微笑地站起来,接下去说:“至于我呢,我也是个人,我也具有自私的美德。眼前我只发了美金一千元的可怜的小财,我为什么要那么小气,自充什么大善士或侠义人物呢?”
景小姐把视线停留在那条红领带上说:“你的口吻,完全跟那个传说中的人物相像,那么,你一定就是……”
“嘘!”荣猛把一个手指遮着口角,扮了一个鬼脸,他说:“亲爱的小人儿!人生的一切,都不过是游戏而已,何必认真。请你别谈这个行吗?”
这一天,他们在这绿色的啡咖室内,谈着绯色的话。他们谈得很多,谈得很久,谈得很密。最后,他们懒懒地起身,依依地惜别,荣猛恋恋地送这位热情的小姐上车,并殷殷地互订后会。
看来,一颗罗曼史的种子,已经投放在沃土以内了。
像这样的喜剧,常在银灰都市里原是习见的事。好在,眼前正有太多的刘龙先生之类的人物。他们富有搜刮天才,他们永远有方法向贫苦大众直接或间接地穷搜猛刮,因之他们永远可以做他们美丽的太太的支票簿,以负担无限的义务支付,于是,那些美丽的太太如景小姐之流,也永远会有足够的资本,可以任意狂赌,以及任想制造罗曼史。
这是我们的社会之一景,多么可爱啊!
可是隔夜那些参加狂欢的人,却绝不知道荣先生与景小姐之间所发生的事。
虽然有人知道刘公馆失窃,但是,他们只知道那天的集会中,另外有个红领带的歹徒(或许就是那位真的侠盗先生),听到了小熊猫的任性的话,以致造成了这件窃案。黑狗闯祸,白狗担当,绅士们偷了东西,由小偷负责。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社会上,也并不足怪。
总而言之,没有人怀疑荣猛,跟这窃案有关。
而荣猛呢,也一直还在大庭广众之间摇摆地出入,逢高兴,他还是垂着他的红领带。
那么,他,真的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神秘人物吗?
这,连说这故事的人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