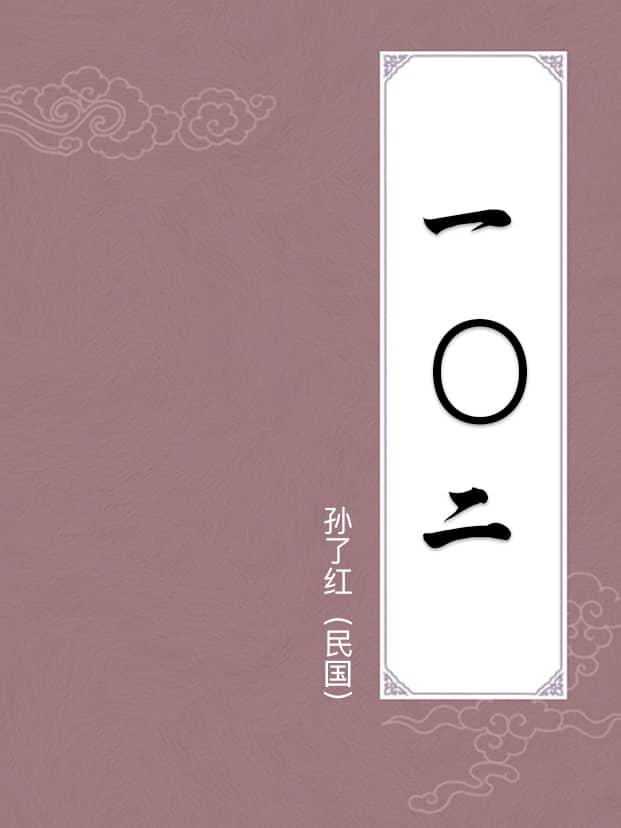以倒栽的姿态,躺在斜坡形病床中的奢伟先生,竭力探索着那张二十世纪“推背图”上的最不可索解的一点,但是他想来想去,却想不出其中的所以然来。
他却始终揣测不出,就是在那张弄玄虚的图上,凭什么理由,那个棕色圆脸的家伙,竟能在这图上留下一个那样确定的日期呢?更可怪的,还有那浓眉毛的“主有杀气”的武生,他居然会大胆地上演他这精彩无比的全武行的戏剧,但是又怎会如一头羔羊似的,偏偏会如此驯良地按照这图上的预示,真的在这被指定的日期:——“二月二十六日”这“黄道吉日”——“隆重演出”这毒辣凶狠的惨剧呢?
这位受着重伤的奢伟先生,脑神经相当衰弱,他虽有思索的能力,虽然他的思想之箭,箭箭都已中鹄,但对于这一点,对于那张图画中的最细小的一点,却无论如何在短时间内揣测不出所以然来;他分明知道他自己现在的处境,还是离“生”远而离“死”近,所以他立即“适可而止”“悬崖勒马”了,他准备安静下心来,让他的“思想之箭”暂时休息一下。他所以如此打算,他有他的理由——
第一,他记得:他在游戏场里打过“一百○二”枪之后,得意地准备返回他的寓所去时,他碰到那位打靶失败的小英雄,那个小弟弟递给他一张说是他——奢伟先生——遗落的“文件”;当他看到“他”遗落的“文件”的内容中,有着一个标明着“一○二”数目字的被射击的标的时,和在街路上偶然听到卖报孩子高喊“八打半岛”时,他——我们的奢伟先生——不是曾经“灵机”一动,把“一○二”当作了“八打半”岛,而钻进了“牛角尖”中去?“兴师动众”,汇合了许多许多的人力物力,从电讯中,从图片中,去研究这张图画与“八打半岛”的关系。但是,结果都是白费时间与精力。原来,当他知道易红霞姑娘的妹妹的小名叫“珑儿”,而间接明了了易红霞的小名是“玲儿”,更因之完全彻底明悉所谓“一○二”即是“易玲儿”的谐音,而那张怪图上所要他挽救的“一○二”,并非远在九百十哩之外的“八打半”岛,却是差不多与他天天相见的“易玲儿”时,岂不是这谜底,恰是符合了两句俗话,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吗?因此,奢伟放弃“新式推背图”上的“日期”的揣测,是避免自己拼命向“牛角尖”中去钻,而或者可以从偶然中触机得到答案。
其次,奢伟先生明白,他困兽似的躺在病床上,决计弄不出什么花样来的。这应归咎于他的脑力与体力,他神经衰弱而且不能动弹。神经衰弱,失去进一步思索的能力;不能动弹,失去了帮助思索的能力;换言之,不能动弹,当然无法找寻关于这一可疑之点的蛛丝马迹;没有情报,凭空幻想会产生出怎样的好结果来呢?因此,奢伟之放弃“新式推背图”上的“日期”的揣测的第二个理由,是准备在病体恢复之后,再“全力以赴”地去探索;现在,在病床上凭空悬想,不但不能找寻到答案,反而足以影响自己的病体。
基于上述二种理由,所以,奢伟先生准备放弃一切徒劳无益的空想,让他衰弱的脑细胞静静休息一回。
但是,或者是适才他的“思想之箭”射击过猛,一时难于收煞;因之,奢伟先生虽然想休息一回,事实上已失去了自制之力。他的“思想之箭”在“二月二十六日”上遭遇了“劲敌”,深厚的堡垒坚不可破,碰住了壁,于是,虽无“预定计划”,但也只得“撤换新阵地”,退到三角边沿上,先探索清楚,三角之中的圆“葫芦”里,究竟藏的是什么药?
自然,谅读者诸位,既然于“二月二十六日”的谜底无从揭晓,也定必急于并且愿意“撤换”一下“新阵地”,知道另一个谜底的吧!
不但是读者诸位,就是笔者又何尝不想获得另一个线索,而进一步(如果有可能的话)帮助奢伟先生解决“二月二十六日”的问题呢!
那么,且听听奢伟先生对于圆“葫芦”里的“L·C·”做怎样的,和是否合理的解释吧。
一个三角,那不过表示三角恋爱;——奢伟先生的脑海里又在奔腾翻滚——而两个尖角上的两个字母:“A”与“B”,也就是代表着两个敌对的角色。但是,三角之中的一个圆圈,是什么意思呢?再说:圆圈中的“L·C·”,又是什么意思呢?
奢伟不得不想得远些的过去了。
摔着蓬松长发,穿着蓝布罩袍的奢伟先生,从游戏场里进进出出,差不多已有三年的历史。京戏班里,后台的角色,和台下的“玻璃杯”,他虽然很少和他们交谈,但由于他具有独特的识见,已把他们的举止行动,井井有条地深深刻画在心版上。前面也已经说过,奢伟先生的估计,作这幅怪图的“画家”决不会是别的浑浑噩噩的家伙,必定是那位棕色圆脸,曾经想和自己打招呼而并没有把招呼打出来的家伙,那么,事情就非常简单,要知道“L·C·”个中的玄虚,只消去请问这位家伙就是了。
然而,这种想头却应该打嘴。因为如果那个家伙,真肯当面答复这个谜底,又何必故弄玄虚,造一幅怪图出来呢?而且,即使他真肯回答,目前他并不在这里,又怎样个回答法呢?无法,只得再进一层想想。
再进一层想想,这位家伙为什么要制造这一幅怪图,它的原因何在?他的如此清晰地知道易红霞姑娘,和她的小名,包围她的“A”与“B”,甚至并不“涨价”,也不打“折扣”地正确明了发生惨剧的日期,可想而知,他对这件事也是非常注意。
其次,——这位棕色圆脸的家伙,以前,奢伟先生曾经有意无意地请教过他的“尊姓”。姓张,弓长张,后台的正角儿到跑龙套,都赶着他叫“张先生”,或者“小张”。那么,“张”,“Chang”,“张”,“Chang”,咦!咦!“小”这个字在英文里不是“Little”吗?如此,圆“葫芦”里的药已经知道了:是“小张”,是“Little Chang”,是“L·C·”。
最后,制造怪图的这位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送进这圆“葫芦”去呢?而且,在这圆圈之外,还有一个三角?说他是“圈”外人,明明关在圈内;说他与三角无关,但是,又偏偏钻在三角之中。
奢伟杂乱地把所想到的凑拢起来,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棕色圆脸的小张,至少是非常同情这位坤伶易红霞姑娘的身世,甚至,或者也有恋爱她的暗流潜伏在他胸中。总之,他对于她的,和包围住她的各式各样人的动静,随时随地,都不肯放过它们,而注意着的;因此,他能够非常准确地知道,她将在何时何日,要遭遇到不幸的事变。但是,或者他没有能力,或者他有能力,但是已经窥破了我的行踪,知道自己有更多的力量会去保护和挽救这位易姑娘的生命,于是他把这重任卸到了自己的肩上;而同时,他也在暗中随时随地帮助我进行;本来他可以直接向我诉说,这一幕悲剧将要上演的缘故、日期、地点,但是他恐怕他自己错认了人,把机密要事告诉一个真真的“大傻瓜”,因之而为好反成歹,弄坏了整盘“棋局”,于是他布下了这幅推背图。至于,他在图上留下“L·C·”这一个他的“大名”的记号,是证明他并不怕事而匿名告发,而坦坦白白地承认这是他本人干的事,如此而已!
但是,我们看遍漫画册子,从来没有发现过作者的名字大大地安放在漫画中间的。他的这种“独树一帜”的作风,又是什么理由呢?这样,似乎适才所猜测的“一人做事一人当”,未免太简单。如果再进一步想,那么,或者是这位棕色圆脸的小张,一定在向我表示:他在这整个三角恋爱故事中,详尽地知道一切的发展过程,因此,这是他所以“躲”在这三角之中的理由;而他的“L·C·”又紧紧裹住在圆圈之中,无非恐怕我缠误,他把“L·C·”放进三角是表示他已占有了这三角的记号,因之,他特别道地地用圆圈替他自己分一道“不相授受”的界限,分清在局内人与局外人的界限。这样的揣测,大致又中了鹄的。
奢伟先生明白,虽然小张为他自己的身份撇清,其实他也正是其中之一员,否则他决不会如此清晰地明了一个不相干人物的私生活和其他的关系。由此,他单恋易红霞之深,以及要挽救她生命的用心之苦,也可见一斑了。
如此,奢伟先生又发掘出了一个谜底,一缕笑意也随着在他的嘴角上一闪。至此,仅仅只有“二月二十六日”,这一个确定日期的由来,还没有获得线索,这是需要等待病痊后,放出全副精神去探索的了。
虽然只有一个疑问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他还是在重伤之后,无论脑力和体力,都不曾恢复到伤前的百分之十的样子,理该静下脑子不再乱想;但是他不可能,在这漫漫长夜里,他总无法安静。
除此以外,在那张图上,另外还有一点,他也不曾获得确定的解释。就是:——那个三角中间,有一个小圈,圈子里,有L和C两个西文字母,边上各附有一小点。这是什么意思?他也想不出来。最后,他觉得这一点已不能单凭悬想找寻答案,而必须有待于别方面的探索。思想至此碰住了壁,差不多已无法再前进。
漫漫的夜,悠长得像一条走不完的路。烦躁混进了他的血液,每一秒钟在增加。思想活动时,烦躁略减;思想略停,烦躁更甚。无可奈何,他只得开足了脑神经的机栝,继续再向乱想里面钻进去。
于是,他又想起了他中枪倒地前的一刹那。
想到当时的情景,立刻,有许多布景的材料,在他脑膜上面开始移动:殡仪馆的牌子,煤屑路,竹篱,空地,手枪,浓眉毛,这些零星而纷乱的东西,渐渐在他眼前,凑成了一幅图。在这流动性的图内,那个杀人的家伙,像一头发疯的狮子被灌醉了酒!一手执枪,扳机待发!由于盛怒,他的手在发抖!那支枪的枪口,距离那个姑娘的胸膛,不到一尺宽!
因为当时的演出真像闪电那样的快!在那个时候,似乎并不感觉到这局势的紧张;实际上,却因他的太紧张的神经,已使他无暇感觉到这局势的紧张!但是,眼前再想想,觉得回想比之事实反而加倍的可怕!
在回想中,有一件事使他感觉到很可怪。
他记得:当时那个姑娘,双足站在那条死亡的边线上,她竟全无惧怯。看样子,她把那支枪,简直看到像舞台上的木头的道具;她把对方的浓眉怒目,完全看得像戏剧中人所戴的虎脸子。她非但不怕对方马上开枪,甚至,她还把一种轻蔑的眼色,在讪笑对方:“为什么不快开枪?”在过去,他只知道这位姑娘性情非常温柔;他从来没有看出,她在温柔之中隐藏着如此的倔强。他只知道这位姑娘为人非常懦怯,却从来不曾发觉,她在怯懦的后面,会掩饰着这样的一份刚烈与勇敢。
他越想越感到那个姑娘的勇敢。
而且他觉得:自己虽然和那个密斯脱死神,上了一个大钉子,结果,却把一个勇敢得可爱的少女,从死神手内,强劫了回来。这事情,似乎不能算是做得怎样愚蠢。而且,更使自己欣喜的,果然这个勇敢得可爱的少女,与二十一年前他所熟稔的,旨趣相同的另一个少女,完全一模一样的,具有内藏刚烈,和外貌温柔的性格!
然而那个二十一年前的少女,与目前这个少女,实际上却是毫无关系,即使她们有相同之点,但是以时间推算起来,至少已隔了差不多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了。而要紧的,是目前的那个姑娘。她,要是在这一刹那,她与那个武生之间,没有陡然地跳进了一个自己去,也许早已“香消玉殒”,魂归奈何天去了!幸喜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代她受了这场灾难。那个武生,瞄准了目标,扳动机栝,“砰——”的一枪,一颗滚烫的,火红的,应该射进那个姑娘的胸膛的子弹,无情地钻进了自己的肋骨,自己摇晃着,摇晃着,倒了!
之后呢?之后自己就不省人事了。等恢复知觉时,自己已经躺在这个斜坡形的床上了。
但是,之后呢?说得明白一些,在我倒了之后,不省人事之后呢?
在奢伟先生“倒了”之后,“不省人事”之后,武生金培鑫又干了些什么危险的事?易红霞姑娘是否脱险了呢?说不定在自己晕去以后,浓眉毛家伙又接连放射了两枪呢?如此,则……
思想至此,奢伟先生似乎听到“砰——”一响,接着,又连接听到“砰——”“砰——”两响,他的脑膜上,突然浮现着一个胸前喷射出血泉的少女,向地下倒去,倒去……接着,奢伟见她,双手捧住胸怀,面色一阵青,一阵白,不时的痛苦地痉挛着,咬着牙,发出低弱的呻吟声;不过又过了二三秒钟,但见她在高低不平的,石卵子铺成的地面上,翻滚到东,翻滚到西,结果,她是停止了动弹,停止了呻吟,绝无声息地,躺倒在鲜红的血泊中了。
“啊!——”
奢伟不自觉地用出了四!年前吃乳时代的气力,极声地叫出了上面的一个字;随着,他的衰弱的心房和衰弱的脑海都在急速地砰跳,使他消瘦的面颊痛苦地一阵阵地痉挛着,他竭尽全力,又大声呼叫:
“姑娘!易姑娘!”
此际,奢伟突然觉得眼前一亮,使他从恍惚中清醒过来,从回想中回到现实。他,睁开沉重的眼皮,向髹着白漆的,在灯光中反射出耀眼的光来的病房中,勉强定睛“巡礼”了一回。所收进他的眼帘的,是那个白帽,白鞋,背后两条交叉的白带,系着一个洁白的围身的看护小姐。
他,奢伟先生见到站立在床前的女子,好似获救了似的,在斜坡形的病床上挣扎着——想起来——而且还叫着:
“小姐,请帮助我起来,我要去救那个姑娘,我要去救她!”
但是,他失望了!他的反常的过于兴奋的,也可以说是“歇斯底里”的动作,并未获得反响。相反的,那位看护小姐还是轻轻地用两条手把他按捺下去,表示不接受他的请求;同时,不说一句话,只从樱桃般的小口里:“嘘——”的一声,阻止他说话和禁止他这种有碍病体的疯狂动作。
但是,奢伟先生却完全变成了任性的小孩,完全不肯听从大人的嘱咐似的,他在两条柔软的,但按捺在奢伟的病体之上,恰像两支铁腕的铁掌之下,拼命的挣扎,迷惘地继续大嚷着:“姑娘,那个勇敢得可爱的姑娘呀!”
然而,一瞬之间,他觉得,他的衰弱的身体之上,已失去了两支铁腕,再一瞬间,在他的面前,光明又忽然消逝,被无边无际的,深不可测的,高不可攀的黑暗统治了他,统治了这一位心头焦悚的,受着重伤的奢伟先生。
他苦恼,烦闷,心房里恰像有千头万绪无论如何不能彻底解决,无论如何无法梳理得清。而且,他眼前又是一片黑暗,又失去了可能扶助他的人。他孤独,寂寞,他苦痛地,喃喃地自言自语着:“姑娘,姑娘,易……”
奇怪呀!怎么灯光又倏地亮了!他费力地睁着眼,他认清了,在这病房中,除了适才的看护小姐之外,另外还跟随着一位,同样穿着白色外衣的男子,他,奢伟先生疑心是她去请来的,特地为了要援助他的人。因此,他又极声叫道:“帮助我,帮助我起来,我要去援助那个可怜的姑娘!”
穿着白色外衣的男子,紧蹙着眉尖,低低地向看护小姐说道:“思索过度,神经太衰弱了,只有替他再打一针……”
奢伟先生见她没有答话,仅仅连连地点着头。
他预备不顾一切,再向他们呼吁,不错,为了易红霞姑娘,他险些与密斯脱死神认了“郎舅亲”,如果她照旧牺牲在那个浓眉毛家伙的,无情的铁丸之下,他,他的奔忙,他的中枪,他的现在痛苦地,困兽似的被捆扎在这病床上,岂非一切等于“流水”?他要……
此际,他感觉到大腿上被蚊虫叮了一口似的,隐隐有些作痛;随着,他的脑海里,一切纷乱无序的思绪,都“逃之夭夭”了。
他的脑海里说是空虚,并不空虚,说不空虚,但是却一点什么都记不起来。他的意识已完全模糊,变成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了。
甚至,又隔了几秒钟,他的眼前的一切,也开始模糊了。他分辨不清,站立在病床面前的白鞋、白帽、白衣服,仅仅变成了一团白,扩大,扩大,模糊,模糊,扩大到,模糊到什么也不再可以辨认出来。
至此,他又昏昏沉沉,跌进了睡梦的境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