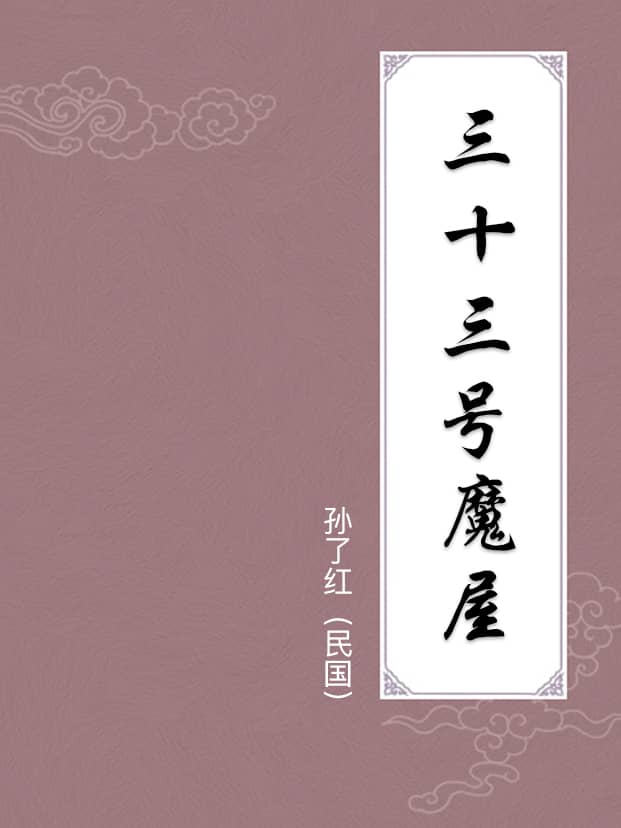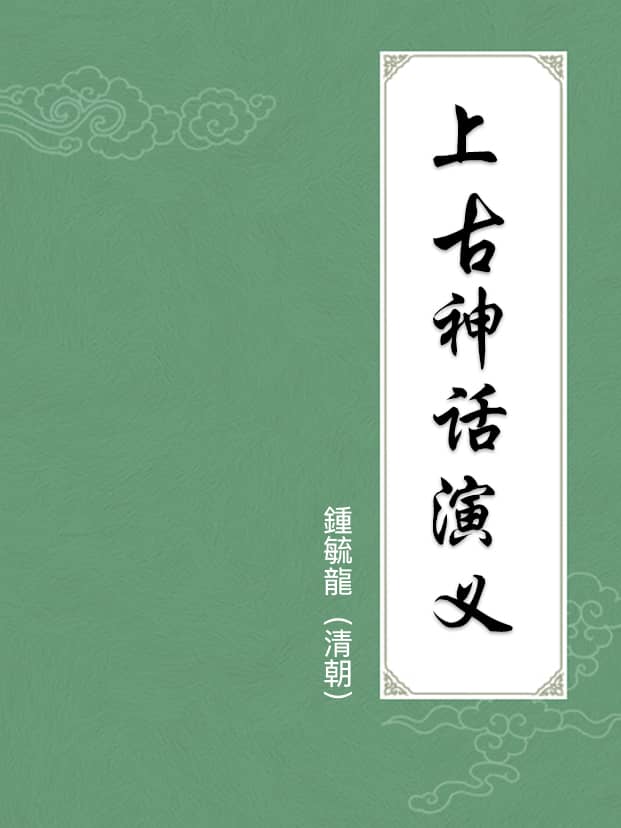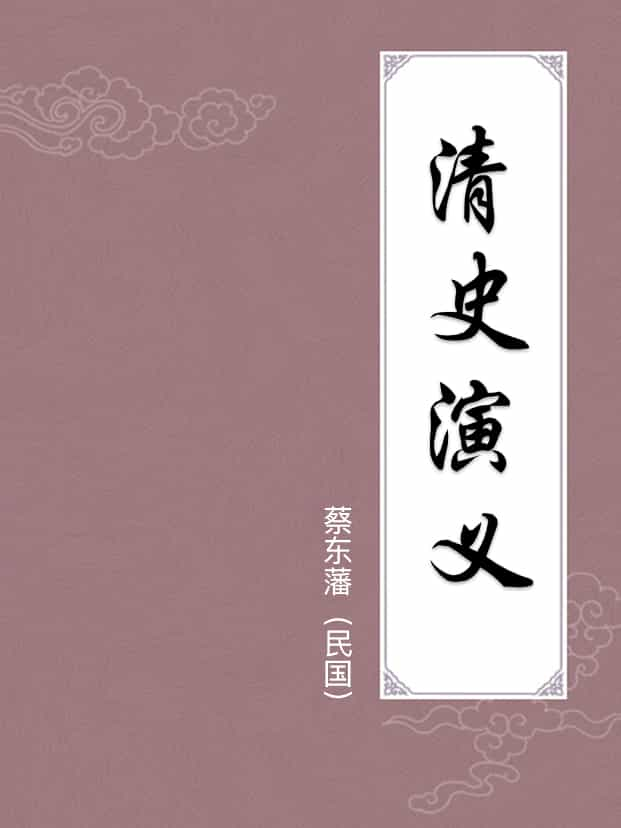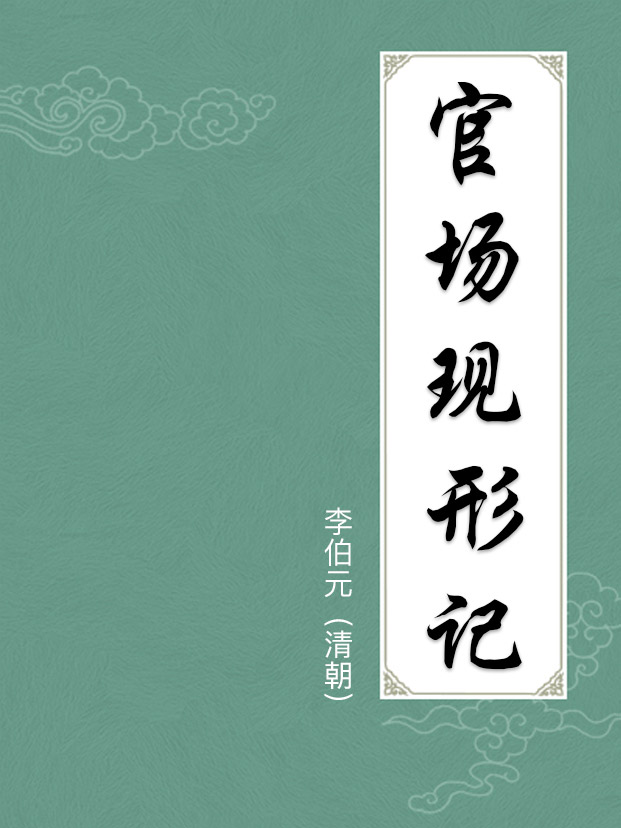萍村的事件,迅速地传到了鲁平的耳朵里。
鲁平生平,差不多可以称为“猎奇”的专家。他的猎奇,具有两种目的。其一:是为了消遣;其二:这简直也成了他的“专门的营业”。凡是社会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件,不论或大或小,只要稍带一些诡奇的意味,在他心目中,便认为这是发掘面包原料的机会来了。不过,他的探奇,也具有一个信条。他认为一件事情,最初在表面看看,好像是神奇无比的,而其结果,往往平常得很。所谓“雷声大,雨点小”的成语,在他过去的经历之中,几乎已成了一种定例。至于一件很小的事,凭他像解剖刀一样的智力,一经细细分析,却又每每会找出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这种例子,在以往有过许多。
萍村事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认为非常不可思议。唯有鲁平,却觉得并不足以引起他的兴趣。尤其那第二件事,他几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吃定那个女伶白丽娟,在那空屋里突然消失,是出于自动的溜走。她所以这样走法,不外乎要眩惑人家的眼光——也许,她就是在对她那位同来看屋子的母亲,在放着烟幕,也说不定——像这种事,他认为平常得无可平常,完全不值耗费他的思绪。至于第一件事,他觉得除了那个中年男子,在楼头的一声惨呼,略堪研究之外,其余的种种,也并不怎样神奇。总之,鲁平对于这所谓萍村事件,在最初,他并不想插身进去。
巧得很哪!在那时候,恰好有个医生,忽然嘱咐鲁平,说他的体力,有静静休养一下的需要。而鲁平自己,也感到在过去的三个月中,一则闲得发慌,脑子几乎生了锈;二则,他也觉得最近他的“生意”,实在太清,“进款”似乎有点不够。因着以上这两个动机,他想,不如姑且到这所谓“魔屋”中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大小生意,可以做这么一下。虽然他明明知道,问题的枢纽,绝不在那空屋里面,不过,即使找不出生意来,就遵了医生的嘱咐,顺便在那里休养一下,却也未为不可。
在主意决定以后,鲁平就以“画家俞石屏”的名义,径向萍村的经租账房,租定那幢三十三号的屋子。在第二天上,他就亲自押着一些极简单的家具,独个儿搬了进去。
所谓萍村也者,地方相当宽绰。在这村里,共有四十宅单幢三层的住屋,前后排成四个行列。建筑相当精美;屋中一切设备,也相当考究。三十三号一屋,位置在第三排。这屋子的二三层前楼,都装着法国式的落地长窗,窗外各有一座长方形的阳台。那后半部的亭子楼,容积比较普通住宅所有的略为宽大一些。这里也装着较狭小的法国长窗,开窗出去,却是一座月牙形的小型阳台。站在那里,可以眺望幽静的村道,和对面第四排的屋子——二三层的后楼,式样完全相同。这种结构,大体上和一般的普通住屋,似乎略有不同。
这里,笔者要向读者们请求,对于以上的情形,稍稍加以注意。因为,这和后面故事的开展,是有些小小的关系的。
鲁平在搬进三十三号屋的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把上下前后的各个部分,细细都察看了一下。不出他的所料,这屋子的内容,绝无半点异状。他觉得一个人会在这种绝无异状的屋子里突然地消灭掉,那简直成了一种可笑的神话;换句话说:那简直是绝对不可能与不会有的事。
“哼!这里面,一定有些可笑的错误在着哪!”这是他搬进这座屋子后的最初的一个意念。
不过,在巡视各室的时候,有一件小小的异事,却迅速地引起他的注意了。
他在三楼亭子间的地板上,找到了一张扑克纸牌;纸质还是簇簇新,显然并未被人用过。咦!在这一所还不曾有人住过的空屋里,这纸牌是哪里来的呢?还有可异的事哩!这纸牌的正面,是红色心形的三点;反面,也是红色心形的三点。原来是两张同式的牌,背对背粘合在一起的,粘合的手法非常精细,粗看,决不能看出这是由两张牌所并成。再细看这牌,那是一种用羊皮碾成的纸张所制造。他本是一个玩纸牌的“专家”,他一看这东西,就知道这是“808”的牌子,品质非常名贵,价值相当可观。况且,他想:在每一副的纸牌之中,并没有同花同点一样的两张,这两张红心的三点,当然是从两副牌内抽取出来而粘合成的。假使这里面并没有特殊的作用,大概绝没有人会从两整副的纸牌中各抽一张,而破费工夫把它们合并为一张。还有更可异的问题咧!这屋子的号数是“三十三”,而这两张纸牌的点数,恰巧也是“三”与“三”!这其中,会有什么微妙的关联没有?若说并没有关联,而仅仅是出于“偶然”,呵!像这种可怪的偶然,未免偶然得太巧啦!
这可异的纸牌,成了一种燃料,把他的兴趣,立刻鼓动了起来。他的敏锐的思想,从此便开始了忙碌的工作。可是,至少在眼前,他对这问题的端绪,觉得空空洞洞,还是毫无捉摸咧。于是,他暂时把这纸牌,小心地藏进了一个信封,又把这信封,郑重袋进了他的衣袋。
当天,他就在捡到这张奇异纸牌的三层亭子楼中,布置下一个简陋的卧室,独自住了下来。
第二天,他独自走到村口,借端去找那个司阍。他把一支上品的雪茄,恭敬地送给了这一位魔屋怪事的经手人。那支“上品雪茄”,轻轻撬开了这司阍者的嘴,于是,他们便开始闲谈,渐渐谈到了三十三号空屋中的第一次所发生的怪事。
鲁平在有意无意之间,把那中年男子的状貌、衣饰、年龄、口音以及突然不见的情形,逐一问得非常详细。据这司阍说:那中年男子在楼头的一声惨呼,他听得非常清楚,可以发誓说是绝无错误。而他在听到这呼声之后急急奔上楼去的时间,至多也不会超过十秒钟。在短短的十秒钟内,那样清清楚楚的一个人,竟会突然消灭不见——就算是一缕烟吧,那也不至于消散得这样快!这未免太可怕啦!
连下来,他们又谈到下一天所发生的事。这第二件事,在这司阍的嘴里,他简直把那个失踪的女伶,描写得如同一个穿着高跟皮鞋在天上闲逛而一不留神从云端里面失足滑跌下来的仙女一样!此公一味形容那女子的美丽,其余,却茫茫然地说不出一个肯定的所以然来。两人谈了半天,鲁平依然感到茫无头绪。好在他对以上的两件事,本来并不十分重视。暂时,他所念念不忘的,却是藏在他衣袋里的那张怪异的纸牌。
喂!你们以为那张纸牌的事,有些可怪吗?不错!当然可怪之至!可是,比这张纸牌更可怪的问题,还在后面哪!
当鲁平拜别了那个魔屋怪事的经手人,而从村口回进来时,他忽见有两个人,神情鬼鬼祟祟,在三十三号屋子后门口诡秘地张望。其中的一个,是四十左右身材高大的壮汉,戴着一顶深色铜盆帽,穿的是黑呢短大衣,下半身,露出着蓝布裤与黑皮鞋。此人生着一双三角怪眼,模样像是一个工人的头目。
另外一个人是青年,穿着蓝布工装皮鞋,面貌也并不善良。
这二人一见鲁平向三十三号屋走过来,便同时回身走开去。鲁平匆匆奔上二层亭子楼,轻轻开了法国式长窗,悄悄探头向下张望时,只见这两个人,向外走了几步,重复又回身进来,对这三十三以及左右两家三十二与三十四号的屋子,只顾徘徊探望。他们站了一会,脸上各各露出焦灼的神色。又看他们细语商量了一阵,第二次又返身向外。鲁平一见他们相偕走出去,他急忙自后楼奔到前楼,开窗走上阳台,看时,不出他的所料,只见这二人,又从后面的村道里,兜到了前面的村道里来。
鲁平偷看到那个穿大衣的壮汉,向着那个穿工装的青年挤了一挤眼,便走向三十四号屋子的前门去,按了一下电铃。只听他高高地喊说:“这里可是姓王?你们是不是要校对电表?”
“不是的,没有!”一个清脆而带厌恶意味的女人的声音,简单地从那三十四号门上的小方框里高声传送出来。
“咦!你们不是写信到电力公司来的吗?”那壮汉一边说,一边将一种饿鹰觅食般的锐利的目光,从这小方框内飞射进去。那小方框迅速地紧闭了起来。这壮汉又诡秘地向那个工装青年耸耸肩膀。看这情形,显见校对电表的话,完全出于假托。
这时,鲁平又见那个工装青年,踌躇了一下,似乎要来叩这三十三号屋子的门,恰巧那个壮汉偶然抬头,却和阳台上的鲁平打了一个照面。这壮汉便立刻闪动着他的三角怪眼,向那个工装青年投了一个暗示,似乎在阻止他的动作。接着,便见这二人重新又向村口那边走了出去。
鲁平看这二人的情形,简直非常可疑。他想了一想,决计追踪出外,准备细看一个究竟。他立刻走出三十三号屋子,急急奔到村口,他满以为这两个人,走得还不很远。不料,他向这幽静的马路上两面一望,早已不见了这两个诡秘人物的影踪。鲁平越想越疑,觉得错失了一个大好的机会,未免有点可惜。
于是,他懊丧地回进屋子。他在他的记事册上,把当天所见的事情,详细记了下来。
为了这两个可疑的家伙,引得我们这位神秘朋友,不时踏上这三十三号屋的前后部的阳台。
他以一种“哥伦布”站在甲板上面眺望新大陆的热望的眼光,不时眺望着下面的村道,准备着随时再有什么新的发现。
可是,三天的时间,匆匆过去了,下面村道之中,一直是那样幽悄悄地,毫无半点动静。这使他感到自己这种“守株待兔”的办法,未免拙劣得可笑。他正打算改换方法,到外面去活动一下。他刚自这样准备,却没有料到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完全出于他意外的枝节,从另一方面岔生了出来;这一种非常诡异的枝节,竟把他的预备向外活动的脚步,立刻拦阻住了。
笔者在前面一节文字中,曾清楚地向读者们报告过:鲁平在这三十三号空屋中所布置的简陋的卧室,是在三层楼后部的亭子间中。推开那两扇狭长的法国式长窗,便是月牙形的小型阳台。站在这里向外眺望,目光最易接触的,却是对方第四排屋子的前部;尤其劈面的一家,更容易映进眼帘。
这一家屋子的号数,是四十三号。由于季节的关系,那边二层楼上的法国长窗,不时开得很直。从这里三层楼上,望着劈面二层楼中的内容,因为居高临下,窗内的情形,可称历历分明。那是一间富丽堂皇的寝室,其中所有的家具,完全显着流线型;一切陈设,也都显示百分之九十九的精美。这简直是一座小布尔乔亚所住的瑰丽耀眼的小皇宫。在这小小的皇宫之中,常常见到的贵人,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大胖子。——看样子,这就是这间屋子里的幸运的主人。另外,还有一个瘦小的中年妇人,大约就是主妇。
以上的事情,看去很平常,似乎不值得加以详细的记述的。可是,唯其太平常了,其中却隐藏下了一种并不平常的成分。不信,请看以下的诡异的发展。
对方那座四十三号的屋子,二层楼上的情形,是记述过了。但是,三层楼上的情形,又怎样呢?
那里两扇与二层楼上同式的法国长窗,多半的时间是半开半掩,看不见室内的情形。但鲁平有一次,走上屋顶露台,望见对面三层阳台上,安放着一张铁架矾石面的长方小茶桌;两边,附属着两张小藤椅。这表示这三层阳台上,时常有人来憩坐。但鲁平自从搬入这三十三号空屋以后,却从不曾在这对方的三层楼上,见到过什么人迹。那里的二楼与三楼,是否为一家所住?却也无从知道。
在那两个可疑的工人模样的家伙,到前后村道里来窥探的后两天,鲁平忽然发现对面这四十三号屋子的三层阳台上,有两个漂亮的西装青年,靠着阳台栏杆,正向自己这边的屋子,在那里指指点点。——这两人的年龄,较长的一个,也不过二十多岁,另外一个,却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学童——两人脸上,都呈露着一种特异的神情。鲁平起初并不十分在意。但,约摸过了一小时后,只见对面这两个西装青年,第二次又踏上了这阳台。鲁平闪身在长窗半边,隔着玻璃斜刺里偷看过去时,只见这两人的神情,较前更显出了诡秘。其中年龄较轻的一个,不时举手遮着口角,扮出一种奇怪的鬼脸。那另外的年长的一个,两手插在裤袋里面,却时时沉下脸色,向他不住摇头,似乎在阻止他,不要做出这种怪模怪样来。
这两人站在阳台上,一面鬼祟地谈着话,一面却把四道可异的目光,连续不断地向这边飞扫过来。
这一次,鲁平发觉到这两个青年的眼光,并不像先前那样,专注着自己这边的屋子,同时他们也集中注意力于这里隔壁三十四号的那座屋子上。
这情形,使鲁平忍不住开直了长窗走将出去。同时,对面的两个青年,也正伸手拉窗,预备回进室内。只听得两人中那个年龄较长的一个,在用一种严重的声气,抱怨那个年轻的说:“你真不留神,要被你弄坏了大事哩!”
后者还未及对答前者的话,一眼瞥见这里鲁平踏上了阳台,便呀的一声叫喊起来道:“哦!你看!三十三号有了人!”
就在这一声非常惊怪的喊声中,鲁平发觉对方这两个青年,四颗闪烁的眼珠,正像机枪子弹那样向自己身上怒扫了过来!
以上连续发生的种种怪异事件,使鲁平的脑海之中,堆起了许多许多的疑云。连日的事情,姑且抛开那张第一天所捡到的怪异的纸牌,暂且不说。在两天之前,那两个工人模样的诡秘的家伙,曾跑到这屋子的前后左右,多方窥探。他们不但注意着这三十三号的屋子,而同时也注意着这里三十四与三十二号的邻屋,这已经大为可异。不料,今天对方这座四十三号屋子里的两个西装青年,也有着同样的怪异的情形。照这样看,这里萍村的屋子,不单是这座三十三号的所谓魔屋,大有神秘意味;甚至,连这前后左右的邻屋,也都无形地在散放一种神秘的辐射!
呵!这未免太可异了!真的,太可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