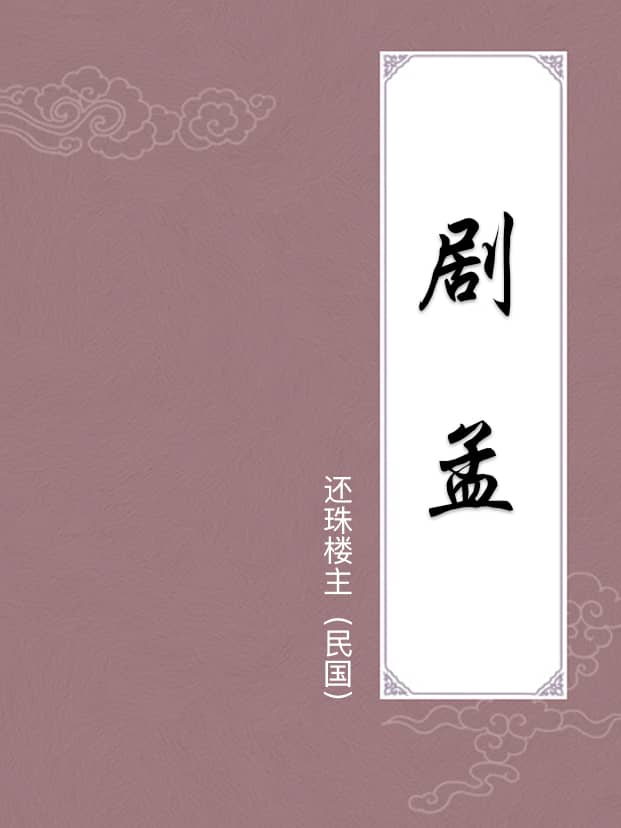四五月间,正是麦子成熟时候。斜阳光中,快要收获的麦子,吃初夏的暖风一吹,闪动起一层接一层的金色柔辉,晃漾起伏,波涛也似;而太华三峰又正当其前,灵石撑空,烟云缥渺,岚光如染,苍紫万千,越显得风景雄丽,画图不殊。
麦子成长到了这个时候,说熟就熟,分布在田野里的乡民,正在查看那些早熟的麦子,准备收割。庄稼长得这么茂盛,按说最少也有九成以上的年景,可是这些人十九面有菜色,衣不蔽体,有的壮年人还面有忿容,望着自己终岁勤劳所种出来的好庄稼在叹气。
这大片肥田沃野,由华阴南门起,直达华山脚下,都是南郊赵亭乡富豪赵家所有。主人赵他羽,是当地首富,手眼甚大,从朝中亲贵、富商巨贾以至江湖上的有名人物,多有来往;对于许多失势被贬的朝官,更多结纳,有求必应;本人又善于骑马击剑,家中养有不少江湖豪客。真个是有财有势,关内外没有不知道赵公子的。
赵他羽虽然结客挥金,人却沉着机警,非常精明,他认为该用的钱,脱手千金,从无吝色,不该用的钱,却是锱铢必较,决不轻舍,行起事来,又是刚柔并用,使人难测,手下徒党都把他奉若神明,不敢丝毫违抗。因为家财富有、服用华奢,又喜豪饮、赌博,还养有不少女乐歌姬,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声势煊赫,车马盈门。
前些日,朝廷因吴王刘濞装病不朝,却命使臣曹阳来京敷衍,便将曹阳扣住,严下诏旨,责问不已。赵他羽觉着奇货可居,一面托朝中亲贵照应;一面暗派党羽,买通监守人,将曹阳放走。曹阳逃出咸阳,便有赵家所派党羽迎护着往华阴逃来;同时,钦使朱原,也正奉命往见楚王刘戊传达诏旨,路过来访,都是午前到达。主人好饮,每餐至少要喝一个半醉,何况当天又来了这两位贵宾;午宴才罢,宾主三人都由美貌歌姬陪往午睡去了。
赵家门下众宾客徒党知道当日要大赌一场,由主人自作头家,醵金(凑钱,这里的意思是指抽头)夜宴,为这两位来客饯行,饭后无事,便先聚赌起来(这种赌法名为“摴蒱”,又名“五木之戏”,发源于老子,赌具乃坚木制成,约有桂圆大小,和现在的骰子形式相同,共是五枚,上黑下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全黑者为“卢”,得头等注,二雉三黑为“雉”得二等注,二犊三白为“犊”,得三等注,全白为“白”,得四等注。也有分刻“枭”、“卢”、“雉”、“犊”、“塞”等鸟兽关塞形象的。凡掷出以上四种彩色的便可再掷,名曰“打马过关”’以争取得最多的彩注。和后代的升官图掷法大略相同,今已不详。)
赌场设在一个广约五丈、深约三丈的大厅堂上,宾客徒党本就不少;这类场合,照例来若不拒,主人又不愿来客减了赌兴,款待既极周到,陈设尤为富丽,有那不请自来的富商豪客,赌后还要留宴,输得太多的还要赠上一些川资,设筵相送。因此门庭若市,热闹非常,呼卢喝雉之声,常与细细笙歌交作,响彻于外,直到深宵。
厅堂当中一座大屛风,三面门窗洞启,地上满铺锦茵柔席;屏风前面又是两丈多方圆一片绣毯,中心放着一个高仅四寸,约有六七尺方圆的木制大浅盘,盘内外均围有一圈二寸来高,一尺许宽的边沿,备赌客下注和放置银钱之用。
内圈盘沿上并画有黑白二色的图案,雕饰华丽,精细非常。环盘一圈锦垫,为头等赌客坐处(汉朝席地而坐,其坐如跪,今日本人之坐法,犹有汉之遗风)。头家座位居中,左右各有一人分执柄长数尺、饰以金银珠玉的长钩长刮,专管分注吃注之用;另外还有几圈软垫和上蒙文绣的木墩,由内而外,逐渐高起,按赌客的身份和下注多少来分等次。下注最少和一些无关紧要的党羽,都环立在最后一圈,所下赌注,又有专人代为传递,轻易不得近前。
厅堂正门又高又大,中垂五色绣幕,两边各有银钩挑起;门外大片白石平台,为女乐歌舞之地,台下设有两列茶档行灶,数十名豪奴分班伺应,专司饮食,堂上微微—呼,立用银盘捧了食物,鱼贯而上,日夜不断。势派之大,当时贵戚公侯之家,也不过如此。
日色虽已偏西,主人尚拥爱姬酣卧未起。赌徒不分贵贱,挤在赌盆旁边,攘臂狂呼,高喝“卢”、“雉”,乌烟瘴气,蚁聚在一起,连嚷带叫,喧嚣不已。就这紧张哗吵声中,两个穿着华丽的俊童,忽然狂奔而来,进门,连话都顾不得说,喘吁吁把手连挥,便自退去。
众人—见,当时停手,慌不迭抢起各人的注,按平日等第,站在各人席次之后;有的便忙着将方才挤歪了的软垫整理还原。满堂百余人,各按平日等第,退归席次,当时肃静无声,繁嚣立止。
主座两旁,专管分吃注的门落,刚将钩刮拿在手内,忽然瞥见众人皆起,盆侧绣垫上,却坐着一个生人,神态从容,若无其事。仔细一看,那人年约四十以内,中等身材,方面大耳,长眉俊目,红脸虬髯,手白如玉;头戴一领软巾,衣履均极朴素,但甚整洁;腰带上斜插着三条宽约一寸、长约七寸的木片,左胁挂着一个黄麻小袋,不知中藏何物。本想挥令离座,无奈主人曾经严嘱,遇见初上门的生客,不摸清他的底细,不许无乱,未便轻易发作;若不遣开,又恐主人出来嗔怪,好生为难。
内一门客笑问道:“尊客因何而来?若见主人有事,请那边坐。”
那人笑答:“我是来赌钱的。”底下便没有话。
门客见那人毫不知趣,脱口说道:“就是来赌钱的,这里也不是你的座位。”
那人笑问:“都是赌客,还分等么?”
门客忍不住方要发作,另一门客忙使眼色止住同伴,凑近那人身前,低声悄吿道:“靠近盘外一圈席位,都是主人请来的贵客,下注很多,尊客素昧平生,初次登门,不妨请到后面,先看—看,如果下注多时,主人自会请你入座。规矩如此,尊客请勿见怪。”
那人刚把面色微微一沉,忽又微笑道:“请问座位既分等次,赌注有限制没有呢?”
那门客道:“主人赵公子家财豪富,无论下上多少金银绢帛,赢了当时取走,去年有一无赖,来此扰闹,竟被我们打个半死……”
那人突然变色,不等话完,便笑道:“多承指教,我暂作旁观,如值当赌时,再下注罢。”说完便自离座,立向外圈木墩之后,一言不发。
二门客暗骂:“真个没有眉眼,料你也不敢不躲开。”
余人都暗笑来客不知自量,因主人就要出来,谁也没有理他,跟着便见一队美貌的歌姬,分持羽扇,由屏风两侧走出,先将预设的小铜鼎内的香点起,再将手中羽扇款款挥动,然后分列在主座之后。一时篆烟袅动,兰麝香浮,加上舞袖当风,笙歌迭奏,更平添了好些豪华富丽的景象。
又隔了一会,才见八个美貌少女前导中,由屏风左侧走出宾主四人,除曹阳、朱原外,还有一个有名人物,名叫田生,因由咸阳往南方去,路过当地,被赵他羽知道,命门客以盛礼相迎,强留晚宴,也是刚到不久。主人提早起身,便由于此。曹阳、朱原都是中年,各穿着一身华贵的衣冠,高视阔步,神情甚傲;田生年已五六十岁,貌相清癯,雍容雅步,很象一位山林隐士;主人赵他羽是个中年人,却生得猿背蜂腰,面如冠玉,浓眉丰额,高颧鹰鼻,笑口常开,神态非常谦和安详,那—双光芒内蕴的鹞眼,顾朌之间,威棱逼人,与众不同。
满堂宾客,本来鸦雀无声,恭恭敬敬排列成大半环,站在那里,这宾主四人刚一露面,忽然蚊雷聚哄也似,同声唱喏,拜伏在地。
方才那个不知姓名的生客,站在众人后面,旁观微笑,手都未举。众人正抢着行礼,那宾主四人也在答礼,谁也没有注意到他。
主人把手一挥,笙歌立止,宾主各按等次入座,笙歌又起。赵他羽略为客套了几句,从容回顾,嘴里似哼不哼地嗯了一下,立有一个年约十三四的美貌侍女,捧着一个玉盘,由主座后面走来,跪在主人面前,盘中一块小锦袱上,放着两粒一黑一白,方约寸许,上用黄金镶嵌着么二三四五六的骰子。赵他羽将这两粒骰子随手拿起,少女便行礼退去。
赵他羽把手上骰子微微颠了一颠,笑道:“‘摴蒱’之戏,我想大家都玩腻了,前两天定制了一个新鲜玩艺,取名‘色子’,这东西又可以赌单双,又可以赌大小点数,赌单双和大小都是一胜一,另外如押一定的点数,胜了可得九倍,以上都按所下赌金,连本抽二成的头。在座都非外人,由我来当头家,先赌大小点,以点多者为胜;今天因有几位佳客远来,特意设此博戏,以壮行色,头钱虽是按十抽二,比往常多了一成,我并不要,就是侥幸获胜,也将所赢的银钱全数奉赠这几位佳客,略表我们敬意。诸位如有雅兴,请快把注下好,我就要奉陪一试了。”
众赌客听了,都取出金银,下在赌盆内沿图案之上;隔得远的也有专人传递。
田生嘴皮微动,刚要开口,猛抬头朝对面人丛中看了一眼,忽又缩了回去。
众人下注之后,便按次序来掷骰子。头层人圈以外的赌客,照例只能附注,不能自掷,赌注也有专人传递,赌的人多,后来的赌客还在不断走进。―时呼单喝双声,骰子落盆跳掷声,赔注的多少声,以及赌客胜后哗笑之声,虽然吵成一片,秩序却是井然,有条不乱。
好赌人的心理都是赢了还要赢,恨不得把谁赢死,输了决不认输,那怕倾家荡产,也想翻本出赢钱。头家这样豪富,饮食设备,样样精美周到,单这一点,就符合了人们势利和享受的胃口;何况赌得那么心明眼亮,只要你有钱,就有赢的希望。
这么多精明会算计的人竟没有想到那要命的头钱只要几个进出,便会化为乌有。结果赢了的变输,输了的更是越输越多,输到赌友不肯再借,连头家也以婉言拒绝,劝他休息一会,缓缓手气,明天再说……表面仿佛是好意劝吿,并代不平,实则早看透了他的家底,知道再借永无还期,绕着弯加以拒绝。省事的垂头丧气,自认倒霉是便宜;再要老着脸皮苦口纠缠,头家一说出难听的话,就要自找无趣了。
内中也并非没有赢的,那都是赌得极精,不常下注,和在旁助势帮衬的赵家门客。此中奥妙,各有不同,赌客算是吃定了亏。不过是下大注的都是一些富商巨贾和拥有财产的土豪,家中可以取钱,主人又肯借赌本,输只管输,依然不肯停手,互相争胜的嚷叫之声,反比主人未出来以前还要火热。
曹阳、朱原明知主人为他抽头,还想混水捞鱼,就便赢上几个,好在慷他人之慨,自是乐得。于是越赌越起劲,也跟着攘臂喧呼起来。
赵他羽偷看田生干坐在旁,面前虽有自己给他代备的赌本,竟连动也未动,不禁暗中点头,一面令人把大量金银与曹朱二人不断送去作赌本。随手—掷,又获了个全胜,正在得意;忽觉众人吵得太凶,有些头疼,浓眉微皱,停手笑道:“诸位且慢下注,今天来客较多,这样赌法,仿佛尚欠文雅,输的人也难翻本。现在专赌单双,我以单为胜,诸位以双为胜,愿以点数多少分输赢的,庄家仍居单数,让下注人多占—点,押单双的不抽头钱,押点数的,因为头家吃亏—点,仍抽十分之二。诸位以为如何?”
众人同声赞妙。这些久赌的人因觉当日头钱太重,都押单双,不押点数。
赵他羽一因众人吵得太凶,又觉曹朱二人贪鄙惹厌,不愿锦上添花。反正胜败全在自己,有意把赢到手的钱再吐出去,不让这两人饱载而归,才改变了赌法。上来先掷了两个单,等把众人的赌火激发,下注越多,跟着好几次,连掷皆双,方才赢的钱便和水一样输出去,眼看所余无几;忽然瞥见众赌客固是兴高彩烈,皆大欢喜,田生也在拈髯微笑,曹朱二人却紧缩着眉头,目光注定在两粒骰子上,身手也在随同骰子起落,不住颤动,面容愁苦,精神紧张。当时心中一动,暗忖:“这两人一个是朝廷宠臣,一个是吴王心腹,虽然为人卑鄙,将来利用他们之处甚多,结交还来不及,如何令其失望?”念头一转,跟着就掷了几个单,把吐出去的钱又全赢了回来,比前更多。
曹朱二人知道头钱以外,主人赢的钱也是他的,不由心花怒放,喜笑颜开。
内一土豪输得太多,一时情急,意欲回家取上大量金银再赌。把手一拱道:“小弟还有一个约会,必须回家一行,少时再来陪诸位玩个通宵罢。”
赵他羽明知对方赌急,正想挽留,客套几句,那土豪已红着脸不等答话,气冲冲往外走去,只得罢了。
赵他羽刚刚坐下,忽听有人间道:“这样赌法,真是新鲜。方才听说,主人家财豪富,输赢大小并无限制,远来人爱赌如命,一时技痒,不知主人能容我这不速之客奉陪一试么?”朝前—看,并不相识。
左右豪奴见发话的正是方才站在众人后面的那个面生人,因主人正望着那人尚无表示,不敢过去,都干着急。
赵他羽见那人衣冠朴素,但是举止沉稳,谈笑自如,虽然觉出对方多少总有一点来头,但因自己这样大的财势威名,来人既未以礼求见,连名姓都没有说,开口便说要赌,并还暗含轻视之意,不禁有气,就佯笑道:“赌注大小,悉听尊便?不过远客光临,尚不知名;此是方才那位好友的座位,少时就要回来,恕我事前不知,没有安排好来客的坐处,只得有点对不起了。”
那人笑道:“主人不必太谦,逢场作戏,只要一决输赢,便自各分东西,随便站在那里都可,不将我摒诸门外,就足感盛情了。不过,初闻大名,所带金银无多,这里有一包散碎东西,聊作赌本,和主人赌—回点子多少,以博一笑罢。”说罢,便将腰间小黄麻袋取下,就土豪面前赌点数的图案上放好,然后从容退去。
众人都在忙着下注,笑话声中,赵他羽并未听清;又见那黄麻口袋不大,看去并不起眼,以为是些散碎银两,对方上来只是试手,自信必胜,毫未在意,也未命人打开;把骰子托在手上,颠了颠,口喝:“诸位看清!”手背微微往下一沉,业已贴近盘底,就势往外撒去。哒的一响,头一粒骰子,先由手指缝里落下,略动了动,先定了一个五点;同时另一粒骰子被大中二指掐住,随同往外—撒之势弹将出去,便顺着盘沿咕噜噜乱转起来。
下注的人都把全付精神注定在这粒骰子上,同声疾呼:“要单!”“要单!”
赵他羽大喝道:“非但要双,而且要六!”
那骰子渐渐定住,果然是个六,共凑成十一点,押单双的人全输。
曹、朱二人和众门客见这回下注人最多,头家大胜,都由不得喝起彩来。
专管吃注的二门客,因为一直没有人押大小点,十一又是单点的最多数,就有人押,也万难赶上,一持长钩,一持长刮,忙就盘沿四围钩刮那些赌注,准备二次再赌。
持长刮的一个正往里刮钱,忽然瞥见押点数的图案上,有尺许来长的一个黄麻袋,这才想起还有一个押点数的。心虽微动,因觉那人远方新来,穿着并不体面,心存轻视,依然随手刮去。
长刮刚挨近小麻袋上,忽听哈哈一笑,同时一道尺许长的寒光由斜对面人丛后,电也似急飞来,直射盘沿,夺的一声过处,—柄七寸来长两面开口明光耀眼的小刀,正扎在麻袋结口之处,深钉入木,震震有声!众人全都吃了一惊,靠近的人纷纷往后仰避,惊呼起来。
赵他羽见状大怒,方要开口喝问,一条人影已如巨鸟飞旗,由右侧人圈头上越过,落向方才土豪坐处,一看正是方才那个虬髯生客,笑嘻嘻望着自己,似要开口。那样急的来势,落地以后,却和原立在那里一样,神态甚是从容。他念头一转,不容对方发话,先朝左右二门客喝道:“你们怎么
这样粗心大意?那一注是押点数的,下注人还占有一个点的便宜,你没问明人家认输不认输,就吃注么?”随又转过面来,笑对那人道:“赌无大小,须要输个心服口服,含糊不得。我虽掷出最多的单点,下注人还有一个十二点可赶;这是我手下人一时疏忽,还望不要介意才好。”
那人仍是一张笑脸,安静静地等主人把话说完,微笑道:“我押的注不多,只是从来没见过这样赌法,想借此试掷一下,杀一杀手痒罢了。”说时,瞥见主人嘴皮微动,一个侍女便捧着一个玉盘,上托二粒同样的杀子走来,笑道:“我只掷一下,不必再费事了。”同时身子往前一探,便把盘中原有的两粒骰子拿到手里。
赵他羽一面挥手令侍女退去,冷笑道:“我望尊客掷一个十二点。”
那人拿起那两粒黄金嵌镶的骰子,暗中颠了—颠,接口笑道:“我赌了二十多年,这样金光灿烂的讲究赌具,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掷不出十二点,怎么对得起人呢。”说罢,先不出手,只把骰子在木盘里连抓连放,试了几次,仿佛很希罕的神气。
众人只当那人不知进退,少时定找无趣,均未在意。
赵他羽因这两粒骰子一轻一重,内中有假;又想对方是个孤客,下注不多,就算武功不差,凭自己的本领和手下这样多党羽,好说歹说,都无败理,所以明知来者不善,并未放在心上。为了表示大度包容,笑嘻嘻望着对方,先不答话。初意那人即使是个行家,至多和自己一样,会使手法,就是被他赢些钱去,等走之后,仍可命人追上,给他一些苦吃;不料事情竟出意外。
那人就盘里试了几把,忽然起立,笑道:“现在就要和主人—分谁胜谁败了。”说罢,一把握紧骰子,往盘里掷去。那掷法和寻常一样,并无异处;只是用力猛些,两粒骰子却在盘中,跳掷乱转,重的一粒跳了几下,首先现出一个六,轻的一粒猛撞在对面盘沿上反震回来,又落到盘中心滴溜溜乱转。
赵他羽方觉那人只是好赌,不象会使手法,忽听又像“六”又象“土”的低喝了一声,众赌客便喧呼起来。再往盘中一看,又现出一个六。心想天底下真有这样巧事,这厮居然掷了一个十二点。随笑道:“今天还没有人掷过满数,这位客人一出手就得了满点,实在难得,除原注照赔外,再加三成彩,略表微意罢。”主人的话讲了后,赔注的门客,立时应了一声是。
那人不等二门客问注多少,接口笑道:“能照我下的注照付,已足感盛情,加彩无须,请打开来点一点数目吧。”
赵他羽毕竟精明强干,闻言,猛想起此人说话有因,莫非这一个小黄麻口袋,内中装的不是散碎银子?心方一动,忽见一个门客已过去将那小麻袋一拉,袋口被刀尖划裂,袋内的东西立时随手激射而出,满盘都是银光乱闪,耀眼生花。定睛一看,原来那东西竟都是比黄豆还大的明珠,粒粒滚圆,一出口袋便满盘乱转,水银也似的,兀自流走不停,少说也有六、七百粒之多。这样光圆的宝珠,价值大得惊人,便把自己家财全部赔上,也难抵这一注。平日以“豪”侠自命,众目之下,绝不能说了不算,心里又惊又急,表面却仍装着镇静,强笑道:“赢了照赔,这没什么。不过,方才我们一时疏忽,没有看注,这许多的明珠,一时备办不及;多蒙光降,蓬荜生辉,小弟还未尽地主之谊,也太失礼。少时晚宴之后,便请尊客暂住寒舍,容我明日备好明珠,再行奉上如何?”
那人笑道:“我为赌而来,赌罢即去,输赢只凭一掷,话已言明在先,主人不能赔此—注,我也不会为此区区,作出那无赖行径,使满堂宾客见笑,素昧平生,座席尚且不堪承受,如何敢当盛宴,卧于宾馆?请命左右把原注代我收入袋内发还,再见罢。”
赵他羽才知来客是位非常人物,有意给他难堪。若让他收注走去,从此威名扫地,这脸怎丢得起;无奈这类明珠都是南海奇珍,就有万两黄金,也收买不了这许多,只得勉强陪笑道:“小弟向不食言,断无反悔,今日天色已晚,明日一定买来奉上就是。”
那人笑道:“微物戋戋,虽不足道,一时间恐也无从购买呢?”
赵他羽又急又愧,立时乘机发话道:“我们原赌的是金银,不是珠玉。因为手下人—时疏忽,你既得胜,自应照注奉赔,只要尊客宽限一时。如何逼人太甚?”
那人笑道:“你能赔则赔,不能赔我走,怎说是逼你呢?”
赵他羽那知对方恨他作恶多端,有意刺激,非要他现眼不可;闻言怒火越壮,喝问道:“你到底是谁?”
那人见赵他羽说时,把手微举,身后和左右的一群爪牙,便纷纷磨拳擦掌,怒目相视,大有动手之意,暗中好笑,从容答道:“远客路过,逢场作戏,只保赌本,何必留名。”
赵他羽闻言,实忍不住怒火,正要发作,旁坐田生早就认出那人是谁,因其暗中示意,又恨赵他羽横暴贪鄙,先不打算开口;后见双方针锋相对,一般恶奴爪牙都在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忽想起好汉打不过人多,那人本领虽高,孤身在此,难免吃亏。忙即起立,朝着那人把手一拱道:“请恕我年老眼花,现在才认出来,先生可是雒(洛)阳剧孟么?”
在场的人本就看得目定口呆,一听来人竟是洛阳大侠剧孟,俱知此人非但剑术高强,无人能敌,并且善于经商,富可敌国,自来济困扶危,疾恶如仇,名满朝野,为世推重。照此情势,分明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都代主人捏着一把冷汗,面面相觑,做声不得;赵他羽更似当头着了一下重棒,急切间不知如何是好。
剧孟还未答话,田生忽又瞥见陈县周庸,符离王孟,不知何时走了进来,也在后排人丛中出现;另外还有一些少年,都是貌相英俊,衣冠楚楚,腰间还挂有长剑,分列四外,微笑旁观。知赵他羽近年作恶太多,剧孟此来,事出有心,并非全无准备。心中一喜,意欲先声夺人,将在场的人先镇一下,以免少时动手,多伤人命。忙指王、周二侠,笑对赵他羽道:“原来符离王孟,陈县周庸二位大侠,还有好些位豪杰之士,也来在这里。你这当主人的竟未以礼款待,未免疏忽了些罢?”
赵他羽闻言,心中一震!同时瞥见外圈人丛中,果然站着好些生人,一个个英姿飒爽,气概昂藏,一望而知是些江湖游侠之士。久闻王、周二侠与剧孟至交,平日除暴安良,丝毫不留情面,最不好惹。似此大举而来,只管自己人多,决无幸理,那么阴鹜横暴的人,竟急出了一身冷汗,―张白脸也变成了青色。暗中正叫不迭的苦;猛一抬头,见剧孟一双英威炯炯的目光,正注望自己,满面笑容,依然未敛。猛触灵机,忙即起立,笑道:“我真有眼不识泰山。诸位大侠既然赏光,便是三生之幸。只要有诸位一句话,我赵他羽没有不认罪服输的。快请过来,容小子专诚礼拜,再请教罢。”说罢,命二门客将盘中明珠另用锦囊装好,交还原主;跟着一咬牙,便想朝剧孟身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