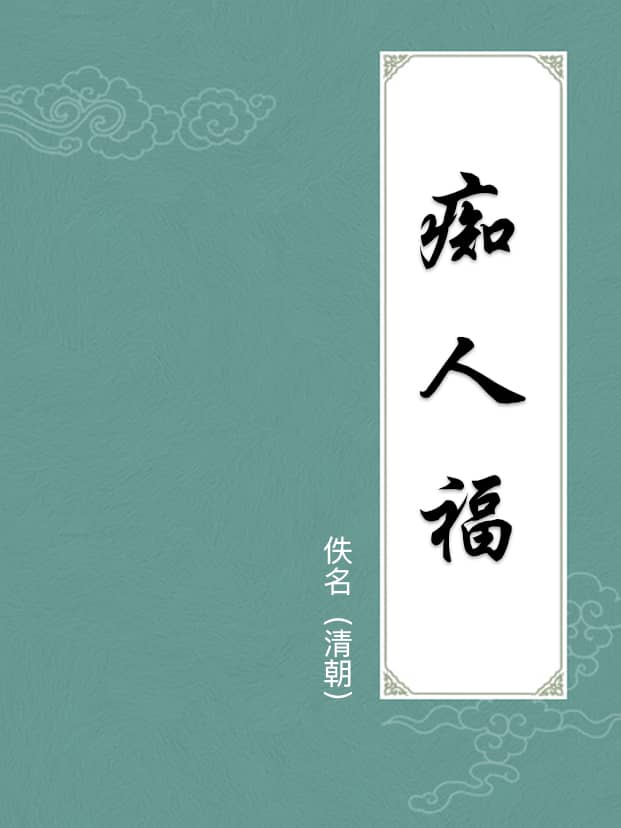众佳人爱洁翻遭玷,丑郎君怕娇偏得艳。
好童仆争气把功成,巧神明救苦将形变。
词曰:
多少词人能夺俪,还生演作风流剧。
美妇因而仇所适,纷纷邪行从斯出。
此番破尽传奇格,妍丑联姻真叵测。
须知此理极平常,不是奇冤休叫屈。
大凡世间,百千万亿止靠一天。而天自盘古至今,春秋鬲矣,不无龙钟暮景,设施布置,大都不合时宜。故今日之天,舍却“奈何”二字,别无名号可呼。
开辟之初,男女无心,忽然凑合,彼时妍丑二字料无分别。即妍者未必甚妍,丑者亦未必奇丑。
变化至今,炉钟改样,遂令美恶大殊,以致爱憎纷起。讵非造物者之过欤。
簇簇闺英,令其五官完具足矣,奈何夷光其貌,道蕴其才,既令才貌相兼,则当予以佳配。
即云至美难全,好物鲜并,亦当配一寻常男子。何蘧除、戚施之人,令人见而思避。
如田北平其人者,溺其珠而粪其玉,一之已甚,况复至再至三,颠颠倒倒,安得不以奈何二字加之!
非特此也。唐经略负命世之才,具掀天之手,即使佳丽成行,温柔作队,为风流侈糜之郭令公,亦未为已甚,奈何天绝坐失,拥嫫姆以终身。
韩解元抱怜香之素志,具冠玉之清标,使之永有丽娟,常餐秀色,为琴心独注之相如,亦未为不可。奈何觌面难逢,致王嫡之别嫁,田义貌邻潘宋,心并许张,使之生于贵族,早历宦途,畅所欲为,更不知作何竖立,奈何屈作人奴。正是:
胸前瑞云忽纷飞,眼底桃花终堕落。
鸾风乘风上碧霄,蛟龙获雨归丘壑。
嗟乎!每见奈何天上,英雄跻跻,才子跄跄,为唐为韩为田义者,不知凡几,特三女同居,为泪雨愁云之世界乎!
作此者,不知决几许西江之泪,喷多少南岳之云,濡墨写嗔,挥毫泄痛,于无可奈何处,忽以“奈何”问天,天亦不能自解。作者又代为解之,此红颜薄命之注脚所由来也。
世人不知,怪作者蹂香躏玉,蚀月摧花,演此杀风景之传奇,为挑琴、煮鹤者作俑,不知作俑者天,非人所能与也。天之作俑已久,亦非自今日始也。
却说先朝湖广荆州府,有一个富户,姓田,名唤北平,字万钟。父母早丧,自幼当家理事。父亲在时,曾与邹长史联姻,后来因父母亡过,居丧守制,不便婚娶,故不曾娶得浑家过门。
如今孝服已满,目下就要迎娶,因自说道:想我家自从高祖田九员外,靠着天理,做起一分人家,后来祖父相沿积德,所以一年好似一年,一代富似一代。如今到区区手里,差不多有二百万家赀,也将就过得日子了。只是一件,自祖上至今,只出有才之贝,不出无贝之才。莫说举人进士,挣扎不来,就是一顶秀才头巾,也像平天冠一般,再也承受不起。我也曾读过十几年书,如今倒吊起来,没有一点墨水,这也还是小事。天生我这副面貌,不但粗蠢,又且怪异,身上的五官四肢,没有一件不带些毛病。近有个作孽的文人,替我起个混名,叫做填不平。又替我做了一篇像赞,虽然太过刻毒,却也说得一点不差。他赞我道:
两眼不叫做全瞎,微有白花;面不叫做全疤,但多黑斑影;手不叫做全秃,指甲寥寥;足不叫做全跷,脚跟略点点;鼻不全赤,低稀微有酒糟痕;发不全黄,朦胧看似有沉香色;口不全吃,急中言常带双声;背不全驮驼,颈后肉但高三寸。更有一张歪不全之口,忽动忽静,暗中似有人提:还余两道出不全之眉,或断或联,眼上如经樵采。
你道这篇像赞,哪一句不真,哪一字不确?是但是这等说,我田北平,蠢也蠢到极处,陋也陋到极处,当不得我寓也富到极处。
“替我取混名,做像赞的人,自然是极聪明,极标致的了。只怕你没银子用的时节,全不缺的相公,又要来寻我这田北平的财主。田义,你是我得力的管家,一应钱财出入都是你经手。你说平日间问我借债的人,哪一个不是绝顶的聪明,绝顶的相貌?”
田义道:“大爷说得不差。”北平道:“任他才如锦绣,貌似莲花,只怕那才貌穷了来,没处去当。”田义道:“莫说别人,就是田义才貌昂藏,识字知书,怎奈这命薄,是个执鞭随镫之命。前日有相士说道:大爷是大高大贵之相。我问他,何以见得,他说大爷身上有十不全,犹如骨牌里而有个八不就,是难逢难遇的牌,就晓得十不全是极富贵的相了。”
北平笑道:“说得妙,说得妙。只是一件,富便是我的本等,那贵从哪里来?”
田义道:“自古道:财旺生官。只要舍得银子,贵也是图得来的。只要做些积德的事,财神比魁星更显应的。”正是:
乌纱可使黄金变,黑墨难磨铁砚穿。
田北平道:“我这一向有事,不曾清理账目,不知进了多少银子,出了多少银子,你可把总数说来我听。”
田义道:“一向房租欠账等项,共收起一万八千余两。昨日为钱粮紧急,一起交纳上库去了。”
田北平叹道:“你说到钱粮,又添我一桩心事。朝廷家里,近来窘到极处,只因年岁凶荒,钱粮催征不起,边上的军饷又催得紧急,真个无计可施。我这财主的名头出在外面,万一朝廷知道,问我借贷起来,怎么了得。”
田义道:“大爷你这句话倒也说得不差,近来国家多事,库帑尽空。田义闻得朝议纷纷,要往民间借贷,我家断不能免。田义倒有一个愚计在此,只怕大爷未必肯依。”
北平问道:“什么愚计,你且讲来。”
田义道:“昔日汉朝有个富民,叫做卜式。他见朝廷缺用,自己输财十万,以助军需。后来身做显官名垂青史。大爷何不乘他未借之先,自己到上司衙门动一张呈子,也做卜式的故事,捐几万银子,去助边饷。朝廷自然欢喜,或者天下一剿太平,叙起功来,万一有个官职赏赐,也不可知。这是一条青云大路,须要急早登程,不像那些纳粟求官的例,难得到手。”
北平道:“主意倒好,只是太过费了本钱。”
田义道:“大爷的田地房租,一年准有四十万。舍得一季的花利,就够助边饷了。欲要助公家的粮饷,须捐私囊,破余赀,往上司衙门呈状。”
北平道:“说得有理,却也亏你算计,倒难为了你一片心思,替我得便宜,也是一点忠良之心。”田义道:“替大爷补足生平缺陷的事。”
北平道:“我且问你,家主公的吉期近了,花灯彩轿,可曾备下了么?”
田义道:“都备下了,只等临时取用。”
北平道:“既然如此,你且退下了。”
田义道:“小人知道了。”
北平见田义去了,乃叹一口气道:“娶亲所用的东西,件件都停当了。只是我身上的东西,一件也不停当,将来如何是好?闻得邹小姐是个女中才子,嫁着我这不识字的丈夫,如何得她遂意。莫说别的,只是进门的时节,看见我这一副嘴脸,也就要吓一个半死,怎么还肯与我近身?近身不得,则那话儿越发不要题了。还有一件,我生平只因容貌欠好,自己也不敢去惹妇人,妇人也不敢来惹我,所以生了二十多岁,那些风月机关,全然未晓。自古道:色馒头也有三个口,生做亲的事,如何不操演一操演。我有一个丫环,名叫宜春,容貌虽然丑陋,情意总是一般。不免唤她出来,把那各样的风流套数,都把演习一演习,等待临期,好来选用。宜春哪里?”
宜春听得呼唤,便说道:“今日买来明日卖,将身卖与猪八戒。只道无人丑似我,谁知更有人中怪。大爷叫宜春出来,哪厢使用?”
北平见了宜春,笑道:“走近身来,与你说话,不要站在那边。”
宜春道:“有话便讲,何必一定要走近身来。”北平道:“因做亲的事从来不曾操演,我和你权当一权当,操演一操演。”
宜春推开,说道:哎喏,我从来不替男子做这件事,故此怕见男子的面。的风流,只求恩免罢了。
北平怒道:“丫头不识抬举,好看成你,反是这样装模作样,你难道不怕家主么?”
宜春道:“阿弥陀佛,这样的家主,谁人不怕,只为怕得紧,所以不敢近身。”
北平道:“你怕我哪一件?”宜春道:“大爷身上无一件不害怕,这副嘴脸,越发怕死人。”
北平怒道:“呔!你是何等之人,也敢来憎嫌我,欺负我!没有家法么?你这贱丫头,贼贱泼,敢出恶言来欺我,气得我力绵手软,也要打你几下。”
宜春便取家法,跪送求打,说道:“宁可打我几下倒好,那桩罪犯实当不起。”
北平道:“你要我打,我却偏不打,明日卖了你去。”
宜春道:“越发求之不得。便换一个新家主,那新家主九桩不全,也省了合欢时一桩不便。”
北平又笑道:“也不打你,也不卖你,只要把你权当做新人,操演一操演。”
宜春道:“你若放我不过,宁可到晚间上床,待我来伏侍你罢了。俗话说得好:眼不见为净。”北平道:“这等说,我就依你。”
既然妾面羞郎面,来时傍晚依成宪。
宜春又道:“你要我来,须要预先吹灭了灯,我方才来。若灯不曾灭,我是决不来的。你休把灯光耽误了姻缘。”说完便走进去了。
北平叹一口大气说道:“这等一个丑陋丫头尚且不肯与我近身,都要等吹灭了灯,方才肯就我。何况邹家小姐,是一个美貌佳人,还肯来近我的身?这一桩难事,叫我怎么样做?”
想了半晌,便道:“有了有了,宜春方才这些说话,分明是一个成亲的法子,明日新人进门,与我拜堂的时节,有银纱罩住了脸,料想看我不见。我等她走进洞房去了,就把灯火吹灭了,然后替她解带宽衣,颠鸾倒凤,只要当晚成了好事,到了第二曰就露出本相来,也不妨了。妙妙妙!这是丑男人成亲的秘诀,不可轻易就传授了与别人。若有丑男子不得成亲,来问我的时节,我便要他拜我为师,我才说这法子与他。”正是:
色胆虽寒计未穷,肯令好事暂成空。
良宵奠把银虹照,最喜相逢似梦中。
话分两头。却说邹长史,知道女婿的貌丑,忧虑女儿过门,不遂其意,便暗说道:—官姓邹,名先民,字无怀,由乡贡出身,官拜中郎之职。荆妻早逝,侧室天亡,常嗟伯道无儿,空抱蔡邕有女。下官只因宦途偃蹇,家计萧条,不以朱紫为荣,但觉索封可羡,所以生平止生得一女,不愿她做诰命夫人,但求为富室院君,但:生男不愁多,生女不嫌少,痴人幅不幸作中郎,订婚休太早。
山鸡与凤凰,雏时难预晓。
一旦惑冰言,终身误窈窕。
传言择婿翁,莫仪图温饱。
“只因当初在襁褓之中,田家央人来议亲,下官因他是个富室,只说是财主人家的儿子,生来定是有些福相,况且女儿又是婢妾所生,恐怕长大之时,才貌未必出众,所以一说便许,不曾看得,女婿长成,又是个非常的怪物,一字不识,倒也罢了。”
“不知天公为什么原故,竟把天下人的奇形怪状,合来聚在他一个人身上,半件也不曾遗漏。那田北平的名号,莫说通国相传以为笑柄,就是下官家里,哪一个男子不知,哪一个妇人不晓,刚刚瞒得我女儿一个人。下官明晓得不是姻缘,只因受聘在先,不好翻悔。今晚就是遣嫁之期了,不免唤她出来,吩咐几声,虽然不好明明说出她丈夫的丑陋,只好把嫁鸡随鸡的常话,劝诲她一番便了。”
吩咐家童:“叫养娘伏侍小姐出来。”
家僮随即传命,走入后堂,与养娘说知。养娘随即对小姐说道:“老爷吩咐家童进来请小姐上堂说话。”
小姐听说父亲呼唤,随移莲步,步出堂来。见了父亲,便道:“爹爹万福。”
邹公道:“罢了。你且坐下,听我吩咐。我儿你的女职将终,妇道依始。那四德三从的道理,经传载得明白,你平日都看过了,要晓得妇德虽多,提纲挈领,只在一个顺字。妇人家的德行,重在无违夫命,勉励宜室宜家,婚姻都是前生定。你的才称得妇魁,智可以解围。如今的女子,哪里有与你双配的!你爹爹做了一生的贫士,半世的冷官,没有甚么妆奁嫁你,你平日最欢喜读书,凡是家中的书籍,尽行把与你带去,到那忧闷之际,也好拿来消遣。况你无兄弟,把与你当做妆奁。”
小姐说道:“这些书籍孩儿已经看过多次了,都记得的,不必带去,留下与爹爹消闷。遣我自然有笥腹当做妆奁,又何必要这五车书在轿后推。旁人不知,只说我夸才华。爹爹你一向应酬的诗文都是孩儿代作,自今以后,代作无人,俱要自构思了。况高年之人,精力有限,如何应酬得来,毕竟文人孝亏,才人德微。倒不如那木兰武弁将爷劝替。你早知机会,把那笔砚封固了,省得费尽精神,把那寿命摧。”
邹公道:“良时已近,你可收拾起身。我先在中堂候你上轿。养娘你可伏侍小姐,收拾起身。田家花轿将近来到门了。”邹公复叹道:“正是:涕泪有如嫁齐女,唏嘘何异遣王娆。”
却说养娘奉了邹公之命,催道:“小姐,轿子到得快了,请来更换衣服。”
养娘替小姐换了衣服,便背着小姐,低声叹道:“可惜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嫁着一个田不全的丈夫。”
小姐道:“养娘你在那里自言自语,说些什么,”养娘道:“我不曾说什么。”小姐道:“我明明白白听见你唧唧哝哝的说出田不全三个字,还说不曾说什么?”
养娘道:“这等说来,小姐听错了。我说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正该配那田十全的丈夫。这是我替小姐欢喜的说话,小姐不要多疑。”
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文库小姐问道:“怎么叫做田十全?”
养娘道:“只因田家官人有十全的相貌,故此人家替他取了一个美名,叫做田十全。”
小姐听了此话,因暗喜道:“这等说起来,奴家幸得所夫了。这两三句说话,好似画出了潘安的美貌相来。”想想名不虚传,定无假话。
养娘道:“那霸王的夫婿,正好配着虞姬,耳目官骸,件件都是出奇。那些文人,逐件都题有像赞,何必猜疑。少刻间亲自相逢,自然知道真假高低。”养娘暗地又说道:“两个字不曾说差,只有一个字是欺哄你的。”小姐道:“正是:十年私意祝乘龙,羞对傍人问婿容。”
养娘听了,便回答两句道:“二人言名开笑面,愁看实际锁眉峰。”
却说闲话方完,只听得鼓乐喧天,竹歌嘹亮,一篓时,灯烛辉煌,银缸灿烂,从仆数十,拥护着一乘五彩花轿,迎人中堂。
邹公着家仆进来说道:“叫养娘伏侍小姐上轿。”
养娘扶了小姐,轻移莲步,出到中堂,参拜了家先,辞别了邹公。二人哭泣分别了一会。傧相读罢词文,催扶小姐上了花轿,鼓乐迎出大门去了。且住说邹公之事。
却说田北平,自打发花轿鼓手迎亲去后,说道:“我今晚的佳期,与世上人的好事,有一半相同,也有一半相反。喜的是洞房恼的是花烛。怕近的容颜,喜沾的皮肉。所最爱者是倩兮巧笑;所最恶者兮美目。美好,人之所同;恶丑,我之所独。世上人的才貌,也尽有似区区一般,自己不知,反道是潘安宋玉。到成亲的时节,不肯遮盖,惹得新人痛哭,还要凌辱阿娇,逼她死于金屋。怎似区区,不昧良心,或者将来还有些厚福。想起来又好笑,我田北平成亲的着数都摆布停当了,只等进房之后,依计而行。不免吩咐丫环,教她帮衬帮衬,可不是好。宜春在哪里。”
宜春听得呼唤,便道:“郎君件件奇恶,原只道有那一着,谁知本事又平常,空有牛形无力作。你今晚成亲,有替死的来了,又叫我做什么。”
北平道:“有桩机密事与你商量,你须要帮衬我。我与新人拜堂之后,恐怕她嫌我丑陋,不肯成亲。我要预先吹灭了灯,然后劝她脱衣服。你须要会意,不可就点灯进来。”
宜春道:“你这个计较,是极好的了。我还替你愁一件。她的眼睛,便被你瞒过了,只怕鼻子塞不住。你身上那许多气息,你有什么法子,遮掩得住么?”
北平道:“我身上没有什么气息。”
宜春道:“原来你自己不觉得,这也怪不得你,你身上有三件臭气。”
北平道:“哪三件臭气?”宜春道:“口臭、体臭、肢臭。”
北平听了,痴呆了半晌,便说道:“原来如此。你若不说,我哪里知道。这怎么好?”
宜春道:“这也不妨,只要你晓得,就好作弊了。脚上那一种做一头睡,自然闻不见,不消虑她;身上那一种,是从肋下出来的,你上床时节,把手夹着些,也还掩饰吹灭了花烛,我与你除去环簪,解去衣带,没了灯光,则索把罗裙解了,早上牙床,把那做新人的俗套,一并抛脱罢了。”
便把邹小姐搂抱上床去了。
不知后来如何识出田不全的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