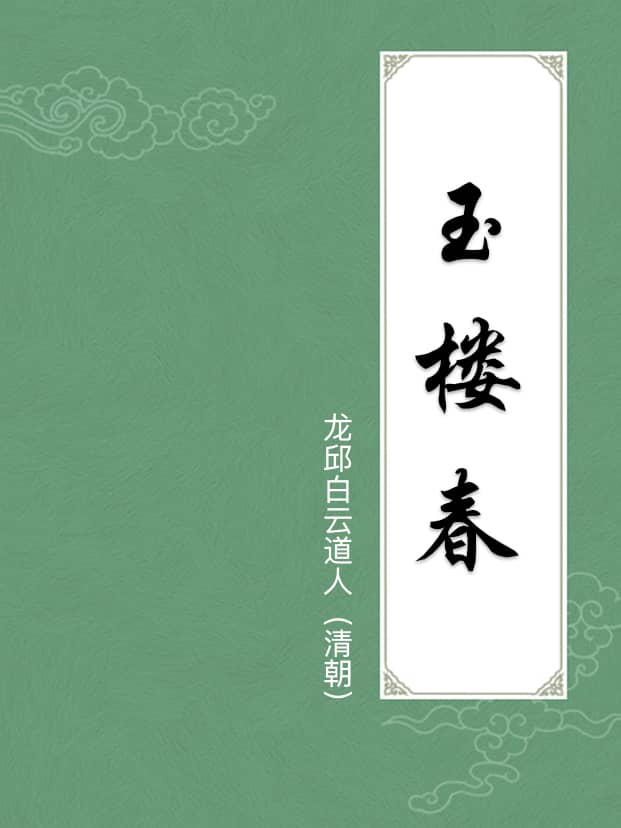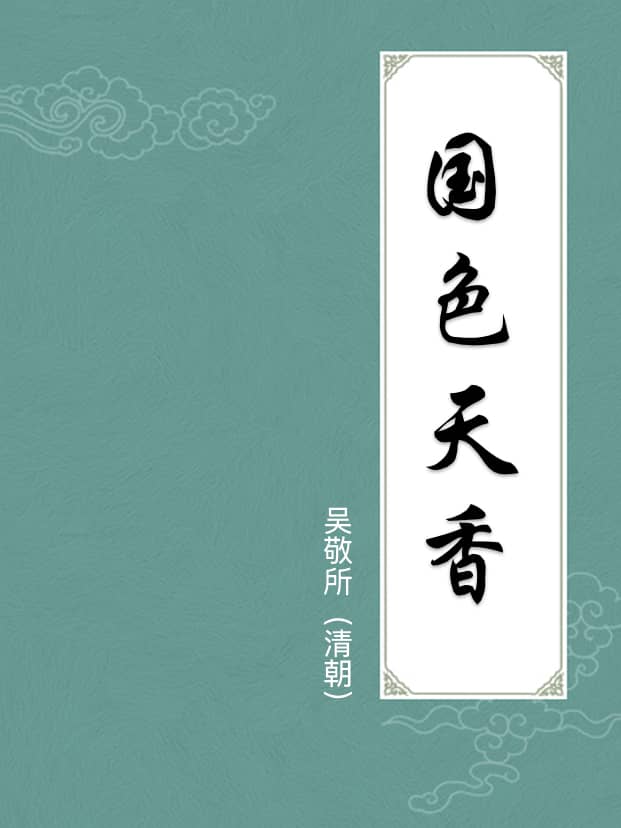话说嘉兴西门内乡绅黄缓,字汉侯,庚戌进土官拜太宰,致仕在家。止生一男一女。男名唤黄钺,是个目不识丁的蠢货,年二十二岁。女郎玉娘,生得容如西子,才若班昭,诗词歌赋,无不精通,黄尚书夫妇爱如异宝。她是十月望日生的,自幼舍名福寿庵白衣大士前。故每岁生日,送二十两香金到庵里,母子两个必定来庵中拜佛,做一日功德。是以十四晚庵中忙忙收拾纸扎。十五日早,一群家人妇女护送黄夫人和小姐,两乘轿子进庵来。庵主慌忙出迎到正殿上,参拜了三宝诸佛,各处拈过了香,方才人斋堂坐定。献茶罢,起身闲步。诸尼自去札佛拜忏,单是悟凡棚陪黄夫人、小姐,同到她房里闲玩。十州躲在内里一个侧厢下。夫人一路闲一人来,十州在纸窗洞边私窥那小姐,果然生得有些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十州看出了神,不觉失声称道:“好个女子。”却被这些跟随妇女听见,便说:“呀,那壁厢谁人大胆在内窥探?”早有三人推开厢门,一看,三个妇人吃了一惊,也失声赞道:“好一位仙女。”惊动了黄夫人,问道:“你们为什么事大惊小怪?”家人妇女走近面前禀道:“这壁厢藏一个佳人在内。”
夫人便问悟凡:“此内之人,是何宅家眷?”悟凡不敢隐瞒,把昨日来踪述了一遍。夫人道:“这是个落难的女子了。可请她来见我。”那家人妇女走到厢下唤道:
“大姐,我家夫人请你。”
文新遂缓步出来,到悟凡房里。黄夫人同玉娘举目一看,见她仪容袅娜,举止端庄,神如秋水。文新行到夫人面前,众妇女喝她叩拜,倒是夫人道:“不消。”反要尊以远客之礼。彼此推逊了一回,黄夫人只得依了,小姐不肯占。文新道:“夫人小姐是金阙玉质,贱妾乃茅屋微躯,怎么敢占客礼?”必要推小姐在上。见礼过了,夫人与小姐将她周身细细看了,不但容貌推绝,而且言词温雅,不像小家出身,只是一对金莲略粗了些。夫人问她贵姓氏,文新道:“贱姓文名新,年方十五岁,洛阳人氏。”
夫人因适才悟凡把她来踪说过了,便不再问,命她同坐。文新取了一张椅子,在下面朝上坐了。悟凡献上茶来,吃了几杯。黄小姐偶然去悟凡书桌上闲看,看见一幅白笺,压在砚下,将手去拿起来看,上写五言绝句二首。
其一日:
薄命轻如箨,秋风任飘泊。
来去无定踪,未卜何所托。
其二日:
客夕乘舴艋,今宵蹴招提。
萍踪失巢鸟,谁借一枝栖。
洛阳薄命女偶题于长水之福寿庵。
文新见黄小姐取那纸起来看,连忙走来拿时,早被她看过了,不好去夺,只得任她阅完。那小姐连声称赞道:“诗字俱佳。”就呈与夫人看。夫人看了道:“诗句清新,字迹端楷,真乃才貌双全的女子。可敬可敬。”
黄小姐暗想道:“我只道女中才子惟吾与翠楼两个,不想此女如此大才。若与翠楼两个合作一处,外貌内才,岂不是状元榜眼探花?可惜她是个女子,若是个男子,我与他结连理之枝,遂于飞之愿,岂不是天生一对才子佳人?”心下已有相爱相怜之意。黄夫人见了女儿目不转睛视她,已晓得女儿爱她之意,“我何不便与老爷说知,收留这女子与女儿作伴?”及至黄昏,功德作完,老尼进来陪吃晚膳。临散时候,黄夫人拉道白到外边,私与她说要留文新到府里相伴女儿之意:“待明日与我老爷说了,着人来接她。”道白满口应承道:“在我身上,老尼到明日早造府回复夫人便了。”黄夫人同小姐与文新作别,便有一种依依不舍之意,不得已上轿,二簇人飞拥地去了。
道白走到悟凡房里来,就将黄夫人的话,对文新说了。文新道:“只恐贱妾不中她意,若黄夫人肯留,贱妾愿同翠楼一同服侍小姐便了。”
道白欢喜。明日清晨就到黄府里来见夫人。先谢了昨日所赐厚仪,然后把文新之意回复夫人。夫人甚喜,小姐在旁便喜之不胜。遂令人放轿到福寿庵,接文新姐进府。原来昨晚回时,夫人即将此话达知太宰公,又把那幅诗与太宰公看了,也称道不已。故夫人一等道白回话,便着人去请。顷刻问家人来报说,福寿庵文新已到了。夫人命道白接她入内,叫丫头去书房里请老爷进来相见。黄公一见,心中也想:“世间有这样绝奇女子,与我女儿相去不远。”道白领她上前见礼。黄公夫妇受她两拜。小姐受了两个小礼又唤翠楼过来相见。黄公就吩咐侍茶,自往书房里去了。这道白用过点心,遂辞回庵中去。
翠楼领文新到小姐闺房中。原米玉娘的卧室是一座绝高的楼房,楼后又是一大间!是二面开窗阁子。两旁边还有两间披楼,一个六十余岁养娘,另横一个在左边。披楼里掩上楼门,竟是个鸡犬不闻的仙境。楼上书籍满架,古帖名画,不计其数。文新举目一看,真好个名人书窒。四壁俱是玉娘与翠楼的题咏糊满。到得晚上,老妈送上夜饭来吃过。玉娘看了一黄昏书,然后去唾。翠楼移烛引文新到自己床前来道:“新姐不嫌不洁,当奉陪同榻了。”文新笑道:“姐姐说哪里话来,只恐作妹子身上不洁净,不敢有污玉体。只是同床各被睡吧。”翠楼道:“妹子不须讲客话。我姐妹两个从今就是亲骨肉一般,大家都不用客气,倘妹妹若有独性的毛病,我和你合被各单睡如何?”文新道:“甚好。”要让翠楼在内床睡。翠楼只得先上床,坐在里面。文新一头脱外面衣服,一头把自家一本诗集去镇好桌上。翠楼看见便问道:“妹妹是什么书?”文新道:“是名人涛集。我平日喜欢他的文字,所以当时在身边,闲时观看的。”翠楼道:“可借我一观。”
文新便取来递与翠楼,翠楼接书一看,却是雪梅的二集,上写长安邵十州着,有小牙章印在上面,是风流解元四个字。翠楼惊道:“这不是小盂尝的郎君,号邵有二的么?”文新道:“正是,姐姐缘何晓得那人?”
翠楼道:“我家老爷有个门生,去年往长安带得一本雪梅初集下来,送与老爷,说是长安一个秀才所作,年才十三岁。老爷看了,十分称道,遂即送与小姐。小姐持来看时道,字字珠玑,言言锦绣,恨他不得生在本县,有个相见之期。今年又见乡试录上中了第一。但不知他外貌何如,只是见他诗文奇妙,每每形诸想念。常时对我说道:‘我若嫁得这个才郎,死亦瞑目。’所以晓得他。不知妹妹何处得这稿儿,还是他亲手写的?还是抄录来的?”文新道:“就是此解元的真迹。你看他笔法秀雅,便可想其风流气象了。”翠楼道:“这般说来,妹妹必曾见其丰采了。”文新笑道:
“他就是我姑表兄,时常亲见。他容貌是男子中当今无二的,只是他要觅一位美貌佳人,方肯成亲,所以至今,十五岁尚未聘室。”翠楼道:“小姐终日诵他诗文,尚未知他人物何如耳,若是听见妹妹这一番话,还要欢喜杀了呢。”二人直谈至五鼓,方才就寝。翠楼见他不脱小衣,问道:“妹子如何穿了挎子睡?”文新道:“我是自幼犯了寒疾,每年到十月时分,便不脱里衣而睡。”翠楼信了,大家睡去。
到天晓起来,翠楼拿了那本稿儿,走到玉娘床前来笑道:“小姐有件宝贝在此。”玉娘道:“有甚东西,如此欢喜。”翠楼把文新的话说了一遍,然后把那本稿儿取出。玉楼接来展开一看,是雪梅二集。真个字字珠玉,兼得书法尽妙,即忙披衣起来,叫文新来问。文新之言,从头一样。玉娘大喜,又问道:“那邵郎既未聘室,他如今在家可有说亲的来么?”文新道:“家表兄近来朝中有事,他已远游到南边来了。”玉娘忙问道:“你可晓得他望南边来还向哪一方去?”文新停了一会道:“不知他往哪里去了。”玉娘也不再问,及梳洗毕,把这本雪梅集读了又读,口中吟咏他文词,肚里又想他是个风流才子,一时间着魔在十州身上,连早饭俱无心去吃,呆呆地拿在手里细看,不忍放手。到得晚上,玉娘有心要与文新打得热闹,好趁机问十州的消息。
吃晚饭时,玉娘自己坐在上座,叫翠楼文新坐在两旁。玉娘提起壶来,亲手斟一杯酒,送到文新面前来,文新便起身接了。玉娘道:“我敬你这杯,非为别意,难得你三四千里之外,有缘相会。名虽有上下之分,情实骨肉之爱。自今以后,你我三人生死同心,大家如姐妹一般,倘有负心,杯酒为誓。不知你意下如何?”文新道:“贱妾受小姐提携,得备员奴隶足矣,又焉敢结为雁行。自今以后,当腹心上报小姐,次报翠楼姐,倘有少欺,鬼神是鉴。”也斟一杯酒,敬上玉娘。又斟一杯酒,奉与翠楼。翠楼也敬她一杯,然后大家坐定。玉娘道:“今日不许拘束,要饮个尽兴。”彼此讲古论今,饮得有兴,讲得有味,所谓酒逢知己干杯少,不觉城楼已敲三鼓,此时玉娘已是十分醉倒。翠楼被文新连陪数杯,不觉大醉,睡在椅上。玉娘叫文新扶她去睡,文新道:“服侍小姐先睡,奴辈方好出去。”
玉娘依她,便去解衣上床。文新先已替她打扫床内洁洁净净,铺设帐褥,又去替她放下帐钩,说声小姐好睡,便来扶翠楼到床上来。文新叫道:“姐姐脱下睡罢。”怎奈翠楼如玉山倾倒,和衣倒在床上,蒙咙睡去。任文新推动,只是叫不起来。
是夜天气又极寒冷,文新恐翠楼酒后伤风,故把锦被拿来,罩在翠楼身上,自己却去剔下银缸,拿了一二卷书,在灯下披阅。转眼四顾,见翠楼房内玉签牙边万卷纷披,文房四宝一栩,罗列十分齐正,把玩不置。及至玉楼叠推,漏下四鼓,翠楼酒气少退,转动起来,见文新尚在灯下观书,便叫道:“新姐,天气寒冷,到此时候,何不睡罢。我晓得了,你想是中个女状元么?”文新道:“女状元,贱妾却不敢,还是让小姐、姐姐中罢。前在福寿庵曾闻悟凡言及小姐与姐姐诗名,如雷贯耳,一邑之中,文人学士,无不钦服。文新于此道,却亦路暗,尚欲请教一二,姐蛆其许我否?”翠楼道:“请教何必一时,日子可待。夜色已深,睡罢。”于是文新吹灭灯火,行到床上,和翠楼拥衾而睡。只因这一睡有分教:文新百年之好,于此而谐;翠搂抱稠之愿,由是而始。而熊梦亦自兹而吐焉。欲知后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