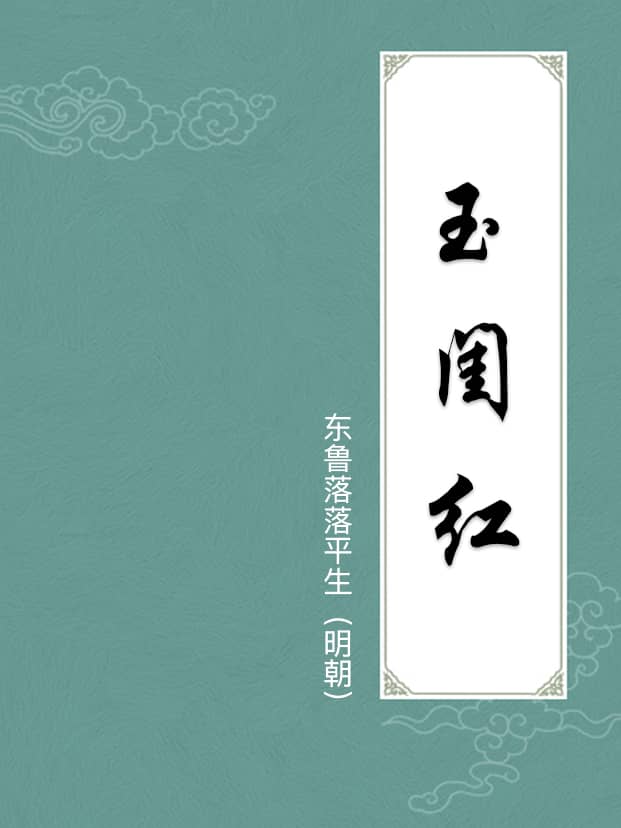诗曰:
红艳枝头花正浓。那禁一夜妒花风。
晨起落红飞如雨。不堪卒听杜鹃声。
话说小姐自从府中逃出,在长街上彷徨了一日,同红玉失散,被吴来子骗卖到小白狼手里,遭了顿毒打,又寻了回死,已是疲惫不堪。自从初到张小脚家里,进了一点饮食以后,滴水未进,眼泪不干。又因夜里自尽未成,索兴躺在炕上不吃东西,预备绝食自裁。
到了晌午,那小白狼笑嘻嘻的进来向张小脚道:“好了,方才我找他们可费了事。最后在雨来茶棚碰见吴六哥、刘大哥,还有胡四哥,连上赵三哥,一共五人,今天晚上也够热闹了。快些备饭,等晚上还有好吃的呢。”
张小脚依言,在炕洞上将饭作起。是一锅小米粥,十个窝窝头。又叫小白狼去买了两块碱菜,二人狼吞虎咽的吃了一顿。把那剩下的窝头,小白狼送至窑子里给赵三同姑娘们吃了。
这里张小脚指着小好道:“死bi!还不快同你姐姐把粥吃了。”
小好道:“方才给他,他不吃呢。”
小脚道:“不吃哪行,一会儿晚上就要来了,吃了饭才能够盯着。”
小脚便过来向躺着的闺贞拉了一把道:“你吃不吃?”小姐两目紧闭,僵卧不动。
小脚怒道:“你这不识抬举的丫头,我看你是找死。”
正好小白狼走进门来,问道:“什么事?他又惹你生气?”
小脚道:“他不吃饭,。一会儿那能有劲盯着干?我看让我替她灌下去吧。”
小白狼道:“正好,这不识抬举的东西,恐怕扒着嘴还填不上呢。”
小白狼即过来将小姐抱起按住,问小姐道:“你吃不吃?”
小姐闭目流泪,摇头不语。惹得小白狼兴起,喝道:“给我灌!”
张小脚取过木勺,盛了一勺热粥,小白狼将小姐的玉鼻捏住,小姐不由的樱唇开张。张小脚乘势将一勺热粥倒了下去。小姐出其不意,啊咳不止,那热粥滚下喉咙,烫得痛彻心肺,从口角溢出。烫的玉肌生疼。小姐娇弱之体,哪里忍受得住?不禁一劲挣命。
看官,一个娇弱女子能有多大力气。那小白狼真力如虎,小姐文风也动弹不了。张小脚又盛了一勺热粥,预备再灌。只听小姐告饶道:“别灌,奴家我吃了。”正是:
恁你铁般强,也要刚化为柔。
小白狼放了小姐说道:“这也得吃了罢,不听话还有厉害的呢。”
小姐整整衣服,凄咽咽把那点小米粥吃了。郤仿佛长了点精神。小姐这两日连受奔波,发髻已散乱不堪,衣服也多有皱撸。面上更不用说,被眼泪抹得花黑一片。
吃完了午饭,张小脚便过来替小姐梳妆。小姐才受荼毒,不敢违拗,横了心任他作去。小脚先解开小姐的青丝,只见发长委地,不由的心意又妒又羡。梳了梳了,施了自家平常舍不得用的桂花头油。那张小脚虽然风月,郤对于宦家的髻儿挽不上来,没奈何替小姐挽了两个大抓髻在头两边,倒也别有风味。见小姐头上尚有金钗一枝,小脚顺便掳下戴在头上。
不一时梳头已毕,吩咐小好打水净手,又替小姐净面。那小姐如木雕泥塑死人一般,任她作去。净完了面,小脚将铅粉用唾沫和了,涂了小姐那白嫩脸,直涂得那娇生生白嫩嫩弹得破似的小脸都看不出了,方才住手。又取过胭脂在小姐两颊上涂了两块猴屁股。小姐被铅粉煞的面皮生疼,也不敢言语,任他摆布。不一时梳洗已毕,揽过半块铜镜与小姐照。小姐一看,大吃一惊,想道:“这是那里来的妖怪,雪白满脸上印着鲜红的两块胭脂,两道蛾眉变了粗黑,小樱唇涂得腥红,仿佛吃过死孩子。”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也不敢言语。
当下无话,转瞬已是掌灯时分。小白狼、吴来子、刘虎、胡二等,都一齐来了。那刘虎一见,哈哈大笑道:“七弟,你那里弄来这样好看的女娘?叫咱一看,那裤裆就不由得不得劲儿。”
小白狼笑道:“大哥,少不得也要陪你睡几回呢。”
吴来子道:“这全是我的功劳,要不是我,就凭你们这几块,到哪里去寻得这样好的女娘?又赚钱又过瘾。要说赵三上回找的那几个,别说是三吊,六文钱人家还都嫌贵了呢。”
胡二道:“别说了,要不是我用车给拉了来,你们找谁人拉去?”
吴来子道:“难道除了你,京城就没人赶脚了吗?”
小姐低首坐在炕角,面红过耳,低头不语。
正在说笑,张小脚啐了一声说道:“你们别嚼舌根子了,天到这般时分,门掌柜的还没有来,也许他嫌贵,那三吊到手的钱恐怕要飞了吧。”大家登时一怔。
只见房门启处,走进一个长大汉子,面如锅底,气喘吁吁。一手提了两个纸包,那手中郤拿了一只竹篮,内盛四碟小菜,一壶烧刀子。众人一看财星到了,慌忙迎接。门掌柜向众人了拱手道:“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多劳诸位弟兄助兴。”
小白狼道:“事还得你自家干,俺们也帮不了什么,不过大家凑个热闹而已。”张小脚将三吊钱和酒菜篮子接过,吩咐小好在炕洞里烧起柴火,烧水暖酒,又蒸上几个窝头预备下饭。
那小姐起初低首独坐,任人嘲弄,不敢抬头。及至听见门掌柜来,心想:“这就是说的那人了。”不由的轻启睐目,偷看过去。只见黑粗高大,满面麻斑,像个凶神。骇得心惊肉跳,心想:“今晚是逃不出这厮的侮辱了,倘若这样将父母清白的遗体,破坏在这粗暴的胚子手里,不如及早寻个自尽,落个清白。”
小姐正想着,忽听张小脚道:“酒已热了,都围在炕上吃罢,你看人家门大爷都等不及了。”又向小姐道:“人家门大爷今天破费了银钱,赔上了身子,来给你成人,怎的一声也不言语?快过来给门大爷磕头见个礼儿。”
看官请想,小姐乃千金之体,岂肯给下等人磕头,只当没听见一般。
小脚喊道:“你耳朵敢是聋了吗?”众人听得这条破裂嗓子一喊,都怔着了。那门老贵好不羞耻,面红过耳。
小脚益发冒火,吩咐小好道:“去到炕头上将那皮鞭子取过来。”小好依言取过。
小脚握在手中道:“你磕不磕?”小姐一见皮鞭子,就吓得四体战栗,战战兢兢的向着门老贵跪了下去。含了泪磕了四个头。
门老贵慌忙扶起道:“我的宝贝儿,一会儿我还替你成人,和你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咧,何必行此大礼。”小姐羞愧难当,掩面啜泣。
小脚道:“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笑还笑不够,哭个什么?”小姐一看小脚的鞭子还在手中,随即止声,依旧躲在炕角,心中盘算自尽之法。到了这时,也只有碰壁才能不被人拦住。可是那室中四壁尽是泥土涂墙,碰在上面顶多掉下几块泥皮,也不会碰掉半点柔皮。
小姐正在无方可想,那边张小脚已将酒烫好。把门老贵拿来的一碟拌黄豆芽、一碟碱豆腐、一碟小葱、一碟粉皮,都安置在炕心,说道:“快来喝吧,酒菜都已齐了。”
胡二道:“今天大喜的日子,想那赵三哥整天每日的忙,也该一同来喝一盅。再说现在只有门大爷一人有女娘陪伴,俺们也该找那几个姑娘来陪陪才是。”
小白狼道:“这很好,我也想要连赵三哥请来。”
吴来子道:“连骚姐、色姐也都叫了来吧,陪这一会也少赚不了几个。”小白狼立时跳下炕来,往外走去。
在窑子门口,只见里面雾气蒸腾,拥挤不动。赵三正抱了一个瓦罐向那里边放钱。小白狼道:“买卖不干,大家吃酒去吧。”
只见一个汉子恶狠狠的回过头来说:“什么?我已经等了够一个时辰了,下回就轮到我,难道就白等了吗?”
那骚姐杨氏正在忙着,一听以为又在催促,百忙中喊道:“等一等,快了,还没有最后缴枪。待我使他快些。”
那人怒道:“怎这半天还不行?”
小白狼再看刘玉环时,也是正在占身。旁边还有三个等着的,都已经把衣裤脱尽,屌儿直直的挺着。
赵三悄悄拉了小白狼一下道:“钱都收了人家的了,难道还能退回去吗?你们有酒,不妨送到这儿弄一份来吃。”
小白狼道:“等一等完事再带她们去吧,待我给留点酒菜。那刘大哥他们还要他俩去陪睡呢。”赵三点头。
小白狼回来,围团坐下。没有酒杯,便就壶嘴而饮。猜拳行令,好不热闹。闺贞小姐也被拖了过来,就坐在门老贵的旁边。酒过三巡,都有了一点酒意。
胡二道:“你们看门大爷同这女娘,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
那门老贵被奉承得心迷意醉,便揽过小姐的粉颈道:“小宝贝儿,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恁的不吃口酒?”
吴来子道:“对了,小姐你也该吃一杯交杯酒,你那死鬼爹妈可曾替你寻个汉子来过?”
这边门老贵将酒壶送到小姐樱唇,小姐粉颈低垂,两目含泪。老门性子一急,便将小姐的玉鼻一捏,提起酒壶灌了一口下去。小姐觉得又苦又辣,娇声干咳不止。
正在这时,忽见草门启处进来两个女娘,全都如白鹤只只,赤身露体,精赤条条一丝不挂。一个年约三十余岁,皮肤黑嫩,怀抱小孩,也是裸无寸丝,偎在怀中喂乳。
那一个二十多岁,皮肤白净,si处红肿,兀自滴滴搭搭,阴mao湿漉。后面跟一个男人,鬼鬼祟祟。
众人一见齐道:“赵老三,等你好久了。酒菜还热呢,快来吃吧。”那三人便过来就席。
小姐一见,大吃一惊,心想:“这两个妇人如何这般的没廉耻,就说烟花巷中,也没有赤身露体和许多男人陪酒之理。”
那杨氏见小好,小好见了杨氏,母女相会,心中凄恻,郤不敢则声。当下杨氏挨了刘虎,刘玉环挨了吴来子。又吃了一会酒,都已有些酒意发作。将那两个姑娘搂着,挽舌吮乳,秽亵不堪言状。小姐被老贵拥住,欲挣不得,好在还穿着身裳,没受怎样羞辱。
只听刘虎道:“今天是新人成人的日子,新人也得唱个曲儿给大家取取乐。”小姐摇摇头。
老贵道:“敢情是不会唱吗?”
吴来子道:“他乃名门闺秀,诗词歌赋无一不晓,那有不会唱之理?”
张小脚道:“你既是会唱,就唱一个吧,不唱可又要看鞭子伺候咧。”
小姐被逼无奈,只得轻启朱唇唱道:
愁锁淡春山,泪洒颊边。天涯肠断恨难填,教人羞煞深闺面。侬辱难言。
唱毕,老贵道:“不佳,不佳,我一句也不懂。倒不如骚姐唱的曲好,又动人又好听。”
说罢,叫杨氏唱。杨氏唱道:
喜煞奴家,乐煞奴家,哪人有奴福分大。
一天到晚入洞房,新郎换他十来个,把钱与奴花。
肏bi搗眼真好受,独眼和尚沾着上来酥麻。
不愿作人家。只愿朝朝暮暮在花下。
杨氏唱毕,众人喝采叫好。又叫色姐唱,刘玉环唱道:
叫声哥哥,你使劲肏,休把奴膛透。
奴家为你把命丧,你休来把别人逛。
别看六文不打紧,小妹对你好心肠。
口里哼着香舌舔,还招架舞动刀枪。
就是你把奴家的下嘴喂得飽香。
二人唱罢,众人酒已吃毕。那四碟凉菜能有多少东西,也被几个人如风卷残云一般吃个精光。这晚老贵欢喜非常,得意忘形。且在这种地方,便毫不客气的搂过小姐粉颈,向那樱唇上亲了个乖乖道:“我的好人,怎么尽不说话?敢是也等不及了吗?”小姐叠次受辱,积愤已深。这一下更是平生曾没受过,不由大怒,也顾不得皮鞭子的厉害,顺手向老贵的黑粗脸上打了一个嘴巴。正是:
怒从心头起,羞上粉颊红。
老贵被打了一下,更是抱住小姐死不放手。小姐拚命的乱挣,别想动弹分毫。
张小脚向老贵道:“此时不下手,等待何时?”
老贵慌忙将小姐一提,抱下炕来。众人也离了坐,吩咐小好将炕收掇净了,又将草席铺上。小姐仍然还在老贵怀里挣命。
小白狼道:“门大爷你只管自家歇等,这丫头交给我收拾吧。”
门老贵依言放手,小白狼便同刘玉环二人将小姐按倒在炕,下手与他宽衣解带。小姐拚命不从,直剥得小姐娇声哭喊。不一时小姐已身如白羊,浩浩乎裸无寸缕。众人一看,不由都喝起采来。只见:
肤似羊脂,乳如椒发。
白生生遍体似玉,香喷喷全身如绵。
更难得是骨肉停匀,恰容怀中一抱。
最堪怜如羊羔初生,足够美味一喻。
真个是出浴杨妃,落水仙子。
任你铁石心肺,一见犹怜。
凭那真柳下惠,也要魂销。
小姐被剥得赤条条一丝不挂,羞得无处藏身。双手难掩丑处,恨不得地上裂一条缝跌了进去。只有缩成一团,那玉臀白嫩,尻骨隆拢,也都在众人眼目之下。羞愤欲死。
张小脚道:“门大爷请上来吧。”那门老贵早已把衣服脱好,露出一身鱼鳞般的黑皮,挺屌兒走上前来,要将小姐翻转过来。
那双铁爪般的粗手,才一沾小姐的玉肌,小姐又大声娇哭起来。门老贵性子急,使劲将小姐扳将过来,横架在炕沿上。小姐益发撑拒,惨不忍闻。这里众兄弟拍掌叫好,外面也听不见小姐哭声。
老贵一动手,小姐便如风引洞箫娇呼。惹的老贵性起,心想:“今天晚上倘事不成,我那三吊铜钱岂不白花了。”便双手捧定屌兒,照準bi縫便肏。
小姐到了这时,见已无可如何,只得含泪哀求道:“可怜奴还是女身,不曾破过肉的,从容些则个。”
那老贵那里肯听,腾身上去,大喝一声,整根肏進。小姐叫了声“啊呀”!只见他粉面死灰,星眸紧闭。
张小脚道声:“不好。”
叫老贵道:“你别动。”连忙取过一卷草纸点着了,在小姐鼻子上薰了两薰。
小姐已是悠悠醒转,娇喊一声:“痛死奴也。”
那老贵心疼三吊铜钱,欲火正炽,哪懂得怜香惜玉?挨开两股,径将膫子耸动。无奈小姐黄花幼女,含苞未放,门老贵一心为了捞本,根本不知憐花惜玉,只是一味蛮肏。小姐瞪目蹙眉,咬碎银牙,极力忍耐,遍体生津,额角上香汗像黄豆般大。
待门老贵兴尽精泄,霎时绿暗红飞,丹流浃席,云收雨散。大家过来向老贵道喜。小姐已是奄奄一息,伏卧在炕上。张小脚取过被子与他盖了。
老贵心里惦记买卖,告辞回去。
这里小白狼道:“大哥该是你了。”
刘虎道:“让来子先上去吧,是他领来的,怎的不叫他尝鲜呢。”
吴来子依言,遂到小姐身傍道:“小姐,我来肏你了。”
小姐知道是他,只道不知。那吴来子一面肏,一面又小姐长,小姐短说个不了。小姐只是紧闭两眼,装作死去。
吴来子道:“小姐你怎么了?”小姐不答。
又道:“小姐你可也知道这有汉子的乐处?”小姐又不答,吴来子没趣,胡乱了事。
接着上来胡二,又换刘虎,那小姐黄花之体已经三人,受创不堪。何况刘虎又是伟男,不由的双目圆睁,口中频呼饶命不止,声如猿啼。那小好吓的躲在炕角,面如土色。正是:
倾盆暴雨摧娇蕊。无边狂风折嫩芽。
要知小姐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