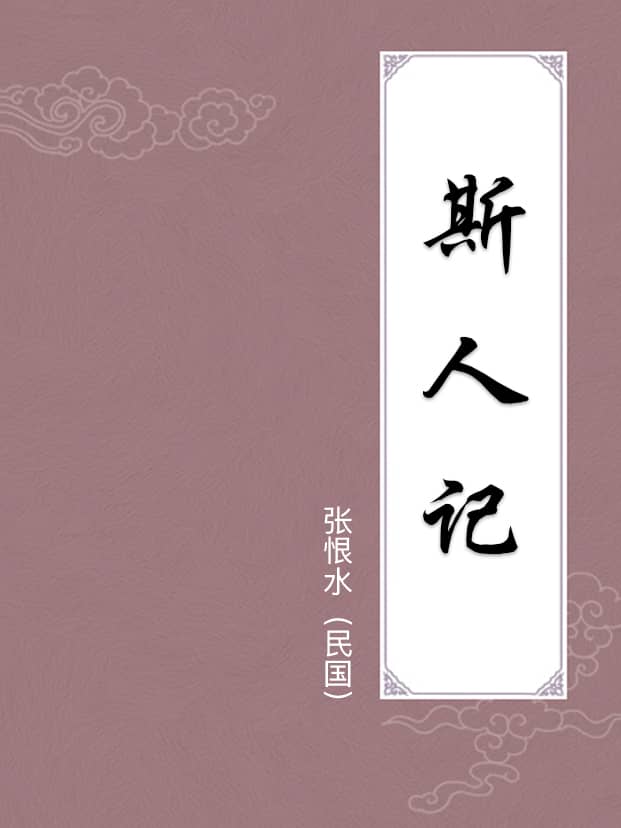果然在这个时候,薛爱青因今天没有戏,是清闲得很,正手上拿了电话机,和人打着电话。听到老妈子说有一位贾先生来会,便向电话里笑道:“别说了,我来了客了。”
停了一停。又道:“你可别瞎说,人家是很客气的朋友,挂上吧。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吧。”
说毕,将电话径自挂上,就到前面客厅里来,见着贾叔遥,因笑道:“让您久等,真对不住。”
贾叔遥道:“刚刚到,并没有多候,我知道薛老板今天无事,所以过来谈谈。这两天看什么小说没有?”
薛爱青道:“这两天跟着夏老板学两出戏,简直没有工夫看书。”
贾叔遥道:“夏老板倒是一个热心朋友。”
薛爱青脸皮一红,顿了一顿,然后一笑道:“要说他帮我忙的,那可帮大了。不过这也就止于朋友交情而已。有几家小报上,前两天,造了许多谣言,说是我们要结婚,这可成了笑话了。坤伶拜男伶的门,那有的是。况且现在社交公开,男女交朋友,都是不成问题了。”
贾叔遥道:“我这话问得冒昧一点,夏老板也知道这事吗?”
薛爱青笑道:“你是个文明人,怎么也说这话。我瞧报上和杂志上,外国人那些女明星,常常就有报馆里人当面去访问她的婚姻问题。”
说到这里,她又微笑一笑道:“我虽然比不上那外国的明星,可是情形总是一样。问上一问,那要什么紧?”
贾叔遥笑道:“既然如此,我就敞开来问了。夏老板虽然谈不上婚姻问题,他对于薛老板难道一点爱情也没有吗?”
薛爱青笑道:“若是据我的意思说,我觉得要论爱情,还谈不到。至于夏老板的意思,或者他会连想到爱情两个字上去。可是真要这样办下去,我们的友谊恐怕是要受影响的。”
贾叔遥一听,心里暗想,这位姑娘,总算大方到极点了,对一个平常的异性朋友,却肯把这种话都说了出来。
薛爱青见他立刻没有话答,似乎在想什么,便笑道:“贾先生你想我这话有点不对吗?”
贾叔遥笑道:“不是不是。我想到夏老板对薛老板那样热心,恐怕不是没有缘故的。只可惜他是早有家眷的了。要不然,倒也算是郎才女貌。”
薛爱青笑道:“大概外面人都是这样猜吧?不过不过……不过……”
她说到此处,沉吟了一会,又微微一笑道:“可是很奇怪,我对于他,尽管觉得待我很好,可是一点爱情之念,也生不出来。”
她说到这里,就搭讪着把面前的茶杯拿起来慢慢地呷茶。
贾叔遥一想,这个问题,不宜再讨论下去了。因道:“听说薛老板又要到汉口去,是吗?”
薛爱青放下茶杯,在胁下掏出一条紫手绢,在嘴唇上按了两按,笑道:“要论到成绩,大概是在汉口的成绩最好了,不过我不愿意。那里有几位捧角家,真有点死心眼儿。”
贾叔遥道:“大概银行界的人……”
只说了这句,心里不由得想起来,刚才自己觉得说冒昧了,怎么又把这种话直截了当的说了出来,因之突然顿住,偷看了一看她的颜色。
薛爱青笑道:“倒是有几个银行界的人捧我的场,后来我回北京,恰好又有一个银行经理同车,这话传到了北京,又不免满城风雨。老实说一句,惟有我们吃戏饭的人,行动最容易让人注意。像贾先生所问我的话,我早已知道了。而且外面所说的话,恐怕比贾先生所说的还要过分十倍哩。”
贾叔遥见她都是这样直率答复,却也不好再问了。因道:“有一个会作诗朋友,想来见见,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特意让我来为之先容。”
薛爱青笑道:“这个欢迎之至。是贾先生的朋友,哪还有俗人?何必还用先容呢?”
贾叔遥听她今天说话,痛快极了,很是欢喜,正还想谈些什么?老妈子来笑着说:“有电话请薛老板说话。”
薛爱青道:“叫他回头再打电话吧,我这里有客呢。”
贾叔遥一看那神气,料定是夏秀云打来的电话,自己很不必在这里久坐,耽误了人家的情话,便起身告辞。薛爱青笑道:“没关系,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贾先生难得来的,来了也不谈一谈就要走。”
贾叔遥只笑着,也不说什么,已经就走出客厅门了。薛爱青因他已坚决地表示走,也就不必再留,只送到院子门,就不送了。
她回到上房,电话耳机正挂在一边的钉子上。她于是接过电话来问道:“你这人怎样了?叫你等一会儿再打电话,你还是等不及。你这一打电话不要紧,把我的客也给催走了。”
那一边就说:“客走了很好,我来陪你谈谈吧,你可别出去。我来了,你要是不在家,我非等着你回来,我是不走的。”
薛爱青笑道:“你爱等到什么时候,你就等到什么时候。等急了也是活该。”
说毕,就把电话挂上。
可是真不到十五分钟,大门口一阵汽车喇叭响,这就是夏秀云到了。他下车走将进来,他也并不要什么通知,一直就向上房而来。他隔着帘子先笑着嚷道:“客来了,让进来吗?”
薛爱青笑道:“你这不是废话,我不让进来也得成呀!”
夏秀云这就打着一阵哈哈,自掀了帘子进来笑道:“刚才是一个什么客?让我一个电话给轰跑了。”
薛爱青笑道:“不是捧我的,是一个报馆的人来谈戏的。”
夏秀云一面说着一面坐在薛爱青附近一张椅子上,两手扶了椅子靠,两脚向地下一伸,人向椅子背上一靠,伸了一懒腰,望着薛爱青笑道:“也不知道怎么了,这几天是真倦。”
薛爱青道:“这一个礼拜,你也没上台,为什么倦?”
说着话看他时只见他穿着月白印度绸夹袍,外套青纱花马褂,真个是黑白分明。因笑道:“穿这样漂亮的衣服,你就是这样随便地躺下,你又不怕坏了你的衣服。”
夏秀云笑道:“我只顾着和你谈话,什么也都忘了,你信不信?”
薛爱青望了他一眼,什么也不说,抿嘴微微一笑。夏秀云道:“我知道你总不肯相信我的话。”
薛爱青笑道:“我又没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不信你的话?”
夏秀云笑道:“一个唱戏的人,从小儿就学的是做手做脚,岂有看不出人家脸色的道理?”
薛爱青笑道:“不要胡扯了。今天你规规矩矩坐在这里把娥媚将军那出新戏,给我说一说吧!”
夏秀云笑道:“你一个聪明人,这句话可说得有一点过于老实。人家正说我丢了事情不干,教你的戏。我们应该避一避才好,干吗还要把我自己编的戏让你去演。以后你要学戏,还是让我给你说些老戏吧。”
薛爱青道:“我糊涂吗?你才糊涂呢?你教给我的腔调,你教给我的身段,上台一演出来,都像是你唱的一样,不唱你的新戏,人家就不知道吗?”
夏秀云道:“你这话也有理,不过一唱我新编的戏,那就更明白了。今天我一不来说戏,二不来聊天,我想和你一块出去溜达溜达,你赞成不赞成?”
薛爱青道:“我正想在家里休息,你又要我出去?像上次和你到汤山去碰到了熟人。多不方便。”
夏秀云道:“今天去的一个地方,无论是谁也不会碰到的。我有一出带外国味儿的戏,快要唱了,我想到印度洋行去买点印度绸来作行头,这件事儿,倒没有你在行,你替我去挑一挑好不好?”
薛爱青笑道:“那也不见得。不过我也想去看看,倒可以给你去作一作参谋。”
夏秀云一听说,马上站立起来。将那顶巴拿马草帽戴在头上,说道:“最好是就走。”
薛爱青笑道:“瞧你穿得这样花花公子似的,我不换一件衣服,就好意思和你一处走道吗?等着吧。”
她于是进房去,从从容容地换衣服。
夏秀云在外面屋子等了许久,不见她出来,在院子里走走,走了一会又进屋子来,进了屋子来复又出门,拐到她的窗子外来。薛爱青在屋子里嚷道:“瞧你急得这个样子。”
她家人对于她的朋友来了,向来是不敢有所过问的。这会子她的母亲,薛奶奶就答言道:“你就快点儿吧,让人家夏老板老等着。”
说了这话,便由这边厢房里走将出来,对夏秀云又点头又招手,嚷道:“反正玩儿去,迟早没关系。要不。你到我这儿来坐一会儿吧?”
夏秀云连连摇着手,只对她微笑着,却没有说出什么来。薛爱青这才笑着出来,两只手可还在扣脖子上那高领的扣子,因瞧着夏秀云道:“你越是急,我越是不忙,看你摆来摆去,摆到什么时候!”
夏秀云说:“我又没说什么,我摆来摆去,你就让我摆着得了。”
薛奶奶道:“是呀!人家可没说什么呀。”
薛爱青道:“我就不信他这一股劲儿,真能忍耐,倒要瞧瞧他要老憋着呢?可是妈又给他说上了话了。”
夏秀云道:“这也不算受憋呀!我哪样事又不能等着你呢?”
薛爱青此时已走出屋子门,便道:“走罢,别废话了。”
她说着话,径是在前面走。
夏秀云觉得薛爱青是极富于艺术的。她纵然是生气或者小骂,似乎都含有艺术性,值得人去赏鉴。所以薛爱青一说他废话,他倒乐了。眼见得她上了汽车,夏秀云也就跟着上来,不多一会,到了印度洋行。这家洋行,只卖外国货物与绸料的,对外国人自然欢迎,中国人去买东西,却不大理会,然而上门的,倒是以中国人为最多。夏秀云的汽车停在门口,和薛爱青一路进那洋行,见两个店伙,正陪着两个外国兵,半鞠着躬,笑嘻嘻地和他们说话。这边却只有年轻些的,似乎是个学徒的样子,望了一望道:“买什么?”
夏秀云道:“我们买一点印度绸。”
那小店伙将头一偏道:“那边去买。”
看那情形,很随便的样子。另外有一个店伙,看到门口停了一辆最精致的汽车,料想是夏秀云的,这才一点头道:“请上这边来吧。”
夏秀云和薛爱青一路走过去,在玻璃格子里,挑了几样颜色的,各剪了一件料子。这时另有个店伙。微微一点头道:“先生,你今天来剪点料子?你好久不来了。”
夏秀云道:“我和胡总长来过两次的,你还认得?”
那店伙立刻满脸是笑道:“怪道呢?我说好面熟了,你是我们的老主顾。”
说毕,一回头,向小柜台里一个正写账的外国人说了两句外国话。那外国人,也就放了笔,走将出来和夏薛二人点了点头。夏秀云向来没有和外国人作过交易,这倒愣住了,不知道要怎样才好。那外国人倒很客气,连说我们东西好,真正西洋来的,请你多照顾,夏秀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对了他微笑。
薛爱青一看这样子僵得厉害,倒成了不受抬举了,便拉着夏秀云的手道:“你瞧,这料子不错。”
说着向玻璃窗子里一指。借了这个机会,这才把夏秀云的窘状遮盖过去。夏秀云因为外国人亲自都出来招待,这给了面子不小,因此又挑选不少的材料。最后一结账,共是三百多元,他一点也不踌躇,就在身上掏出钱来给了。二人上了汽车,绸料堆了一大堆,薛爱青笑道:“你说是叫我来给你拣材料,我买的倒比你多。”
夏秀云道:“你说这话,我要罚你。我们还能分个彼此吗?我这不能说是送你的东西,要送你的东西,恐怕你又未必肯呢?”
薛爱青道:“这话可怪,你送我的东西,总是好意。听你这话,好像是我不乐意你送似的。”
夏秀云有一句话要说出来,想了一想,又停住了。薛爱青道:“我瞧你有一句什么话要说似的,说呀!怎么又忍回去了。”
夏秀云笑道:“不说了,等着送你东西的那天再说吧。”
薛爱青听他的口音,也就猜个七八,他既不说,也不问了。
车子复回到了薛家,夏秀云便吩咐车夫,把车子里的东西送了进去。车夫以为所有买的,都是薛老板的,一件也不留,完全送了进去。夏秀云只管和薛爱青说话去了,他就没有留心到汽车里搁的绸料,却是两份。这时汽车夫完全拿了进来,他才省悟过来,分明是自己一份,也让拿进来了。多送薛爱青一份绸料,这倒不算什么,只是今天上印度洋行去买东西,算白跑了一趟了。
偏是薛爱青的母亲见拿了许多东西进来,就笑嘻嘻地上前去,将绸料一包一包地接了过去,口里还说道:“这是怎么好?要夏老板送这么些东西。”
夏秀云道:“这又值什么呢?不过是几件衣裳料罢了。”
薛爱青的母亲道:“哟!我们这一礼全收吗?”
夏秀云笑道:“这又不是过什么虚套,送人的礼,还要自己留下一半?要送自然是全送的。”
薛爱青道:“你不是说你剪料子吗?怎么全送我呢?”
夏秀云道:“我要不那样,你不肯剪许多的,那岂不要和你费许多唇舌吗?”
薛爱青对于这话,不再回问,就让她母亲把东西全收了。
谈了一会,薛爱青笑道:“你多坐一会儿吧,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
夏秀云见她自动的请吃饭,这一喜非同小可。只是和家里说了,一定回家吃晚饭的。若是不回去,家里一疑惑就会推想到是到此地的,说话不应点,以后出来就更不方便了。便笑道:“你请我吃饭,我一定到的。可是我在五六点钟,还有个约会,要应酬一下才好。”
唱戏的人,都感到应酬是一桩很要紧的一件事。所以夏秀云说,要去赴约,薛爱青倒很谅解。因道:“那是自然要去的。我就叫家里缓点作菜,等一等。”
夏秀云见薛爱青并不见怪,心里很欢喜,因为要早去,马上就告辞出门。
他坐汽车到了家里,表面上一点也不露形迹,等着和家人同吃晚饭。饭端上了桌,只推心里不大舒服,只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就放下碗了。饭后推说上胡同口王小仙老板家里去坐坐,也不坐汽车,就步行到王小仙家来。王小仙是个唱花旦的人,倒常是和夏秀云配戏。他二人无论公私,做事都是共同行动,所以有许多事,夏秀云不便在家里办时,就到王家来办。
王小仙家里,局面小得多,遇到请人吃酒,或者请人打牌抽头的时候,也假座夏秀云家里。这时夏秀云一人走到王家来,王小仙道:“这两天,你正和小青儿上劲,怎么还有工夫到我这里来?”
夏秀云道:“女朋友得上劲,男朋友也得上劲才好。”
一面说话时,一面掏出怀里的金表来看一看。王小仙道:“别挨骂了,来给我上劲,又不知道有什么事,要在我这里绕弯儿哩。”
夏秀云笑道:“总算你聪明,让你猜着了。劳驾,给我打个电话到汽车行里,给我叫一辆车来。”
王小仙道:“自己有车不坐,干吗又要到外头去找车?”
夏秀云道:“小青儿请我吃晚饭呢。我是刚才由她那儿坐了汽车回来的。这会子,又坐了车子去,让家里知道,又是个麻烦。”
王小仙道:“怎么样?我就猜着这里头有文章。吃饭是很公开的事情,能不能够带上我一个?”
夏秀云道:“我倒没有什么,可是我没有先给她说明,多带一个人去,怕人家不乐意。”
王小仙道:“我说着玩罢了。谁真要去呢?”
她说着,就去打个电话叫汽车。
当她打电话的时候,夏秀云趁她离不开话机,伸手摸了一摸她的脸,笑道:“这孩子越过越要好,你瞧,在家里都抹上这些个粉。”
王小仙尽管让他摸着,把电话打完了。然后将夏秀云的手拿着,笑道:“干吗摸我,摸得我怪痒痒的。这儿姓王,不姓薛,别在这儿出了神,拿我开心。”
夏秀云笑道:“我为什么出了神?你拿镜子瞧瞧,你脸上的这粉,够多么厚。你这衣服里的小衬衫,又是粉红色的。由脖子望上瞧,白的是肉,黑的是头发,真会想你是个大姑娘。”
王小仙道:“我哪里擦粉来着,不过是抹上一点雪花膏。你在家里就不使这个吗?你要是说我这个脖子白,别到薛家去吃晚饭,就在我这儿瞧脖子吧。”
夏秀云道:“这孩子一张泼妇嘴,真够硬的。打此以后,我真不敢和你说话。”
二人闹了一阵,门口就是汽车喇叭响。王小仙道:“车来了,去吧,问问薛老板好。”
夏秀云道:“干吗要你带个好去?她和你有什么交情吗?”
王小仙道:“交情这两个字,可是你说的,怪不着我胡说。老实说,咱们交情是有,向来是很秘密的,可不知道怎么样让你把这件事调查出来了,是小青儿对你说的吧?”
夏秀云道:“好孩子,你真会沾我的便宜。”
王小仙道:“这话怪了,怎么会是说我沾你便宜,嘿!真有你的,这小青儿就算是你的人了。”
夏秀云一伸手,将王小仙的粉脸,又掐了一把,笑道:“得,算你说赢了,现在我没有工夫和你瞎聊,回头有工夫,我再来和你算账。”
说毕,也不等王小仙的回话就匆匆出了大门,上了汽车。
到了薛爱青家,她正背了手,昂着头,站在院子观望天色呢。夏秀云就笑道:“现在日子长,别望着天还没黑,可是已经不早了。我真对不住,让你等久了。”
薛爱青的妹妹薛爱芳,就比姐姐喜欢说话。她看到夏秀云就一脚踏出了屋子来远远地向着他笑道:“你既然知道时候晚了,干吗不早来?我们老等着,饿得肚子直嚷嚷。现在你虽然是来了,非罚你不可。”
夏秀云就爱听他姊妹俩说俏皮话,当时就答道:“真该罚,但是罚我什么呢?别罚我的酒,喝了闹嗓子,怎么上台呢?”
薛爱芳道:“罚酒,那是好过你了!要罚你五大碗饭。若是吃不下去……”
夏秀云道:“吃不下去怎样呢?还得罚上加罚吗?”
薛爱芳道:“这个我就不便再说,你问一问我姐姐,应该怎么就是了。”
夏秀云听说,就掉过脸来,望着薛爱青。薛爱青笑道:“依我说,压根儿就谈不到罚。我们既是请人家,来就是赏面子,不来也不算得罪了咱们,迟来早来,听客的便,主人翁哪里管得着?”
夏秀云道:“呀!这不是好话呀。得,我自己来罚吧。就请二位,快快赏我饭吃吧。”
薛家的人,从亲至疏,从上至下,无论是谁,也得过夏秀云好处的。一声说到夏秀云要吃饭,大家早是七手八脚,将预备好了的酒莱,一阵风似的端上。酒菜摆在客厅旁边一间屋子里,只有三副杯筷,就是薛氏姊妹二人奉陪他。老妈子是不喊不进来。
薛爱芳的饭,吃得很快,便是老早的吃了饭先出去,屋子里主客二人,慢慢地浅斟低酌,夏秀云虽不敢多喝酒,但是他觉得今天极端地容易醉,只喝了一杯半葡萄酒,人就有些支持不住了。他忽然一省悟,可不能再喝,家里人原以为是到王小仙家去了。待会回家去,一股酒气冲天,问起来是怎样的说法,因此便停杯不饮。笑道:“别尽管让我喝酒呀。喝醉了怎么办呢?”
薛爱青先还以为他是随便的一句推辞话。后来一想,他若是果然喝醉了,会引起家里人注意,就不再劝他喝了。夏秀云吃过了饭,掏出金表一看。薛爱青道:“别当着我的面,只管看表。你若是有什么事要走你就请便。”
夏秀云道:“这可不对。难道当着面看表,那就算告辞吗?”
薛爱青道:“你是真不走,还是假不走?你若是能坐一会儿,我倒有几句话,要和你说一说。”
夏秀云待说什么时,薛爱芳在屋子外叫道:“停一停办交涉吧。王小仙打电话来了。”
夏秀云一听,连忙去接电话,只听到王小仙道:“嘿!你忘了是打我这里雇汽车走的吗?你家叫人找你来了。我也没让他进来,我就告诉他们马上就回去。就是这么一档子事,你瞧着办吧。”
夏秀云道:“好,好,我这就回来。”
薛爱青站在旁边,等他挂了话机,便道:“你们大奶奶下了圣旨了吗?”
夏秀云道:“你别瞎扯。这是王小仙在他家,打来的电话。他说林总长由天津回来了,现在他那儿等着我呢。”
薛爱青道:“既是到王家去,你干吗在电话里说就回来呢?”
夏秀云道:“这也犯不着挑眼,我不过是说急了一点罢了。你若是不让我去,我就给林总长打电话。”
薛爱青道:“那更胡闹了。林总长不是像从前,能天天和你见面了。现在他由天津来一趟,很不容易,也许当天就走,你不去见他那是什么话呢?”
夏秀云心里巴不得她如此说,却站着发愣,似乎有些不知道如何处置是好的样子。薛爱青道:“自己有事,当然去办自己的事,难道为吃了一餐便饭,把正经事都得耽误了才痛快不成?”
夏秀云道:“倒不是为这个你说有一句话要和我说,我没有听到,心里老是不安的,你能不能先把话告诉我。”
薛爱青道:“这话很长呢。等你没有事的时候,我再慢慢地把话告诉你。若是不走,我有话还不告诉你呢。”
夏秀云听了这话,就放大了胆,告诉回王小仙家来。
王小仙听到汽车响,早就迎了出来。夏秀云刚一下车,王小仙就两手一伸,作拦阻之状,口里连道:“你快回去吧。车钱我给你开发就是了。”
夏秀云道:“这孩子就是这样没见识,又有什么事,忸得这个样儿?”
王小仙将他拉到身边轻轻地对着他耳朵边说道:“你家派人来找你,说是老婶娘有事和你说呢。若是知道并不在我这里,是打我这里汽车走的,还说我和你串通一气,我是吃不了兜着走呢。”
一面说,一面就把他向着阶下推。
夏秀云的母亲,最是厉害,平常管得儿子最是严谨。夏秀云一听是母亲派人来叫,也不敢再耽误,匆匆忙忙地走回家去。到了家里,直就去见他母亲夏大奶奶。夏大奶奶,身边又坐着夏秀云的老乳母魏奶妈。夏大奶奶板着一张黄瘦似的枯蜡脸儿,像丧门神的样子,翻着一双吊角眼望了夏秀云。那乳母却像大母猪似的胖,单提那个大肚子,就活像胸面前挺着一卷大棉絮。她正坐的是一把小围椅,满身的肉,都由椅靠子上挤了出来。不过她身虽是如此肥胖,头却比平常的人,还要小一点。因此外人见着她,都称呼她为兔儿奶奶。兔儿奶奶自己虽是这样的肥,可是她奶着夏秀云兄弟,都刚健婀娜,一个是青衣,一个是花旦。夏家念她奶得孩子好,所以夏氏弟兄都娶妻生子了,还留着她在家里做活。
这时夏大奶奶望着夏秀云有生气的样子,兔儿奶奶便将一双肉泡眼,先笑成一条缝,然后将脸泡上那块肥肉一缩,笑道:“大奶奶有话要和你商量呢。大爷,就是有这样的大爷脾气,无论到哪儿去,只要有乐子,就会把正事忘了。”
夏秀云道:“我哪是玩?林总长今天下午由天津来了,刚才他由王家门口经过,下车坐了一会。人家老远的来了,见了面,我能不到人家坐一会吗?”
夏大奶奶原是满脸都带有几分怒色,一听到林总长三个字,那怒色不由得慢慢淡下去,及至把话听完了,连忙问道:“林总长还在王家吗?怎么不到我们家来呢?林总长这人真好说话,有几句好话说着,他就软了的。别是小仙这孩子使鬼,不让他上这儿来吧?照说是不能够的。他总是帮着你的忙,没有说过一个不好字儿,不能说是他现在不作官了,就不管你的事了。”
夏秀云道:“人家是有公事来的,听说今天晚上,又要回天津去呢。刚才到王家去是因为他车打王家门口过,停了车子下来坐坐,他哪里有工夫到我们这儿来坐呢。听说他待一会就要走,我倒是想到车站上去送他一送,可是今天太够忙了。”
夏大奶奶道:“白天一点儿事没有,谁让你那样忙?这会子真有事了,你倒又嫌累不去。”
夏秀云道:“知道车夫在不在家呢?”
夏大奶奶道:“你真随便,你是全不在乎,大财神爷让人家抢了去了,也是活该。”
兔儿奶奶就接嘴道:“是呀!别说你了。就是我真也得了林总长不少的恩典,他要让我见面,我就真愿给他磕一个。我瞧着这齐齐整整的屋子和你那亮光光的汽车,我就想林总长人真不错。咱们总别忘了人家的好处。”
夏秀云一想,这事情算办得成熟了,用不着再废话,便道:“现在快要到时候了,既是那么着我这就得去。”
于是就吩咐汽车夫开车,直待他上了汽车,然后才告诉他们是到薛爱青家里去。
这一回来,薛爱青却是出于意料以外的。夏秀云走到上房门外,正听到薛爱芳道:“小夏儿真点大爷脾气。刚才自己车没来,还另外雇了汽车来,坐一趟洋车,也不要什么紧呀!大老板到底是大老板。”
夏秀云就在外面笑道:“不敢当!不敢当!这回是自己车来的,算不算大爷脾气呢?”
薛氏姊妹一同哟了一声,一齐向外看。夏秀云笑道:“我并不是非坐汽车不行,因为赶着到这儿来,怕是坐洋车慢了。这是我够朋友,怎么算是大爷脾气呢?”
薛爱青笑道:“真是凑巧,一提到你,你就来了,幸亏是没有骂你,若是骂了你,那可糟糕了。”
夏秀云道:“那也没有什么糟糕,我是最爱挨骂的人,若是老有你们骂我,我倒乐了。”
薛爱芳道:“姐姐,咱们别依他,他说要咱们骂才好,他意思是说打是疼骂是爱呢。”
薛爱青抿嘴一笑道:“谁有哪么些个工夫,和他说那些废话。”
于是大家就一阵笑。薛爱芳见他今日一天,连来三次,必有所谓,大家坐在一处,显着不合适,因此借个原故,就避开去了。
薛爱青瞧了夏秀云一眼,笑道:“你怎么回事?来了又要去,去了又要来。”
夏秀云道:“我本来打算不来的了。可是你对我说,还有一句话要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好话要对我说,你不对我说明,我心里怪难受的。”
薛爱青瞧着他半晌,才问道:“你以为我有一句什么话要和你说呢?”
夏秀云道:“就因为是我不明白,我才来问你,我要知道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我就不来问了。”
薛爱青微笑了一笑,然后才道:“这话说得是很有理,我驳你不倒。可是我猜你心里,一定以为我有句什么要紧的和你说,所以你等着我的回话。其实……”
薛爱青说到这里,又微笑了一笑,然后才道:“其实是一句不相干的话,现在事情过去了,我也懒得说了。”
夏秀云道:“你不是说,回头再对我说吗?我总算不敢失信。”
薛爱青道:“这样说,你是说我失信了。”
夏秀云笑道:“我决不敢那样说,不过我这人对朋友有点死心眼儿,你说着什么,我就信什么。现在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就不必说了。”
薛爱青想了一想,微笑道:“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过两天瞧瞧,能告诉你就告诉你,不能告诉你就不告诉你,你等着吧。今天你坐着两辆车,跑来了三趟,也真够累的了,坐着休息休息吧。”
夏秀云果然就靠着沙发坐下,头靠了椅背,一个劲不住地微笑。薛爱青道:“你又该走了吧。你不是又有什么约会吗?”
夏秀云摇着头道:“不。我今天晚上什么事都没有了,预备来谈个三点钟四点钟的。”
薛爱青笑道:“照你这样一说,我成了开废话公司的了。”
说毕,格格格地一笑。夏秀云道:“我就记得这样一句话。酒逢知己千言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废话不废话,原是没有一定的。”
薛爱青道:“你哪里听来的这两句文章,我只听到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没听说千言少的。”
夏秀云道:“我真恨从前没有读书,现在遇到要谈字的地方,都透着困难。你肚子比我宽得多了,要不,我就拜你做老师吧。”
薛爱青道:“说着说着,又讨我的便宜来了。”
夏秀云道:“拜你做老师,怎么倒是讨便宜?”
薛爱青将头一伸,向他点了两点,笑道:“你不要装傻了。你想想那得意缘的戏里试试看,是谁拜谁做老师呢。你就常露这一出戏,在这里安下了机关,占我的便宜哩,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夏秀云经她一提,倒醒悟过来,笑道:“原来我真没有想到,可是真这一说,连我也觉得是有点讨你的便宜。其实一个人真有那么一个好太太,拜她做老师真也值。”
薛爱青道:“说你占便宜,你索性倒敞开来说了。”
夏秀云被她封住了门,话就不好向下说,便躺着微笑。
薛爱青向门外望了一望,微笑道:“今天有一桩事对不住你,一直到吃过了晚饭以后,我才明白。”
夏秀云愕然道:“你这话我不明白,你有什么事对不住我呢?”
薛爱青笑道:“你这人太爱一点面子。今天上印度洋行买料子去,不是为你自己要做行头,赶着去买么?到我家来的时候,你的汽车夫又不明白,把你自己的料子,和着送我的料子,一齐送了进来。我们家里人都糊涂,也不问问,就一块收下来了。你明知他们错了,想着要说不是的,一来怕我们不好意思;二来也嫌自己寒碜。所以索性充一个大方,全送我了。你说对不对?”
夏秀云道:“不是那样的,你猜错了。那点东西算什么?交朋友在乎此吗?”
薛爱青笑道:“我说你这人爱虚面子不是?”
她说这话的意思是说的夏秀云让人识破了,还不肯认。夏秀云却误会了她的意思了,以为她指着刚才那点东西算什么几个字说的。因笑道:“你瞧着吧!我虽然爱虚面子,有时候也会是爱实面子的。”
他说了这句话,就不再提了。薛爱青本是批评他的话,他自己既然不提,当然也不便和他说什么,这一场交涉,就此过去了。
当晚夏秀云在薛家谈天,一直谈到十二点钟方才回去。临去的时候,再三约定薛爱青明日在家里等他的电话,明天有要紧的话和她说。薛爱青料着他所说要紧的事,也无非是天天这一套,也就不把来挂在心上。到了次日正午的时候,夏秀云果然有一个电话来,他说有一样东西,要拿来看看,教薛爱青无论如何不要出门,总等着他。薛爱青因他说得很慎重,就坚决地答应了,无论如何不出门,等到天黑,也不走开。夏秀云笑着说,决不让你白等的。于是笑着挂上电话了。在通电话以后,约莫有两个钟头,夏秀云果然来了。
他笑嘻嘻地走进门,手可插在插兜里。薛爱青道:“你不用说话,我先猜一猜看,你这袋里又带了什么玩意儿来了吧。”
夏秀云道:“带是带了一样东西来了,可不是玩意儿。”
说着手向外一伸,拿着一个很精致的洋瓷印花扁匣,约莫有成寸见方大小。薛爱青道:“这是什么呢?”
夏秀云道:“你瞧吧,西洋玩意儿。”
一伸手将那扁匣子打开,里面又另是一个紫海绒的匣子,紧紧地被套着。取出这个紫绒匣子来,再一打开,里面又是翡翠也似的绿绒里子,正中亮晶晶地嵌着小蚕豆似一粒钻石,拿起看时,这钻石在一只白金戒指上。
薛爱青自从走红以来,什么珠宝,都也看过。像这样的钻石,明友之中,竟没有见人戴过,真是可爱,托在手上,不住展玩了一番。夏秀云道:“你看这东西怎么样?”
薛爱青道:“这样大的钻石作戒指正好。既不寒碜,也没有笨像。”
夏秀云道:“既然是这样说,大概你也很赞成了,我索性让你看上一看。”
于是又伸手到衣兜里,再掏出一个锦匣子来,那个匣子,正是和刚才掏出来,差不多大小。打开来,也是装着一粒钻石。
薛爱青托在手掌心里,掂了一掂,正是分量,形式,光彩,无一不同。因笑问道:“这钻石果然不错,你在什么地方收罗来的?”
夏秀云:“这个你别管,你到底是看了合意不合意?”
薛爱青笑道:“这样好的东西,谁不爱?”
夏秀云道:“你爱就好,我今天跑了好几个地方,收到这样一对,花了三千块钱,才买到手。这戒指我自己戴一个,送一个给你,你能不能赏脸收下来。”
说时,脸望着薛爱青尽管微笑。薛爱青笑道:“夏老板,你是成心损我吗?你送我这样的好东西,还问我赏收不赏收,难道我那样不知好歹吗?”
夏秀云听她如此说,就扶着她的右手,拿了一只戒指,轻轻的,给她套在指头上,然后自己也在右手无名指上,戴了一只。于是伸手出来两人比一比,夏秀云道:“这戒指今天咱们是一路戴上的,我要看看,将来是谁先摘下。”
薛爱青笑道:“不是今天初戴上,我说那丧气的话,就凭我这点不相干的本领,大概再混个几年,总也能够糊自己的口,还不至于靠卖了这戒指来换饭吃吧?”
夏秀云道:“你不要瞎扯,我的意思,不是这样说。我是说戴着戴着,总有一天不愿意戴的时候,所以说着谁先摘下。”
薛爱青将戴着钻戒的那只手放在面前看看,又伸了出去,远远地看了一看,笑道:“这东西果然不错,我没有看见谁戴过。要说有来有往,你送了我这重的礼,我应该送你什么东西才好?我可拿不出三千块钱来送你这样一个重礼呀。”
夏秀云望着薛爱青,半晌没有作声,却只管微笑。因道:“你还是装傻呢?还是真不知道呢?难道送礼是做买卖,来一个半斤,就要换回八两吗?只要人情到了,我想是千金不为多,四两不为少的,你瞧我这话说得通不通?”
薛爱青却只管笑着。夏秀云道:“你怎么不说话?”
薛爱青道:“你真能说,让我说什么呢?”
夏秀云见她说话时一双亮晶的眼珠望着人,两颊上晕着浅红,含羞默默,柔情动人,觉得她虽不说什么,可是就在这不说话之间,已经给人一种很深的影响。半晌,这才想起了一句话,因问道:“你老把这戒指戴着,设若有人问起你来,你怎么样说法呢?”
薛爱青眼珠一转,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因道:“那有什么不好说的。若是生人,随便怎么说,也没有关系。若是熟人,我戴着一个,你也戴着一个,我就不说,人家也明白的。”
夏秀云笑道:“人家明白什么?”
她道:“那还要提吗?人家一定猜是你送给我的了。”
夏秀云听她这话,又望着她的脸,就禁不住由心里直乐将出来。在薛爱青倒无所谓今昔,在秀云,就好像自己眼里看着薛爱青今日是格外美丽,而且也是格外有情。
自从两点钟说话起,直谈到七点钟,在薛家用过了晚饭,王小仙打了电话来问,说是林总长今天真来了,你赶快回家去吧,说不定他一定会到你家去的。夏秀云就是不敢得罪林总长。而且也怕昨天撒的谎,会让家里对证出来,因此不敢多耽误,就回家去了。
夏秀云一走,薛家人就一阵风似的一齐围着薛爱青,要看那钻石有多么大。她母亲先就说,夏老板人最好的,多么大气。她母亲这样一说,大家都觉有理,也跟着说起来。薛爱青当着众人便道:“人家的礼物,咱们是受了。可是人家有个条件,都得戴上,谁先摘下,谁就没理。”
大家都说自然要戴上,这样好的宝物不摆出来,难道还收着在箱子里不成?薛爱青就是怕家里反对此举,既是家里都答应了,这就敞开来戴着。在家里戴着,出外戴着,在戏台上演戏也戴着。
她总算是个头等红角,与平凡的坤伶不同的。有一天,她演《汾河湾》的柳迎春,也是照样的把那钻戒指戴着,并没有取下。过了一日,报上就登出一种不好的戏评来。说是《汾河湾》的柳迎春,饭都没有吃,全靠儿子打雁充饥,怎么她手上还戴着一个钻石戒指?这钻石在电灯下,有一种光耀射人,决计是真的,不知道是哪个大阔老,送了她这样一个,让她舍不得除下。当这篇戏评,刚刚登过去两天,恰好夏秀云也演《汾河湾》,照样戴着那钻石戒指,未曾除下:台下听戏的人,有几个注意的,这就看出来了,他们两人戒指圈儿,都是白金的,这未免相同得太凑巧了。于是又有人把这事作了一篇戏评,投到报上去。大意说,老戏原不能十分写真,《汾河湾》的柳迎春,弄成一个叫花子出台,固然令人感到不快。但是这可以是必有的白金钻石戒指,这一男一女,两位名青衣,何以都戴着呢?
唱戏的戏子多半是看小报的,大报虽然有这种批评,夏秀云却还是不知道。有一天薛爱青在一张小报上,看到捧她的人,做有戏评给她辩护。说是中国的旧戏,向来是讲美观,不讲实际。要不然,谁的胡子,会长着盖了嘴。戏台上的古人,胡子都是长在上唇的。又像长靠,就是古人的盔甲,打仗的人,哪能穿得那样的花哨。再说靠后的四面令旗,不能无所谓,真要那样打起仗来,有多么不便。像这样不合理的装束,老戏里,到处都有。为什么都不管,就只攻击这一只小小的白金钻石戒指呢?再说这白金戒指,既然有得卖,就谁也可以戴。不能说有人戴着同样的戒指,就会有什么关系。薛爱青看这篇戏评,倒辩护得理由充足,但不知对谁而发。因此向小报界的朋友,四下打听,这才知道,有关于自己和夏秀云的两篇文章。这虽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过自己的意思,是不愿学芳芝仙去嫁华小兰作二房的。若是像报上这样鼓吹都不去更正,越传越坏,将来一定会传得弄假成真,有一天摆脱不了的日子。与其到将来无可辩护的时候再来辩护,不如先说明白了是干净。如此一想就分途去和报界接近的人物来接头。她想到贾叔遥也是和新闻界人常到一堆去的,大概找他帮一点忙,他也不会推下的。她本知道贾叔遥的住址,草草地写了一封短柬给他,说是有事,请他来面谈。贾叔遥接了信,第二日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