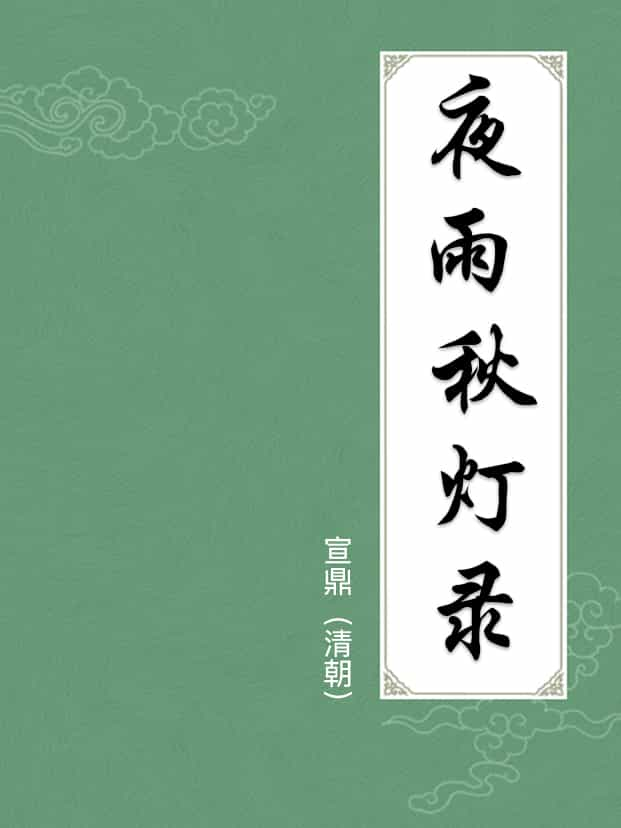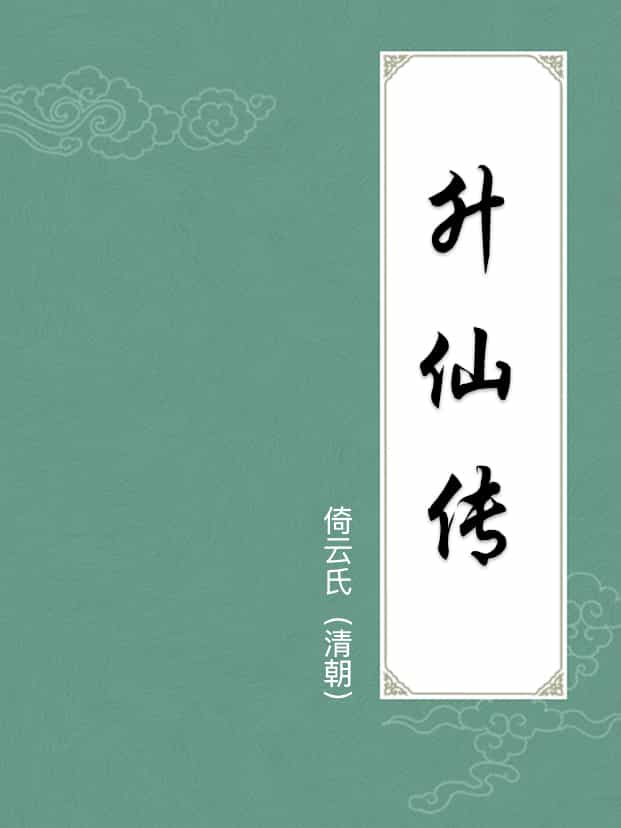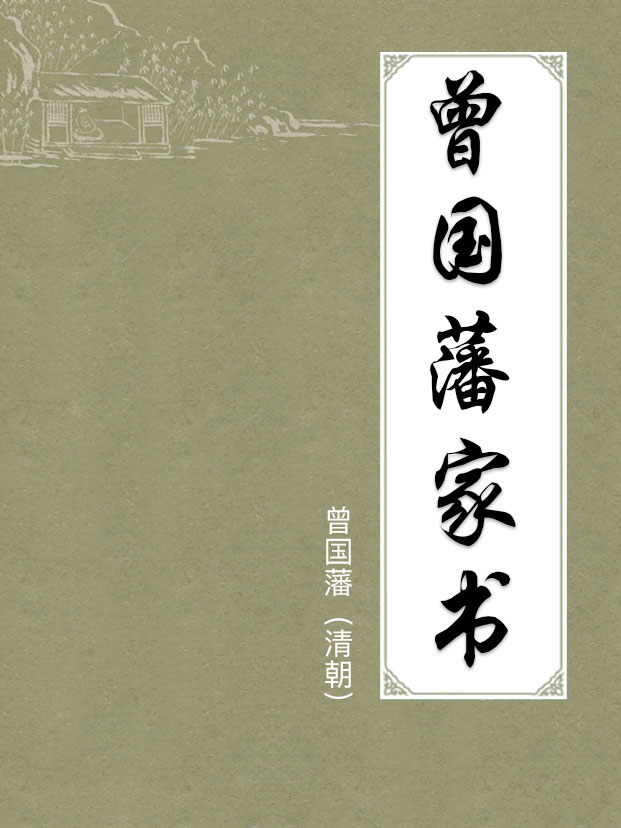诗曰:
哲人日已远,斯文渐投地。
学穷如嵩林,纷纷起角利。
不识四书字,安解一径义。
骗得愚义兄,误却佳子弟。
鹤粮借养鹙,盐车负骐骥。
感慨灌花翁,击碎玉如意。
话说胡楚卿别了俞彦伯,一路行来,见个少年,也是一主一仆,好生面熟。同行了三十里,那人差别道:“兄不是敝府口气,今往何处?”楚卿道:“小弟是鹿邑,有事来拜俞大尹。”那人拱手道:“失瞻了。小弟正要往归德。”楚卿道:“如此同行了。请问尊姓?”那人道:“小弟姓吴,字子刚,本县人。”楚卿就晓得前日县堂上要杀妻子的吴监生,所以有些认得。子刚道:“兄尊姓大号,几时到这边?”楚卿道:“小弟姓胡,字楚卿,来此数日,今早才别的。”子刚肚里也晓得楚卿知道他的事。二人又说些闲话,不觉行到上蔡。楚卿叫蔡德去访沈家,就同子刚上了旧店。少顷蔡德回覆道:“沈老爷已于二十八日赴任去了。再问豆腐店,他说你是哪里人,我说是鹿邑人,要记乡里姓吴的,他说喜新不知哪里去了,夫人小姐甚是念他,临行朱妈妈寄一封字,要与他,说若有喜新乡里来问,就可寄他,你今既是喜新乡里,我把这封字寄你与他。如此我拿回来。”楚卿看封皮是二十七夜,封内写:“撇下衾儿,若不图后会,便是无情也。”不写哪个名字,细认笔跡,乃是小姐的。把《春闺诗》出来一比,虽真草不同,而风雅无二。因想起小姐书欲写而难写,名欲露而不敢露,待撇下而不忍撇下,故写这字来,真好感伤也,又下起泪来。子刚道:“兄有何心事,尚有过于弟者?”楚卿道:“此肠欲断,不能细谈,明日路上,大家一诉。”子刚遂唤主人多设酒肴散闷。
明日途次,楚卿道:“兄之事,弟未悉其始末,若不见弃,一谈何如?”子刚道:“天涯知己,见笑何妨。”遂把父亲如何作家,如何死法,原配贾氏,如何贤慧,如何憎厌,细细说了一遍,说到贾氏抑郁而死,也哭起来。楚卿道:“后来如何?”子刚道:“后来续娶的,就是前日之妇,做这事来。”楚卿道:“今尊意如何?”子刚道:“已勘破红尘,知天道报应不爽,酒色财气,不可认真。向有小典在京师,先父是三分息,今弟去算清前帐,以后一分五厘息了。更有贵府盐店,借银四百两,要去取讨。”楚卿道:“兄有此家私,令堂无人奉侍,还该娶一房才是。”子刚道:“就是要娶,在本处亦无颜。待典中算帐回时,要在外郡置一庄宅,同母亲移居,再作区处。”楚卿道:“这也高见。”就把自己父母早亡,尚未受室,今在上蔡,前后事情,细说一遍。子刚道:“如此看起来,弟与兄异途同辙了。但替兄想来,那夫人说无白衣女婿,来年就是科场,吾兄发愤,博得黄甲,那时肯与兄便罢,倘若不肯,小姐亲有水晶带玦、亲笔诗在此,只说他赖婚,约了同年,共上一本,圣上作了主,夺也夺他过来。今日何须愁闷?”楚卿见说得有理,心上畅快。一路上言语投机,遂成莫逆。
及行近鹿邑,楚卿道:“小舍就在前面,若蒙不弃,屈驾光降,结个知己何如?”子刚道:“弟亦有此意。”遂同至楚卿家,合家接见。楚卿打发蔡德妻子回去,就办三牲祭礼,与子刚结拜为兄弟,子刚年长为兄。楚卿置酒款待。盘桓两日,子刚道:“贵处民风古朴,甚可卜筑。兄园左有隙地数亩,弟欲奉价,建造几间房屋,与兄居止相傍,未知允否?”楚卿道:“弟若得与兄为邻,平生之大愿也。弟原有楼屋一所,离此三里,暂典与寒族,就送兄居住,何以价为?”子刚道:“若得如此,弟旋踪时,就变卖田产,同家母到宅了。”楚卿大喜。明日临行,子刚道:“八月准到此处。兄若要问信,可到府前广货店汪景成家便知。他不时有人来往。”说罢,两人拜别。
自此楚卿深信子刚之言,发愤读书,真个是足不窥园,身不出门,读至四更,犹吟哦不绝。光阴梭掷,不觉重阳节近。管家周仁来到书房,见楚卿沉思默诵,周仁连叫三四声,总不听见,直待拿朱墨来磨,再叫一声,方才看着。周仁道:“相公如此用心,决然大发。但明日是个佳节,该出去散一散步。”楚卿道:“不是你提起,我到忘怀了。我原约一个朋友,明日可顺便到府前问信。”
次早起来,下起细雨,至初十日晴了。楚卿同清书上了牲口,出门但见金风飒飒,衰柳凄凄,已是深秋气象了。行了三十余里,天气暴热,一片乌云西起。忽然下雨。望见山坡下有个竹林,几间茅屋,楚卿急来躲雨。来到门前,下了牲口,忽听得里面赞道:“虽子建复生,不过如此!”楚卿就踱进去,却是两间敞屋,半壁疏篱,几盆黄菊,到也幽雅。有两个老年,一个少年,在那里饮酒,桌上五六个碗,已吃得精光,拿两幅字,侧头摆脑的称奖。忽见楚卿走进,大家立起身来,拱一拱道:“请坐!”楚卿道:“小弟是偶然躲雨,请各尊便!”那个道:“小弟因昨日下雨,不能纪登高之胜,今特约两位知己,在此挈盒补数,限韵赋诗。但瓶之罄矣,不敢虚屈了。”楚卿道:“既如此,必有佳作,敢借一指教?”那一个道:“兄也晓得诗么?”楚卿道:“虽不晓得,却也读得出来。”又一个道:“这位姓高,是个宿儒,一个徽州大店里,请他教两个儿子。弟姓赵,在前村训蒙。因初八日,高先生放学回来,路上买一只鵁,约小弟昨日要来赏菊,就以‘’为韵。不意下雨,未曾一乐。这一位姓邳,是青年饱学,住在城内,就在城中处馆,昨日到这边岳家,要领夫人回去。所以弟两个,各出酒肴在此,屈他来到做一首,效金谷园故事。既兄晓得诗,必定是有意思的了。”遂递过姓高的诗来。楚卿看题目,是《雨中寻菊》;再看上面写着诗道:
七三涂猎捡之,渱也煮妻椒炒精。
菊箾倒风双袖酒,鸡糖溅雨一襟饧。
宾王昔日无三友,陶令今年有四甥。
乐矣归欲渱不见,问貍光惯瓮碪秤。
楚卿念了三遍,也不明白,只得问道:“小弟学浅,不但不明其理,要求逐问讲教;连这“渱”字也不识。”高先生道:“兄方才说识诗,故此与兄看。今兄看不明白,要我讲说。孔子云‘诲人不倦’,我若不肯,就是吝教了。这‘渱’字,是茄娘切。在《海篇》上,夫渱者,渱呣也,渱呣者,吃物而唇动声也。第一句‘三七涂猪检之’,前日弟解馆回来,以七分三厘银子,涂路上遇着个猎户,拿许多雉兔獐鸡,弟捡一只鵁买了,是这个原故;第二句,买到家里,挦去毛,先将水煮一滚,老妻就取起切碎,放些椒料炒着,精品不过,所以说‘椒炒精’;第三句,要晓得未种菊,先插竹,昨日因虚了赵先生之约,到一个邻家赏菊,正在花下饮酒,忽然一阵风来,竹箾吹倒,划泼了半壶酒,老夫双只衣袖,沾得甚湿,故云‘两袖酒’;‘鸡糖溅雨’者,那些鸡一向躲在菊花下放的粪,也有干的,也有白的,也有一样色烂如糖的,那急雨溅起来,急去收碗喋,看衣襟上溅满了故云‘一襟饧’;至第三联,是两个古典:昔日骆宾王寻菊,无三友者,不曾有赵先生、邳兄与老夫三人也,当初陶渊明最爱菊花,为彭泽今。今人每以海棠比西施,老夫发邓以菊花比渊明,是巧于用古处。上年敞邻在朋友处分得一根回来,今年产了四芽,可是生了外甥一般?末两句是照应起两句,赏了菊,吃了酒,乐而归去,还剩那鵁在家,老夫正要想渱呣渱呣的再吃些,不意又见,问起拙荆,他道领家有个狸猫,到舍偷吃,不管多少,一吃就精光,竟是吃惯了,如今把肉藏在瓮里,将碪秤盖好,又恐爬开了,故云‘问狸光惯瓮碪秤’。你说这诗好么?”楚卿道:“果然妙。”高先道:“赵先生,你的佳作,一发与这位看,见得我们为师,俱有实际,不比那虚名专骗人家束修的。”赵先生对楚卿道:“看诗有个看法,须要认题。高先生吃肉,是做死的,我是做活的,不可一例看。”楚卿道:“有理。”只见他诗写着道:
菊边歇下一只,溅湿衣毛活似精。
赶他翟遏像赶鸭,吃他连喋如吃饧。
儿惊磕碰寻老子,婆见吱喳叫外甥。
十六双棋去得尽,刚刚剩得光棋秤。
楚卿看了好笑,只得赞道:“妙!这位邳死一发请教。”邳先生道:“两位先生是前日做起,小弟是今早约来吃酒,方得做起,已有两句了。”弟与楚卿道:“小弟是不做鵁,做了。”楚卿接来一看,只见道:
鵁,花叶啄完光打精。
楚卿见他年少,忍不住道:“诗思甚佳,只怕擃殦,未必做巢在菊花上。”邳先生笑道:“兄只识得几个字,就要批评人?千家诗上,说得食阶墀鸟雀驯,鸟雀既驯,难道鵁殦做不得巢?轻易批评人者,此亦妄人也已矣!”楚卿道:“领教。”意欲别出。赵先生道:“雨虽止了,地上犹湿。兄既晓得诗,也做两三句何如?”楚卿道:“要做何难?”三人便去拿纸笔墨砚,铺在桌上。
楚卿坐着,三人到背后,把眼瞅一瞅,看他做些什么出来。孰知楚卿提起笔,不待思索,一挥而就。诗曰:
溪头雨暗下飞,踏屐篱边致自精。
看去离披如中酒,食来清远胜含饧。
临波洛女窥行客,洒泪湘妃觅馆甥。
带湿折归敲一局,幽香染指拂揪秤。
楚卿立起身来道:“呈丑!”高先生道:“做不出么?”楚卿道:“完了。”三人不信,走到近前一看,果然完了,都说:“这也奇!”今到第三句,高先生道:“这‘中酒’二字不通,那有菊花吃酒?”大家都笑。念完,再念一遍,觉得顺口不俗,且做得快,不像自己苦涩,有些嘴软起来。姓邳的道:“真是仙才!兄在何处处馆!”楚卿道:“不处馆。”赵先生道:“兄该处一馆,若要美馆,有个舍亲,只有四位学生,馆毂与高先生差不多,足有八担大麦。”
只见清书进来道:“相公,路干了,早些去罢!”楚卿遂撒手与三人作别。上了牲口,一路好笑。
明日到归德府,正欲进城,只见茶馆内一人叫楚卿:“贤弟哪里去?”
未知何人叫他,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