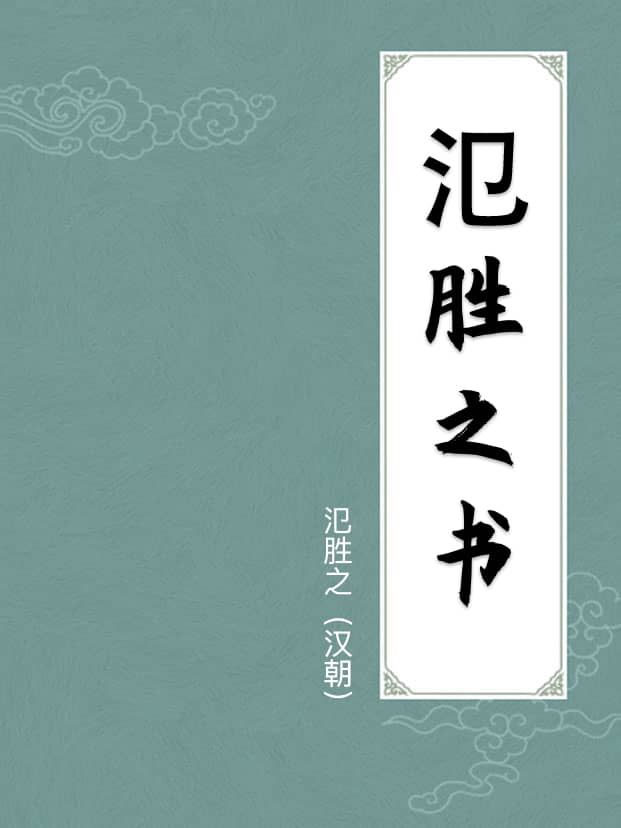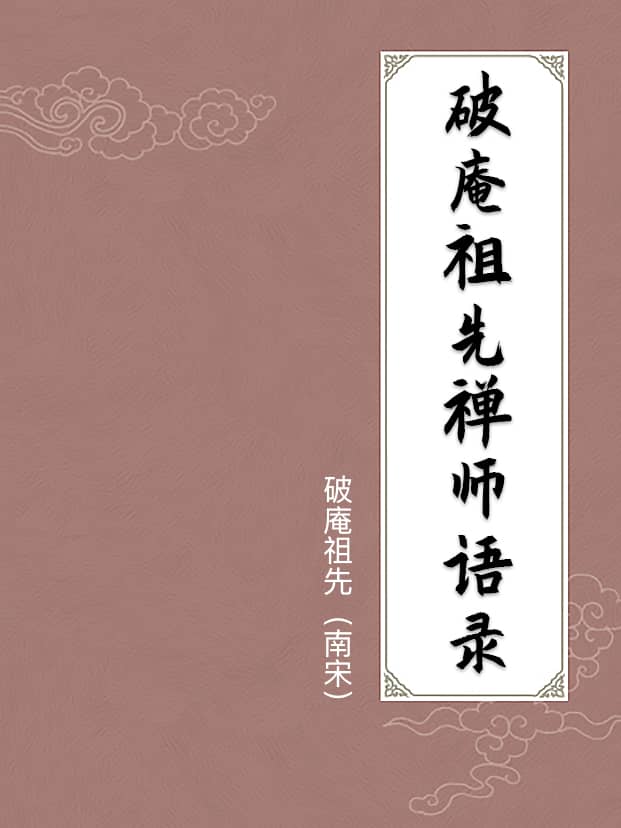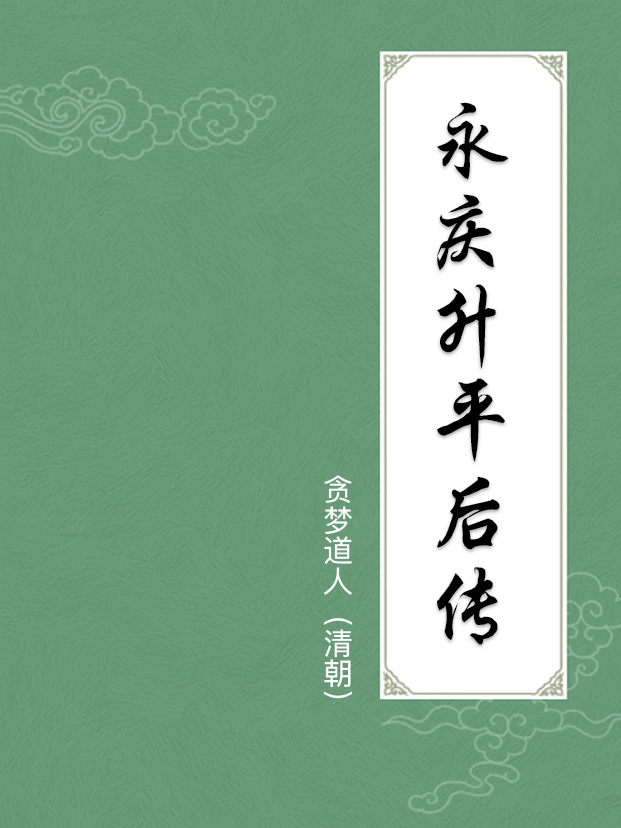于是,我先从月子可能会住宿的宾馆打电话查询。现在我住的这家宾馆是当然的,其他如三年前我们新婚旅行住过的,坐落在旺多姆广场中的宾馆,还有赛纳河畔的日资宾馆,还有月子曾说过她很喜欢的香榭丽舍大街北面的那家小宾馆,我都一一打了电话,但是回答都是没有这么一位日本女客人。月子会不会住在她的朋友处,或者已经去了什么别的地方?
总而言之,要毫不气馁地坚持寻找。而为此先要保证充分的休息,睡上一觉,恢复一下体力再说。这样想着,我便又一次钻入了被窝,不一会便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已是中午十一时了,我简单地吃了些东西,便借了辆汽车,去巴黎市内寻找起来。从里沃利街到协和广场,从香榭丽舍大街到费纳河畔,再去埃菲尔铁塔、歌剧院蒙帕纳斯大道,最后到达拉丁区,凡是日本人可能去的地方我都找遍了,可就是不见月子的影子。
凭着一时冲动,从日本赶到巴黎来,可这么大的城市里,要找一个人真是犹如大海捞针一般呢。我的目光在街上的人流中扫来扫去地看,终于下定了决心去红城堡看看。在市内转了一圈,已经过了四时了,如果再赶到红城堡去,则要将近七时了,但正好是夏天日长,七时左右天也不会太暗。我这样想着,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让我进城堡,但感到现在即使进不了城堡,在外面看看也是有必要的。我这样决定着,便先去了圣?米歇尔广场附近的那家餐厅,这是半年前我与月子一起在那里吃过晚饭的地方,我又去了二楼,看到我们那天坐的餐桌今天空着,于是我便在那桌前坐下,要了一杯咖啡。
去年岁末,我与月子在这里用晚餐,店里的老板曾恭维月子说“真漂亮”。月子那天被老板说得心情也特别好,对着那边墙上的一幅弗兰德地区的风景画很感兴趣。现在这餐厅、这画都原封不动地没有任何变化,可关键的人儿月子却变化得太大了。
才半年时间,就能发生这样的变化。我对这变化感到很是迷茫,心里总弄不明白。
也许我们现在正是最最变化多端的时期,正确些说不应该是我们,应该是我这样的男人,现在正处于一个激烈变化的时代。
不要太远,就是中世纪或者近代,男人绝对是占统治的时代,当时的男人要女人怎样女人就得怎样,我这样说也许有些庸俗,当时是生殖优先的时代,女人只有一个重要目标,便是繁殖后代。
可是到了现代,女人的权利得到了重视,女人可以踏入社会与男人一样工作,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明显地提高了。女人不再是逆来顺受的生儿育女的机器了,女人也有了公民权,也有了恋爱权,可以堂堂正正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男人了。于是男人的地位便相应地降低了,以前的大男子主义再也行不通了,反过来为了取悦女人,男人还得尽心尽力地为女人服务,从这一点说来,男人则是进入了一个受压迫的时代了。不幸的是,我便是这么一个典型的男人。
我对自己的分析如果不错的话,我就是一位不折不挠的新时代的受难者了。我沉陷在自己的这种思索中,感到无法摆脱无从把握。反正必须去城堡,到了那里,所有的问题会有明了,都可以找到答案。
我这样想着,一口喝干了杯里剩下的咖啡,站起身去了地下停车场。从这里朝南去,上a10号高速公路,到布卢瓦下高速路转到国道,沿卢瓦尔河继续朝南,便是红城堡了。
我已经走了几次了!以前大都是傍晚六时或七时左右从巴黎出发,到城堡则是九时或十时。都是为了看月子受调教的情况,来去都是夜里,而且每次都会感到巴黎的秋天是多么地萧瑟。
可是今天,周围还分外明亮,道路两旁都是广阔的田野。田野都是绿色的,有树林,有庄稼,重重叠叠的绿色。这层次分明的绿色,显示着万物的蓬勃生机,可是我的心情却与这大自然恰恰相反,感到郁而又烦闷。
去年秋天,我在这条道上来来去去地好几回,当时心里时时有一种犯罪感和见不得人的沉重感,但说心里话,多少也是有点期待和快乐的。因为我每次去都会看到一些不同的新东西,有时还会被刺激得神魂颠倒,有时还会在车子里自慰,所以说尽管那时干的是坏事,但想到月子调教好了后又会回到我的怀抱,心里还是有着些许的快慰的。
可现在不同了,月子已将我甩掉,我是为了追寻她而赶到城堡去的。当然,我心里也有疑问,就是这样的女人值不值得我去追,这样的女人我何必要去追,我可以在心里用十分恶毒的语言诅咒她,我可以将车头掉回马上打道回府。
但是,我的车子还是在朝着南方飞驰。这是我的心受这大自然的吸引,或者说是我老马识途,无意识地在朝红城堡前进?总之,当我有些清醒时我的车已经下了高速公路到了国道上了。
紧靠着国道右边的卢瓦尔河面非常宽畅,河水缓缓地水波不兴,我不时从车窗里眺望着那泛着碧波的河面,心里的迷茫渐渐地消失了。
“是的,只有去城堡才是对的。”
这意识好像是上帝给我的启示,我心里只感到去城堡一定能找到月子的。
我已经不再犹豫。车子在左边是田野、右边是河流的道路上飞驰,不一会过了一座桥,再过去些便有一家小型旅馆和餐厅,隔了一条路,前面便是一个小山丘,那山丘上便是红城堡了。我将车子停在树阴下的道路一端,下了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甜甜的凉爽的空气是从那小丘上从那茂密的丛林中吹来的,我一口接一口贪婪地吸着,朝着城堡的坡道上走去。
以前可以将车一直开到小丘上的城堡门前,但现在我没有与城堡主人联系过,不敢贸然,只好徒步走上去。大约1oo米左右,坡道右边的树丛中可以看到教堂的尖顶和几家房屋。
以前来这里时是夜里,所以总是看到教堂里灯火明亮,也曾有过一次听到它那响亮的钟声。
坡道很徒,爬一段路要停下歇一歇,我站在坡道的中间朝下看去,那卢瓦尔河面一半已黯然失色,一半还有些波光粼粼,还有几尾水鸟在那河面上飞翔。
这小山丘上,暮色也终于降临了。我不知什么缘故心里十分地坦然起来,朝着芳草萋萋的山坡上望去,可以看到耸立着两个圆塔顶的城堡了。城堡前的一片喜玛拉雅杉树丛里有几个姑娘的倩影,她们都穿着洁白的礼服,是在摘野花,还是在散步玩耍?
远远看去,一望而知那些姑娘便是城堡里的人,那身超短的礼服打扮,是不是那些为月子按摩的姑娘呢?一种好奇心,使我穿过参天的大树林,踏着青青的草地朝杉树丛走了过去。
看清楚了,一共有四人,身材都十分苗条,有两位是咖啡头发,一位是红头发,还有一位是黑头发。我再朝近处走去,想看清她们的脸,但也许是她们发现了我,或者是她们出来的时间已到,她们已并排着朝城堡里走去了。
也许这里面有我熟悉的姑娘,因为我来过好几次,她们招待过我,给我领过路。
“你们好……”
我向她们打起了招呼,可她们却全然没听见似地过了吊桥,我随后追过去,到了桥边正在犹豫不决是不是追进城堡去,突然听到了一阵“轧轧”的声音,原来是吊桥慢慢地被吊上去了。好像是等着吊桥吊起似的,城堡里教堂的钟声又响起来了。
一下,二下,三下,清脆、宏亮的钟声连着敲了七下,我知道时间是晚上七点了。这时,只见吊桥的对面,有一位姑娘站在城堡门口,缓缓地回过了头来。
一瞬间,我的眼睛不动了,再仔细凝神望去,我不由得叫了起来:“月子……”一点不错,那回过头来的姑娘是月子。虽说她的打扮与城堡中其他姑娘一般无二,但她那黑黑的头发,白嫩的脸庞,大大的眼睛,挺挺的鼻梁,柔柔的嘴唇,圆圆的下巴,这一切都分毫不差,不是月子又是谁呢!“月子……”我又叫了一声,忍不住张开双臂挥动了起来,但是月子仿佛是对我笑了笑,马上便转过身去,与其他几位姑娘一起很快便消失在了那厚厚的城墙里面。
我一下子怔怔地不知所措了。好一会清醒过来,只见那吊桥已经吊起,像一块巨大的大黑板竖在了我的面前。
月子果然回到这城堡里去了。抛弃了丈夫,抛弃了父母,她投身到这城堡里去了!
我对着面前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原来如此……”
这里就是月子所说的“异常但却是正常,道德败坏却是人之常情”的地方啊!
我点着头,被清冷的晚风吹拂着,头脑开始平静下来,我心里确实对月子有着憎恨,有着埋怨,但刚才的那七下钟声已经将我的心灵净化过了一遍,现在我的心情是从未有过的清新,我的微笑也是从未有过的自然。
“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此时此刻,我总算心平气和了。我曾恳求城堡中的人将月子强行绑架到里面去的,可现在月子则自己跑了进去。我是想对月子进行一下惩罚,可月子却得到了快乐和欢娱。
从今以后,月子便与那些姑娘一起在这城堡里长住下了,在这里她会与那些男人过着下流但却优雅,淫荡但却舒适,呻吟但却快乐的生活的吧。
这样的生活是好是坏,我已经无法干涉了。如果能干涉,也是止不住他们那些荒淫无度的生活的。因为他们是将这样的生活认为是生命的惟一乐趣的,现在月子已经渡到了对面的世界,我则还留在这边,月子是月子,我则是我了,我们已是天上人间两茫茫了。
也许月子在找到新生活前会一直呆在城堡里的吧,她陷身在一个荒淫无度的地方,但却相信着那里有她需要的爱。
举目望去,太阳已经完全落下了,远处的森林已显得黑黝黝的一片模糊了。高高耸立着两个圆塔顶的城堡也像一尊巨大的鬼魅站在小山丘上,它周围石墙的窗户里已透出点点的灯光。
这以后,城堡中将是最热闹、繁华的时刻,丰盛的晚餐,奢侈的挥霍,醉死梦生的男男女女,当然,月子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月子是变了。我与月子之间也不再有哪怕是一根头发丝的联系了。有的只是我眼前的那道深遂不见底的鸿沟。那大黑板似地竖在我面前的吊桥,已经将我与月子彻彻底底地隔开了。不要说夫妻之情,就是陌路人般地打一声招呼也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之间早巳经横着一条鸿沟了,这是绝对不可能跨越的,可我有时竟会痴心梦想地要跨过去,竟会感到我与月子是夫妻,竟会感到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比学问要简单容易。
可是,现实打破了我这痴人的白日梦!我现在才明白,我这次来法国,来巴黎,来红城堡,其实就是为了弄清楚这一现实的问题而从日本千里迢迢赶来的呢!
我又一次探看了一下横在面前的那条无底的鸿沟,嘴里轻轻地念道:“再见。”再向面前耸立在山丘上,我已无法进去的红城堡,欠了欠腰说道:
“再见。”
最后,在心里对着我费尽心机,但还是没有得到的月子,还有十分自尊的、孤芳自赏的、唯唯诺诺的、瞻前顾后的我自己,轻声地喊道:
“再见……”
虽说还没有什么把握,但我相信明天,也许我会碰上一个柳暗花明的明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