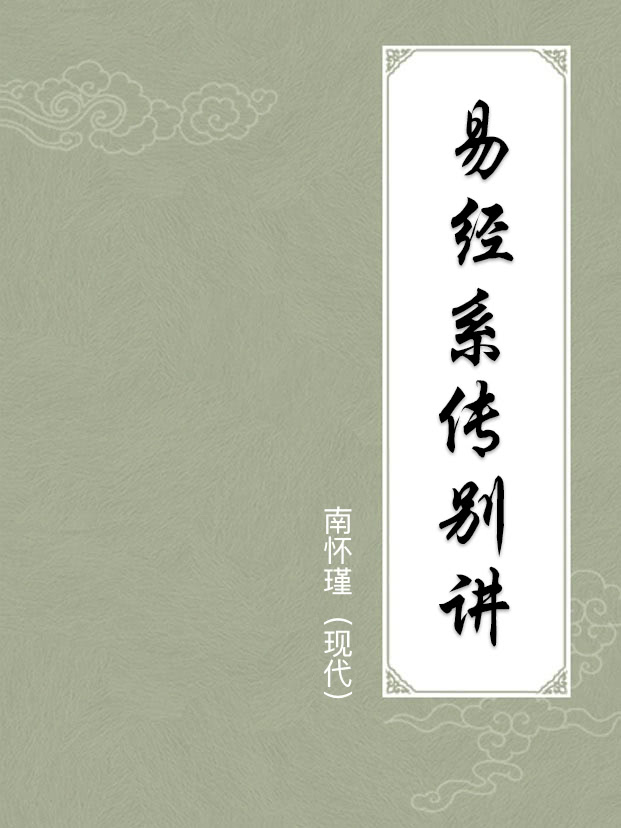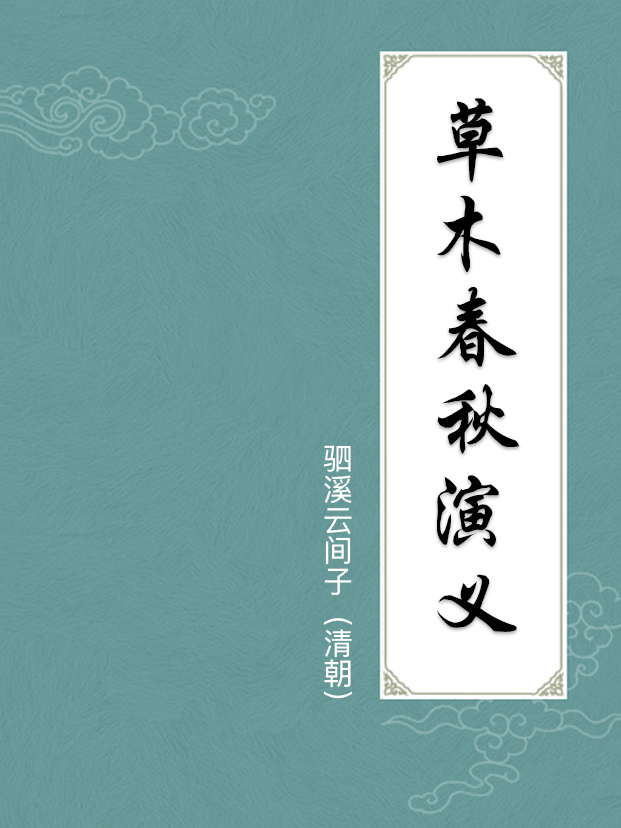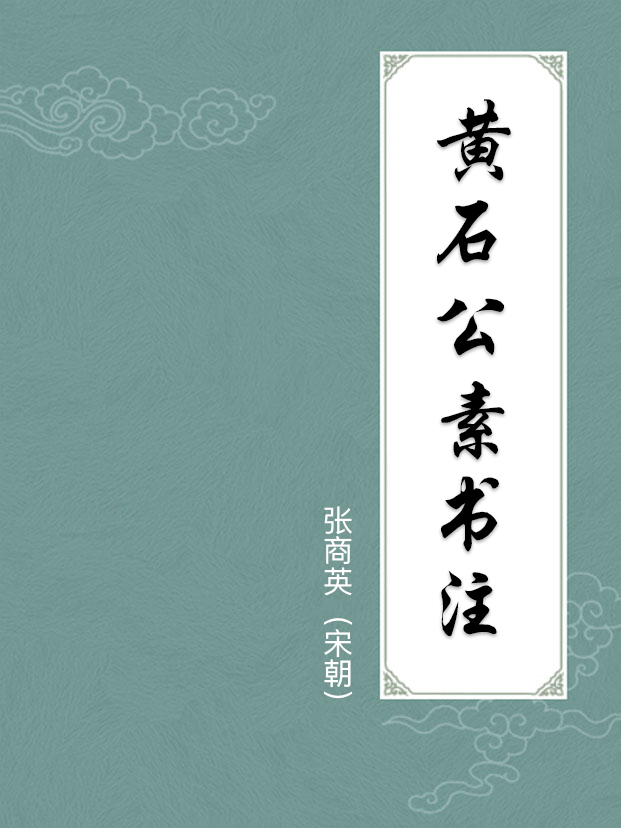中国美术系Apollonian Art与西欧美术系Dionysian Art之别,前者主幽静、婉约、清和、闲适,后者主刚毅、深邃、情感、淫放。中国美术,技术系主观的(如文人画、醉笔),目标却在神化,以人得天为止境;西洋美术,技术系客观的(如照相式之肖像),目标却系自我,以人制天为止境。
西洋近代画最受东方画影响,注意笔致、气韵,然除少数人,如Cezann外,尚未学得用笔。
仿画希腊罗马石膏像,在西方进步的美术学校此调久已不弹,然在吾国美术学校正在盛行。
德国学校有购买有正书局翻印古画为学生图画蓝本者。中国学校则不然。
中国人之西洋画,如中国人用猪油做的西洋点心,一样令人无法消受。
附 跋徐(左讠右于)《中西艺术论》
徐君所言,自是一种看法,一种说法。然予诚不敢苟同。以中国艺术为分析的,西洋艺术为整合的,予以为不然。若一枝梅花,一句佳诗,小巧玲珑,意在疏朗,以一部攫住全部精英,使人神会,无所用于全部之描写也。况风水之学正系发源于全片景物的艺术鉴赏,或为五虎朝天,或为苍龙吸水,皆顾到全部之鉴赏处。若书法之重间架行列,画法之重经营位置,皆超乎骨法用笔应物类形局部问题。艺术之事,要在有中若无,无中若有,虚中见实,实中见虚,何所取乎全部之描写?故所谓分析的。恐只是注重潇洒空灵之意耳。至于所谓“中国艺术重要在于从自然中取来属于自己,把自己的能力与欲望放进去”,正是中国艺术强处。如予所谓中国美术,技术系主观的(如文人画,醉笔),目标却在神化,以人得天为止境;西洋美术,技术系客观的(如照相式的肖像),目标却系自我,以人制天为止境。艺术而不表现吾人之欲望,不以吾之欲望神化之,有何意味?良辰美景自是良辰景,若不加三字“奈何天”,则缺乏诗意。盖人不加以唏嘘惋叹则辰不良而景不美也。世上岂有辰自良而景自美乎?
杂说
《秋水轩尺牍》所以曾风行一时,是因为中国寒士多,书中多觅馆求差语,甚有用处。
“思君”系古文中最无耻的话,然无人耻之。屈子、贾谊皆患此毛病。歌颂圣德,亦极肉麻,但前人亦不觉其肉麻。
孔子三过卫。孔子说话时,卫灵公只顾仰观飞雁。料想当时孔子情极难堪。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一句话,系在卫与南子同车时,见路人只看南子不看他的感慨。
孔子亦曾骂当时政客为饭桶。子贡问:“今之从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筲之士,何足算也!”斗筲系承米器,向来经师解为喻器量之小,不对。今人骂人,应曰承米器,或曰斗筲,比饭桶古雅,而语有所本。
苏东坡好吃鼻液,称其味甘美。又主张以口中津液漱口,是中国人漱口之最早者。(《上张安道书》论养生诀曰:“若鼻液亦须漱,使不嫌其咸,炼久自然甘美。”)
爱国系爱己之一种。爱乡系爱莼羹。
现代学生反对考试甚是。但同时要求及格分数毕业文凭则甚无聊,且矛盾。当今学校,应分学生为二种,一严格考试及发给文凭,一不考试不给文凭。如是天才与蠢才方不致同时同班毕业。
今日学生八时上课四时下课。课室中不许看书。故今日学校是把学生关起不许看书之最理想制度。
一群学生闻铃上课,闻铃下课,与一群羊闻铃出牢闻铃入牢,没有区别。
所谓一百分,系能答先生心中所要你答的话。高材生是教员肚子里的应声虫。凡能意见与先生雷同者或与书本雷同者,谓之高材生。
三十年前谈变政,办洋学堂者,未知彼辈今日所造之孽。
现在各学校课室中似乎都贴上一张章程:第一条,只许静坐,不许读书;第二条,不许用头脑,自有主张;第三条,不许交头接耳交换意见;第四条,不许吸烟以免触起灵机,天才出火。遵此四条校章者,年终品行一百分。
冒孔家牌者,非今日之《论语》,乃隋朝的王通。本刊偷《论语》之名,不偷《论语》之实。文中子偷《论语》之实,不偷《论语》之名。兹联语五则:
道理参透是幽默,性灵解脱有文章。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对面只有知心友,两旁俱无碍目人。
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
领现在可行之乐,补生平未读之书(录袁子才与人书语)。
宗教与脏腑
--有不为斋随笔
《论语》曾刊龚定盦论肾主记忆及通呼吸语,以见古人生理观念之一斑:苏东坡上张安道书亦有鼻液下咽之养生妙论。近偶读俞正燮《癸巳类稿》,“书人身图说后”,更觉其味湛然。据篇首第一句俞所见书,是“西洋罗雅各龙华民邓玉函所释其国人身图说”。“其国”二字甚妙,盖谓其国人身与中土人不同也。俞谓“此书在中国二百年矣,未有能读之者”。考此三人中,邓玉函于一六二一年莅华,一六三〇年逝世,在华期间最短,故译书当在此九年期间内。论文大旨,是阐明中外人脏腑经络确有不同,而结论谓因脏腑之不同,故宗教亦不同,其中演绎根据,似只凭直感而已,恐怕不易用科学方法证明。俞氏之言曰:
“其人南怀仁于康熙时上穷理学书云,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头脑之内,亦不出此书之旨。惜脏腑经络,事非众晓。脏腑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传教,欲中土人学之。不知中国人自有脏腑经络,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国脏腑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于西洋教何益?西洋人倘知此,亦当殷然自惜,掉首茇舍,决然舍去者欤?!”
俞所谓中外脏腑不同,据他看这本书的结论是这样的:
“中土人肺六叶,彼土四叶;中土人肝七叶,彼土三叶;中土人心七窍,彼土四窍;中土人睾丸二,彼土睾丸四;中土人肠二,彼土肠六;中土人肝生左,肺生右,肝系在心系左,彼土心系在肝系左;中土人心带五系,彼土心有大耳二,小耳十一,则所谓四窍者,又有二大孔,十一小孔。”
按西洋人身解剖学发达于十七、十八世纪,血脉循环之理发明于Harvey(参见Buckle《英国文化史》))。罗雅各等所译一书着作既在十七世纪初叶,固然未必尽是,如所谓心有十一小耳,未知究何所指。然大体上,比中土高明,如中说肝在左,心在右,似错误的太离奇了。未知中国人观察力,何以如此薄弱?心之搏跳,到底可以按手扪得。至于睾丸四,当系指副睾丸或指摄护腺,在图说上,与睾丸同形,显然为四,未免使俞惊叹。
俞考定生理之法有二:一,自扪;二,引证古书。儒药所以为儒,就在此点,自扪法,可行于睾丸,故俞曰“及儒自扪睾二,隐约其四,睾之文耳”。“文”当指睾丸之输管等,隐约合睾丸扣之似有四也,殊不知西人却不是如此扪法。引证古书尤妙。其论据是《洗冤录》,《汉书》,《素问》,《战国策》等,真令人哭笑不得。根据这些书,他证明“人生实异”,不可强同。有一段很妙:“向读金楼子,言纣剖比干心有十二穴,其事无所出,或此是西方古说,梁元帝得之西僧者,因以附之比干。此书初译,幸与儒之不读书不通经脉脏腑者商之,故得存其异趣,”其意若曰,若不幸与通经脉读诗书之儒商之,必改为七窍,而西土异趣遂不得传。他据《灵枢》《本神》,知道男子如精是藏于肾的,“肾藏精,精者髓也。《海论》云,脑为髓海,是精由脑随脊而下。今据此书,则西洋人生源已异。古经言精路不由与胃膀胱,不为不净。精髓督脉而下,故谓之精,而此书言要肾积质具(与?)积溺,则佛书以出精为出不净,自是西土禀赋不同,亦不足怪。”这是俞的精出脑说,及精实净说。
他又说子宫中西不同,曾引汉书,证明“羌以妇人肠为子宫”(虽然论据甚薄弱);“羌汉不同,则西洋与中土不同,均不足怪。”他引佛书描写子宫形状,代表西土曰:“佛家禅秘要法云,子藏在生藏之下,熟藏之上。如猪胞,如芭蕉叶,如马肠,如臂钏,形上圆下尖如贝齿。此书(《人身图说》)言子宫有颈,以硬肉成,能缩展拳张,长圆而空,如狗喉管,皱缩不平,则非膀胱之渗者。可知言子宫外广而短,户有细皮阻冷气,亦为中土人所不能言。”
以上可见俞氏一般论调了,读了甚有趣,但不疑其篇末匆有宗教与脉胳之怪论也。古读书人好作零星笔记,好随意揣侧下论断,极少缜密理论,大抵与俞相似。闻友言有西人问,相传中国女人阴户是横的,未知确否,是与俞一般见识,且发见于二十世纪,俞不足深责矣。
又《癸巳类稿》十五卷《天主教论》,将拜日教,拜火教,佛教并为一谈,名为西土,也有相当滑稽。其说耶稣,竟谓“尔撒(即耶稣)圣人者,亦阿丹(即亚当)当圣人之后。……或通其妻,托求异术。尔撒告妻,畏人缚发。于是夜暗系其发,仇至遭擒,便被杀害。其徒愤恨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复事天。”是将旧约犹太英雄参孙事,误托耶稣,且耶稣无娶妻。其考十字架,谓系“翘手脚视日”,符拜日教之义。末云:“今天主教皆罗刹,力距佛,佛以罗刹名被之夜叉戾厉,洋人巧器,亦呼为鬼工,而罗刹安之。其自言知识,在脑不在心,盖为人穷工极巧,而心窍不开,在彼国为常,在中国则为怪也,乃好诱人为之,而自述本师之事,亦不求所本。然则耶稣在罗刹为持世之人,而他部之人入其教,则亦无心肝之人矣。”
与德哥派拉书
--东方美人辩
德哥派拉曼修:豫丰泰握别以来,忽忽经旬,其中事故,诚有出人意外者矣。犹忆是夕畅饮绍兴,吃螃蟹外,席上有数位誉冠一时之上海名媛东方玛但拿,因思及大着小说《夜车中之玛但拿》,曾劝君作一篇素描,名为“螃蟹与玛但拿”,而君于螃蟹则无意,于玛但拿则倾耳以谈,座间玛但拿诙谐百出,意兴酣豪,教我饮酒,教汝吃蟹,虽汝我皆不可教,而此情此景,何能忘之?岂料半月之间,先生离沪赴平,遂有风云不测,大祸临头也耶?当君抵掌谈心之时,窃谓先生幸得与中国风雅名淑见面,对于中国女子,或可翻然得新认识。岂知曼修竟因此入迷,褒扬过甚,语无忌惮,遂为召祸之由耶?现竟有北平潘女士向曼修示威,以褒扬为暗讽,虽曰中国人善读反面文章,曼修毋亦惊愕不知所以乎?兹特为先生解释中国摩登女郎之心理如下,以释疑惑。
据余所见西方文人游华,未有不窃窃称道,中国女子幽娴秀娟之雅致及其凌波曲线之娉婷,以为东方个别风韵,为西土所无者。惟曼修而外,未有公言中国女子之美者。报载曼修悍然无忌,再四声明既好中餐,又好中国女人,甚谓或且将放弃终生独身主义而娶吾国女子,是诚吾国报界所未之前闻。盖向来上海西人未闻有称赞中国人之衣食宫室或中国女子者,即使有之,亦不刊之报章。英人密室闲谈,赧颜供认中国肴馔之佳烹调之美者,固或有之,但若有英人在俱乐部公然声明好中菜,或好中国女子,或好中国人民,则未有不蒙“半痴”(queer)之讥,而失其社会上之位置者。故如美国每一小城必有两三家中国“杂碎”饭店,上海则一家亦不可得。闲尝见欧人便衣粗服,东张西望偷入南京路新雅饭店,虎噬狼吞,大啖大嚼,至杯盘俱空,拂须而去。但谁曾看见体面西洋士女高帽燕服公然跨入新雅之门聚宴者乎?盖自英人视之,社会直无此礼法,公论亦所不容。今者风俗既成,即中国人亦不敢在外人之前,依吾国风俗食华餐,穿华服,说华语,居华宅矣。曼修乃于此际,出而扬言中国女子之美,其谁信之?最不信者,尤莫如中国女子。中国女学生以曼修为戏言,北平潘女士以曼修为讥讽。群雌粥粥,佥谓曼修滑稽成性,且--此最令人难堪者--有意戏弄中国女子。大晚报“火炬”有女士投稿,问曼修何不讥讽巴黎女子?潘女士质问:曼修为文人,何以不谈文学而谋女子,恰似大学二年级课室向话。且曼修既言欲娶中国女子,何以不言恋爱?未言恋爱先言结婚,亦失文明人态度。有一作者附和反诘曰:曼修以为中国女子服装“裹身”,然巴黎女服何尝不“裹身”乎?《时事新报》“青光”作者则取反躬自省态度问曰:何以曼修不讥西洋女子,独讥吾国女子?吾国女子其深思猛省乎?某女士亦发辞严义正之呼声曰:吾辈虽要体面,不可容人任意侮辱,然亦自身须有彻底之觉悟,其辞可悯,其诚亦可哀。种种怪论,轩然大波,皆由曼修尝谓幽默之东方美人为曼修之理想女子一语所掀起。事之怪,有怪于此者乎?
德哥派拉曼修,吾人遭人侮辱欺凌,固早已心灰意冷,故谁有说一句中国好话,亦不敢相信。风俗所趋,积重难返,今者吾辈见有欧人游观天坛祈年殿,神魂怡荡,恭立不语,亦觉得祈年殿应赧颜低首,觳觫屏营,不知所措矣。吾所悔者,祈年殿非铜骨洋灰所筑成,吾所羞者,祈年殿楼仅有三层,不及沙逊大楼之高耳。假使此洋人果发一语,称赞该殿之美,该殿有知如潘女士者,亦必抗议曼修之戏言,或且将控以有意侮辱之罪。其情景恰似苦命丫头一旦遇人拍肩,亦必反唇相讥而诬为非礼,曼修固已出于非礼矣。为曼修计,惟有再三申明东方美人确为曼修所崇拜,始可取信于天下,而下次再有西洋小说家,发表与君同调之意见,庶几不被中国英雄大兴问罪之师乎?
自然,曼修知吾意。潘女士之豪迈不肯示弱,正是外强中干,西俗所谓infeiority comlpex也。曼修为小说家,当知有逊色之观念者,固不必真逊色于人。只要时时日日向一人曰“汝不若人”,不久其人亦自以为不若,此教会星期日校之所以养成许多“魔鬼子”也。小儿到校,闻师言好糖饵游玩即系魔鬼子,故废然返家以魔鬼子自居,以告父母,父母愕然。不有星期日校师,何来魔鬼子?先生之白种同胞,即东方之星期日校师,日日刮脸修胡,高帽白领以告我边幅不修之同胞曰:黄肤平脸者魔鬼子,而吾人亦几置信。自然上海英人俱乐部之所以夜郎自大以矜我者,非尽出于博爱,有所为而然也。夫生活竞存至不易,吾辈常人大都又系碌碌庸才。对镜自览,能无汗颜?以此治事,何事可治?故或托庇于名门显族以自慰曰,吾固贤人之子孙也。至若此层办不到,如东方外人不必皆有名门显族可以托庇,则进一步托庇于上古之祖宗曰,吾固优种民族之子孙也。如此则借镜生辉,吾心泰然,万事如意,人人自信而不复致疑于自己之庸碌。美国心理学教授之言曰,自信即系成功之母,东方外人岂可无自信?故其卑人,非欲卑人,乃欲以矜己而已。且如此自信,对中国文物亦可放心不必研究。此姑勿论,余所欲言者,潘女士之何以心虚。上海英人既如此矜伐以骄我,又加以西洋裸体画及西洋电影明星如梅薇丝,嘉宝之丽质以炫我,遂使中国女生正自悔父母生我无金发碧眼以为恨。潘女士岂料到黑发柳腰之中国女郎亦可使欧人销魂动魄乎?且纵使称赞异邦女子可算为侮辱,则使梅薇丝,嘉宝见到中国电影广告称赞彼姝之肉感香艳,非起诉讼不可,此又岂潘女士所想到者乎?此姑勿论。然电影广告固已移我风而易我俗,其最明显证据,即潘女士之抗议曼修表彰东方美人也。东方美人,何言之虐!曼修何不谈文学,而仅讥讽吾辈弱质女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