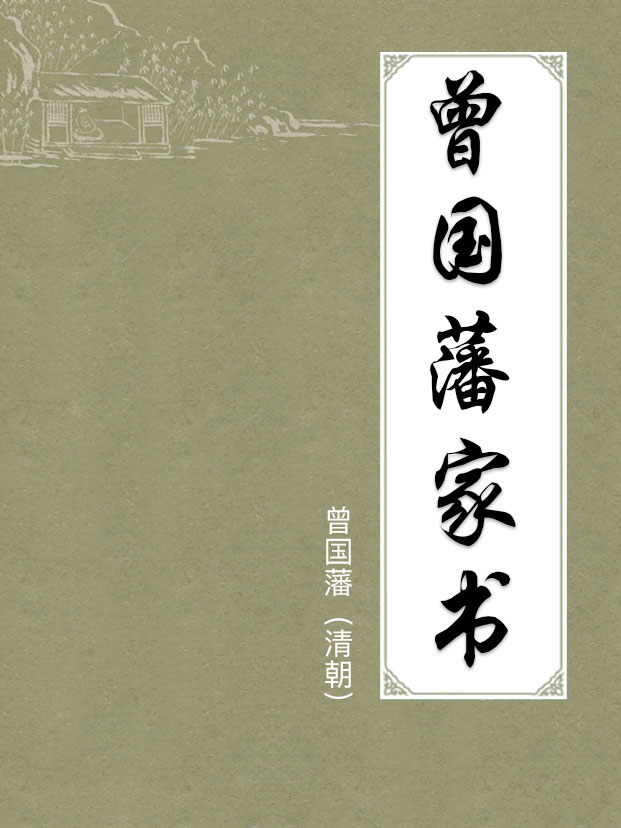同时,我也认为在说话(即今日之所谓语言)的进展史上,女人也比男子占着更重要的地位。说话的本能在女人是得天独厚的,所以我深信她们对于人类语言的演进,一定有着比男人更重大的贡献。我想古代的人类一定是沉默寡欢的动物。当男性人猿离开洞穴去打猎时,邻居的女人在她们的洞穴前无所一事,一定谈论威廉是否比哈罗好,或哈罗是否比威廉好,或是哈罗昨晚多情得讨厌,他性子多么暴躁。我想人类的语言必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此外别无他途。人类以手去取食,使颚部不必再担负去拿食物的任务,结果使颚部逐渐低平,逐渐变小,这对于人类语言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这种姿势最重要的结果,是把两手解放了,使它们可以把东西拿起来观察研究,像猴子捉虱为乐那样,这种动作便是研究精神发展的起点。今日的人类进步大抵还须归功于捕捉那些扰乱人类的虱子。一种好奇的本能也发展出来了,使人类的灵心可以很自由地,用嬉戏的态度去探究各种题目和社会疾患。这智能上的活动和寻索食物并没有关系,而完全是一种人类精神上的训练。猴子捉虱的目的,不是想把它们吃掉,而是当一种游戏玩着。这便是有价值的人类学术和智识的特征,对事物本身发生兴趣,心中存着嬉戏的、闲逸的欲望想把它们了解。而并不是因为那种学问可以直接使我们的肚子不饿。(如果这里有自相矛盾的话,那么,以中国人的立场来说,我对于自相矛盾这件事是觉得快活的。)我以为这是人性的特征,对于人类尊严有着极大的帮助。追求智识的方式,不过是一种游戏:所有一切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以及创立过有价值的伟大事业者,他们都是如此的。从事医学研究的人觉得对微菌所引起的兴趣比对人类更大;天文学家很起劲地记录一颗距离我们有几万万里远的星辰的动作,虽则这颗星辰对于我们人类一点没有关系。一切动物,尤其是年轻的,都有这种游戏的本能,但也只有人类把这种嬉戏的好奇心发展到值得重视的地步。
回向常识
中国人都憎恶“逻辑的必要”那个名词,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世事之中无所谓逻辑的必要。中国人对于逻辑的不信任,起点于不信任字眼,再进而惧怕界说,最后则对一切系说、一切假说表示天性的憎恨。因为使哲学派成为可能者,都是字眼、界说和系说的罪恶。哲学的腐化起于对字眼的偏见。中国作家龚定庵说,圣人不说话,有能为的人才说话,愚人才会做辩论--其实龚氏本人就是一个最好做辩论的人,但他仍说这句话。因为这就是哲学的悲惨经过:即哲学家不幸都是好说话的人,而不是肯守缄默的人。所有的哲学家都喜欢听他自己的语声。即如老子,他虽是第一个指点给我们知道“大块”是无言的,但他自己则在出函谷关去隐居深山,乐享余年之前,仍免不了听从人劝,遗留下传诸后世的五千言。尤其足以代表这类天才哲学言谈家的就是孔子,他游遍“七十二国”以说诸国之君;又如苏格拉底,他在雅典的街上走来走去,遇到走路的人即叫住他,问他几句话,以便他自己可以发生聪明的意见给自己听。所以“圣人不多言”这句话乃是相对的说法。不过圣人和才子之间仍有一种区别,因为圣人的谈到生活,都是以亲身的阅历为中心;才子则只知道研究解释圣人的说话,而笨人则更是只知道将才子的说话咬文嚼字地辩论。在希腊的修辞学家当中,我们看见这种专以咬文嚼字为尚的纯粹谈论家。哲学本是一种对智慧的爱好,已变成了对字句的爱好,等到修辞学的风尚渐渐滋长,哲学便和生活越离越远了。等到后来,哲学家竟专顾多用字眼,多用长的句子;短短的警语多变成了长句,句子变成了论据,论据变成了专书,专书变成了长篇大论,长篇大论变成了语言学的研究;他们需要更多的字眼以定他们所用的字眼的界说,并将他们归类,他们需要更多的派别以区别和隔离已经设立的派别;这个程序接连不断地进行着,直到对于生活的直接地、切己地感觉或知悉完全丧失,致使外行竟敢于诘问:“你在那里说些什么?”同时,在后来的思想历史中,少数几个对生活本身感觉到直接撞击的独立思想家--如哥德、萨缪尔、爱默生、威廉?吉姆斯--都拒绝在谈论家的胡言乱语中发言,并始终极固执地反对归类的精神。因为他们是聪明的,他们替我们维持着哲学的真意义,就是生活的智慧。在许多情形中,他们都抛弃了论据,回向警语。当一个人在丧失了说出警语的能力时,他方去写长篇;而他在论证之中依旧不能明白发表他的意思时,他方去着作一本专书。
人的爱好字句,是他走向愚昧之途的第一步,他的爱好界说乃是第二步。他越从事于分析,他越需要界说,他越加定界说,他越是趋向一个不可能的逻辑的完美境界,因为企求逻辑的完美就是愚昧的迹象。因为字句是我们思想的材料,所以定其界说的企图乃是完全可嘉的,于是苏格拉底即在欧洲创始了一个定界说狂。其危险在于我们意识到曾由我们定其界说的,字眼时,我们便不能不将用以定界说的字眼也定出它们的界说来,因此,其结果:除了用以定生活的界说的字眼以外,我们又有了专用以定别的字眼的界说字眼,而定字眼的界说这桩事便成了我们的哲学家的主要成见了。忙碌的字眼和空闲的字眼之间显然有一种分别,前者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尽它们的责任,而后者则只存在于哲学家的研究团体中。此外苏格拉底和弗兰西斯?倍根的界说,和现代大教授的界说之间也是有着一种分别的。莎士比亚对生活有着最切己的感觉,但他也居然能从容地过去,而并没有做什么定界说的企图,或也可说是因为他没有做定界说这件事,所以他所用的字眼都有着一种别个作家所缺少的“实体”,而他的文字中也充满着一种现代所缺少的人类悲剧意味和堂皇的气慨。我们无从将他的文字限制到某一个动作效能的范围之内去,正如我们的无从将他的文字限制到一个对妇女的特别观念里边去。因为它们都在有了定界说的性质时方使我们的思想成为僵硬,因而剥夺了生活本身的发光的、幻想的色彩特质。
但如若字眼为了必须的理由分割了我们的在表示程序中的思想,那对于系统的爱好更能损害我们对于生活的深切的知悉。系统不过是一种对真理的从旁斜视,因此,这系统越加有着逻辑的发展,则那种灵心上的斜视也越加可怕。人类只想看见偶然所能看到的真理的片面,并将它发展和提升到一个完善的逻辑系统的地位的欲望,即是我们的哲学为什么会和生活势必越离越远的理由。凡是谈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损害了它;凡是企图证明它的人,都反而伤残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个标识和定出一个思想派别的人,都反而杀害了它;而凡是自称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个真理,等到被竖立成为一个系统时,它已死了三次,并被埋葬了三次了。他们在真理出丧时所唱的挽歌就是:“我是完全对的,而你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所埋葬的是哪一种真理在根本上无关重要的,不过根本上他们总是已经埋葬了它。因此真理便如此地在防护它的人的手中受到了虐待,而一切哲学的党派,不论古今,都只是专心致力于证明一点,即“我是完全对的,而你是完全错误的”。德国的哲学家们写了一本挺厚的书,想要证明某一种有限制的真理,但结果反而将那真理变成一个胡说,这班人大概可算是最坏的冒犯者了,不过这种思想的疾病在西方的思想界差不多是随处有的,而只在深浅中有些分别罢了,而在他们越趋于抽象时,这个病症也越深。
这种不近人情的逻辑,其结果是造成了一种不近人情的真理。今天我们所有的哲学是一种远离人生的哲学,它差不多已经自认没有教导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智慧的意旨,这种哲学实在早已丧失了我们所认为是哲学的精英的对人生的切己的感觉,和对生活的知悉。威廉?吉姆斯即称这种对人生的切己的感觉为“经验的要素”。等到日子长久之后,威廉?吉姆斯的哲学和逻辑所加于现代西方思想方式的蹂躏必会一天厉害一天。但我们如想把西方哲学变成近于人情,则我们必须先将西方逻辑变成为近于人情。我们须回到一种对现实和生活,尤其是对于人性,急于接触的思想方式,而不单是求得不错,合于逻辑,和没有不符之处便算完事。我们对于迪卡尔(Descartes)着名的发现:“我思想着,所以我存在着。”这句名言所表达的思想的疾病,应该拿华德?惠德孟所说的那句较为近于人性和较为有意义的话:“我照现在的地位,我已尽够。”去替代它。生活或存在无需跪在地上恳求逻辑代它证明世上确有它这样事物。
威廉?吉姆斯终其身在那里企图证明中国式的思想方式,并替它辩护,不过自己没有觉得罢了。当中不过有着下列的一个分别:他如果真是一个中国人,他必不会用这许多字眼去做他的论证,而只将用那么三五百个字写一篇短文,或在他的日记中短短的写上几句话便算完事了。他将要对着字眼胆怯,恐怕越多用字眼,便越会引起误会。但威廉?吉姆斯在他对生活的深切感觉,对人类阅历的透彻,对机械式的理智主义的反抗,对于思想切心想保持它的流动状态,并对那些自以为已经发现了一个万分重要的、绝对的、无所不包的真理,而将它纳入一个自以为满足的系统中的人们的不耐烦当中,他简直就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坚持在艺术家的意识上,属于知觉的现实比属于概念的现实更为重要这一点上也像一个中国人。其实所谓哲学家者,他就是一个时常将他的感觉力集中于最高的焦点去观察生活的变动,随时预备碰到更新的和更奇怪的矛盾事情,前后不符的事情,和一切不合于常例的事情。在他的拒绝一个系统之中,他所拒绝的并非因它不对,而只因它是一个系统,在这个举动中,他实在破坏了西方的哲学派。照他的说法,对于宇宙的一元概念和多元概念之间的分别,实是哲学中一个最重要的分别。他使哲学有放弃空中楼阁而回到生活本身的可能。
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他还有一句聪明的话,这句话很像吉姆斯的口气,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世界并不是一个三段论法或一个论据,而是一个生物;宇宙不做声说话,只是生活着;它并不做什么辨认,只是进行着。某英国天才作家说:“理智不过是神秘物事中的一个节目;而在最高傲的意识国的统治的背面,理智和惊奇是涨红了脸相对着。不可避免的事情变成了平凡,而疑惑和希望则成了姊妹。宇宙是粗野的,如鹰的翅膀一般带着一些竞技的意味,这还算是一件可喜的事。大自然就是一个神奇之迹,同一的事物不再重回,而即使回来也必是已经不同的。”在我看来,西方的逻辑家所需要的只是一些自谦心;如有人能够将他们的脑袋肿大症医好,则他们就能得救了。
近情
和逻辑相对的有常识,或更好一些的说法:还有近情的精神。我以为近情精神实是人类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情的人实在就是最高形式的有教养的人。世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他只能力争上游去做一个近乎情理的生物。我正期待着世界上将有一个世人在个人的事件上,并在国家的事件上,都会得着这个近情精神之鼓舞的时期。近情的国家将生活于和平之中,近情的夫妻能生活于快乐之中。在我替我的女儿挑选丈夫时,我将只有一个标准:他是否是一个近情的人?我们当然不能期望世上有终身不相骂的夫妻;我们只能期望他们都是近情的男女,只近情的相骂,并近情的言归于好。我们只有在世界的人类都是近情的人时,才能得到和平和快乐。这近情的时代,如果有来临的一天,则就是和平时代的来临。在这时代中,近情的精神必会占最大的势力。
近情精神是中国所能贡献给西方的一件最好的物事。我并没有说中国那些向人民预征五十年钱粮的军阀是近情的;我的意思只是说,近情的精神乃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她的最好的方面。我这个发现曾偶然由两位久居中国的美国人所证实。其中的一位居住中国已经三十年,他说,中国的一切社会生活乃是以“讲理”为基础的。在中国人的争论之间,他们最后的一句有力的论据必是:“这岂是合于情理的吗?”而最严重的、最平常的斥责之词就是:这人是“不讲理”的。一个人如若在争论之中自承不近情理,则他已是输了。
我曾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说过:“在一个西方人,一个说法只须合于健全的逻辑的,他便认为是已很充足。但在一个中国人,则一个说法虽然在逻辑上已是很对时,他也还不肯认为充足,而同时还必须求其近于人情。‘近情’在实际上比合于逻辑更为人所重视。Reasonsbleness这个字,中文译做‘情理’,其中包括着‘人情’和‘天理’两个原素。‘情’代表着可以活动的人性原素,而‘理’则代表着宇宙之万古不移的定律。”一个有教养的人就是一个洞悉人心和天理的人。儒家藉着和人心及大自然的天然程式的和谐的生活,自认可以由此成为圣人者也不过是如孔子一般的一个近情的人,而人所以崇拜他,也无非因为他有着坦白的常识和自然的人性罢了。
人性化的思想其实就是近情的思想。专讲逻辑的人是永远自以为是的,所以他是不近人情,也是不对的;至于近情的人则自己常疑惑自己是错的,所以他永远是对的。近情的人和专尚逻辑的人,他们的不同处可以在他们信札后面的附言中看出来。我最爱读我的朋友所给我的信后的附言,尤其是那种和信的正文互相矛盾的附言。这种附言里边包括着一切近情的后想,一切疑惑不决之点,和忽然而发的聪明说话和常识。一个温和的思想家就是一个在用长篇大论的论据企图证明一个说法之后,忽然回到了直觉的地位,由于一阵忽然而发的常识,立刻取消他以前所做的论证而自认错误的人。这就是我所谓人性化的思想。
我们只需拿各人所写的信来看看,专尚逻辑的人必是在信的本文中罄其所欲言,而近情的人,即有着人类精神的人,则必是在附言中说他的话。譬如一个人的女儿请求她的父亲许她进大学读书,她的父亲或许在回信之中列出许多极合于逻辑的理由,第一怎样,第二怎样,第三怎样,例如:已有三个哥哥在大学读书;负担已经很重;她的母亲正在家中患病,需要她在旁服侍等等。他在信末署名之后,又加写了一行附言:“不必多说了,一准在秋季开学时入校吧。我总替你想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