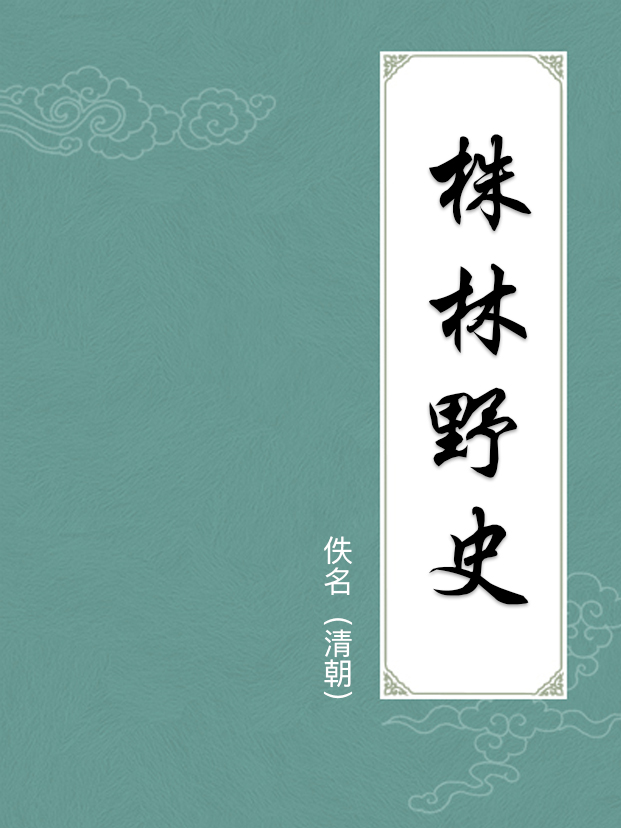话说孔甯认的,是仪行父,见孔甯走来,逐一手拉住孔甯,走到僻之处,附耳问道:“主公在何处射猎?今夜在何处住下?以当实一情一告我,勿得隐瞒。”孔甯见不能讳,只得直言。仪行父知是孔甯荐,顿足说道:“如此好事,如何让你去做?”孔甯道:“主公十分得意,第二次让你做好事便了。”二人大笑而散。
到了次日,灵公早朝礼毕,百官俱散,召孔甯至前,谢其荐举夏姬之事成。召仪行父问道:“如此乐事,何不早奏於寡人,你二人却占先头,是何道理?”孔仪二人奏道:“臣等并无此事。”灵公道:“是美人亲口说的,卿等不必讳矣。”孔甯道:“譬如君有味,臣先尝之,若尝而不美,不敢荐於君也。”灵公笑曰:“譬如熊掌,奇味就让寡人先尝也不妨。”孔仪二人俱大笑不止。灵公又道:“你二人虽曾入马,他偏有物送我。”乃脱下衬衣示之,「你二人可有麽?”孔甯曰:“臣亦有之。”孔甯遂撩衣,现其绣裆。道:“此非美人所赐乎?不但臣有,行父亦有。”灵公问:“行父是何物?”行父解下碧鸡襦与灵公观看。灵公见之,大笑道:“我叁人随身俱有证见,异日同往株林,可作连床大会。”一君二臣在朝堂戏谑。这话早传出朝门外,恼了一位正直之臣,咬牙切齿的道:“朝廷纪纲之地,都如此胡言乱语,是何道理?陈国之亡,屈指可待矣。”遂复身入朝门进谏。正是:
一自一古忠邪难并立,徒怜比千志节高。
却说一君二臣正在朝堂戏谑,忽见一人执笏赶进朝门。叁人瞪目视之,见是冶。孔仪二人素惮冶正直,今日不宣一自一至,必有规谏。逐先辞灵公而出,灵公抽身欲起御座,冶连忙上前拉其衣而奏曰:“臣闻君臣主敬,男一女一主别。今君臣宣一婬一,互相标榜,失君臣之敬,无男一女一之别,沦灭已极亡国之道也。君必改之。”灵公一自一觉颜汗,随曰:“卿勿多言,行且悔之矣。”冶辞出朝门,孔仪二人尚在门外打听。见冶怒气冲冲而出,闪入人空中避之,冶早已看见。将二人唤出责之曰:“君有善,臣宜宣之;君有不善,臣宜掩之。今子为不善,以诱其君,而又在朝堂扬其事,何以为训,甯不羞乎?”二人不能措对,虽谢教。冶去了。
孔仪二人又来见灵公,述冶责备之语。遂道:“主公日後不可游株林矣。”灵公道:“卿二人还往否?”二人笑道:“彼以臣谏君,与臣无涉,臣等可往君不可往。”灵公奋然曰:“寡人甯得罪於冶,安肯舍此乐地乎?”孔仪复奏曰:“主公若往株林,恐难当冶强极之谏。”霆公道:“二卿有何策,令冶勿言?”孔甯道:“除非使他不能开口。”灵公道:“彼一自一有口,寡人难禁之不言。”仪行父道:“孔甯之言,臣知其意,夫人死则口闭。主公何不传旨,杀了冶,则终身之乐无穷矣。”灵公道:“寡人不能。”孔甯道:“臣使人刺之何如?”灵公曰:“卿可一自一为。”
二人出朝,一处商议,行父道:“昨日有司奏一犯罪的强盗,秋後处决。吾见其人凶悍异常,若能赦他死罪,再赏他几两银子,他必欣然愿为。”孔甯道:“此人叫甚名字?”仪行父道:“名张黑夜,因独一自一进楼院,杀了看家的家丁,因此犯罪,若用此人,必能成功。”到了次日,孔甯见了灵公说:“有一犯罪强盗,主公赦他的死罪,他必能去杀冶。”灵公沈吟一时,遂写旨一道,递於孔甯。孔甯接旨,出了朝门,到了仪行父家中,将旨递於仪行父,即着人传旨,速提张黑夜至此处听审,不多一时,将张黑夜提到仪行父堂下。行父命左右回避,与孔甯亲解其缚,用手扶起附耳说道:“如此,如此。”到了次日早朝,百官毕上,张黑夜遂伏於半途要之处,专候冶不提。
却说冶朝罢退出朝门,忽然一阵头昏,目跳一肉一战,一自一己也不知何为,有跟随的一个家人,名唤李忠,见主人这等光景,遂问道:“相公是怎的?”治道:“吾亦不知?”李忠道:“莫非家中有事。”李忠遂急扶冶上马。正走之间,忽见一人一自一松林内跑出,一手将冶扯下马来,举刀便砍。李忠看见大声喊道:“你是何人?辄敢行凶?”黑夜看李忠渐渐赶到,即回手一刀,将李忠砍到在地。冶见把李忠杀了,早已魂飞天外,叁舞两弄被黑夜一刀砍倒。割下头来,用布包好,匿於怀中,来见行父。行父大喜,赏银五十两,纵使归家。此时只有孔仪二人知道,外人俱不得知。二人又私奏陈候,陈候亦喜。冶死,国人皆认为陈候所使,不知为孔仪二人之谋。史臣有赞曰:
陈丧明德,君臣宣一婬一;簪缨组服,大廷株林。
壮哉冶,独天直音,身死名高,龙血比心。
一自一冶死後,君臣及无所惮,叁人不时同往株林。一二次还是私偷,以後习以为常,公然不避国人;作株林诗以讽之。诗曰: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
徵舒字是子南,夏人忠厚,不曰夏姬,而曰夏南而来也。陈侯君臣叁人,和局间欢。未知将来如何,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