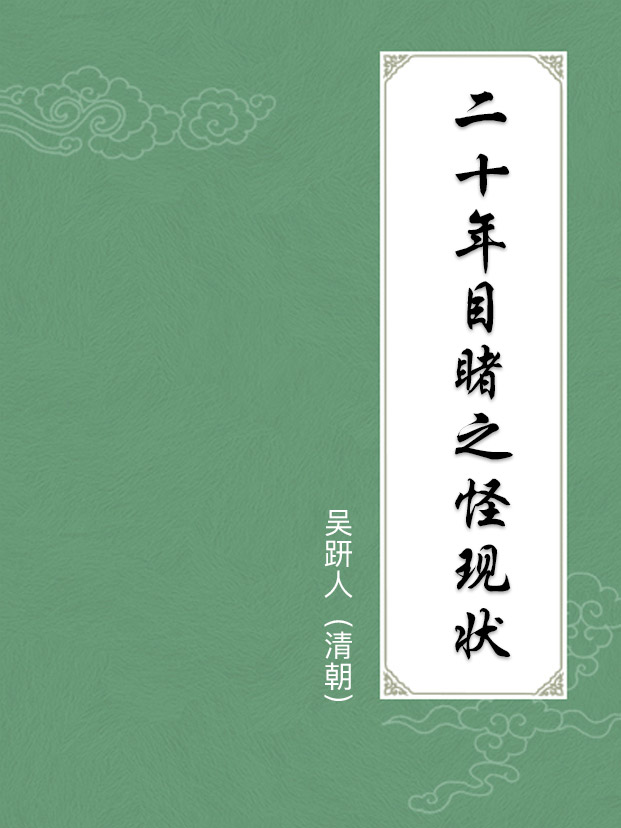第六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却说我听得继之说,可以代我寄信与伯父,不觉大喜。就问:“怎么寄法?又没有住址的。”继之道:“只要用个马封,面上标着‘通州各属沿途探投勘荒委员’,没有个递不到的;再不然,递到通州知州衙门,托他转交也可以使得。”我听了大喜道:“既是那么着,我索性写他两封,分两处寄去,总有一封可到的。”
当下继之因天晚了,便不出城,就在书房里同我谈天。我说起今日到祥珍估镯子价,被那掌柜拉着我,诉说被骗的一节。继之叹道:“人心险诈,行骗乃是常事。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你今日听了那掌柜的话,只知道外面这些情节,还不知内里的事情。就是那掌柜自家,也还在那里做梦,不知是哪一个骗他的呢。”我惊道:“那么说,大哥是知道那个骗子的了,为甚不去告诉了他,等他或者控告,或者自己去追究,岂不是件好事?”继之道:“这里面有两层:一层是我同他虽然认得,但不过是因为常买东西,彼此相熟了,通过姓名,并没有一些交情,我何若代他管这闲事;二层就是告诉了他这个人,也是不能追究的。你道这骗子是谁?”继之说到这里,伸手在桌子上一拍道:“就是这祥珍珠宝店的东家!”我听了这话,吃了一大吓,顿时呆了。歇了半晌,问道:“他自家骗自家,何苦呢?”继之道:“这个人本来是个骗子出身,姓包,名道守。人家因为他骗术精明,把他的名字读别了,叫他做包到手。后来他骗的发了财了,开了这家店。去年年下的时候,他到上海去,买了一张吕宋彩票回来,被他店里的掌柜、伙计们见了,要分他半张;他也答应了,当即裁下半张来。这半张是五条,那掌柜的要了三条;余下两条,是各小伙计们公派了。当下银票交割清楚。过得几天,电报到了,居然叫他中了头彩,自然是大家欢喜。到上海去取了六万块洋钱回来:他占了三万,掌柜的三条是一万八,其余万二,是众伙计分了。当下这包到手,便要那掌柜合些股分在店里,那掌柜不肯。他又叫那些小伙计合股,谁知那些伙计们,一个个都是要搂着洋钱睡觉,看着洋钱吃饭的,没有一个答应。因此他怀了恨了,下了这个毒手。此刻放着那玉佛、花瓶那些东西,还值得三千两。那姓刘的取去了一万九千两,一万九除了三千,还有一万六,他咬定了要店里众人分着赔呢。”
我道:“这个圈套,难为他怎么想得这般周密,叫人家一点儿也看不出来。”继之道:“其实也有一点破绽,不过未曾出事的时候,谁也疑心不到就是了。他店里的后进房子,本是他自己家眷住着的,中了彩票之后,他才搬了出去。多了几个钱,要住舒展些的房子,本来也是人情。但腾出了这后进房子,就应该收拾起来,招呼些外路客帮,或者在那里看贵重货物,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呀,为甚么就要租给别人呢?”我说道:“做生意人,本来是处处打算盘的,租出几个房钱,岂不是好?并且谁料到他约定一个骗子进来呢?我想那姓刘的要走的时候,把东西还了他也罢了。”继之道:“唔,这还了得!还了他东西,到了明天,那下了定的人,就备齐了银子来交易,没有东西给他,不知怎样索诈呢!何况又是出了笔据给他的。这种骗术,直是妖魔鬼怪都逃不出他的网罗呢。”
说到这里,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
吃过晚饭,继之到上房里去,我便写了两封信。恰好封好了,继之也出来了,当下我就将信交给他。他接过了,说明天就加封寄去。我两个人又闲谈起来。
我一心只牵记着那苟观察送客的事,又问起来。继之道:“你这个人好笨!今日吃中饭的时候你问我,我叫你写贾太守的信,这明明是叫你不要问了,你还不会意,要问第二句。其实我那时候未尝不好说,不过那些同桌吃饭的人,虽说是同事,然而都是甚么藩台咧、首府咧、督署幕友咧——这班人荐的,知道他们是甚么路数。这件事虽是人人晓得的,然而我犯不着传出去,说我讲制台的丑话。我同你呢,又不知是甚么缘法,很要好的,随便同你谈句天,也是处处要想——教导呢,我是不敢说;不过处处都想提点你,好等你知道些世情。我到底比你痴长几年,出门比你又早。”
我道:“这是我日夕感激的。”继之道:“若说感激,你感激不了许多呢。你记得么?你读的四书,一大半是我教的。小时候要看闲书,又不敢叫先生晓得,有不懂的地方,都是来问我。我还记得你读《孟子·动心章》:‘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那几句,读了一天不得上口,急的要哭出来了,还是我逐句代你讲解了,你才记得呢。我又不是先生,没有受你的束脩,这便怎样呢?”此时我想起小时候读书,多半是继之教我的。虽说是从先生,然而那先生只知每日教两遍书,记不得只会打,哪里有甚么好教法。若不是继之,我至今还是只字不通呢。此刻他又是这等招呼我,处处提点我。这等人,我今生今世要觅第二个,只怕是难的了!想到这里,心里感激得不知怎样才好,几乎流下泪来。因说道:“这个非但我一个人感激,就是先君、家母,也是感激的了不得的。”此时我把苟观察的事,早已忘了,一心只感激继之,说话之中,声音也咽住了。
继之看见忙道:“兄弟且莫说这些话,你听苟观察的故事罢。那苟观察单名一个才字,人家都叫他狗才——”我听到这里,不禁扑嗤一声,笑将出来。继之接着道:“那苟才前两年上了一个条陈给制台,是讲理财的政法。这个条陈与藩台很有碍的,叫藩台知道了,很过不去,因在制台跟前,很很的说了他些坏话,就此黑了。后来那藩台升任去了,换了此刻这位藩台,因为他上过那个条陈,也不肯招呼他,因此接连两三年没有差使,穷的吃尽当光了。”
我说道:“这句话,只怕大哥说错了。我今天日里看见他送客的时候,莫说穿的是崭新衣服,底下人也四五个,哪里至于吃尽当光。吃尽当光,只怕不能够这么样了。”继之笑道:“兄弟,你处世日子浅,哪里知道得许多。那旗人是最会摆架子的,任是穷到怎么样,还是要摆着穷架子。有一个笑话,还是我用的底下人告诉我的,我告诉了这个笑话给你听,你就知道了。这底下人我此刻还用着呢,就是那个高升。这高升是京城里的人,我那年进京会试的时候,就用了他。他有一天对我说一件事:说是从前未投着主人的时候,天天早起,到茶馆里去泡一碗茶,坐过半天。京城里小茶馆泡茶,只要两个京钱,合着外省的四文。要是自己带了茶叶去呢,只要一个京钱就够了。有一天,高升到了茶馆里,看见一个旗人进来泡茶,却是自己带的茶叶,打开了纸包,把茶叶尽情放在碗里。那堂上的人道:‘茶叶怕少了罢?’那旗人哼了一声道:‘你哪里懂得!我这个是大西洋红毛法兰西来的上好龙井茶,只要这么三四片就够了。要是多泡了几片,要闹到成年不想喝茶呢。’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了。高升听了,以为奇怪,走过去看看,他那茶碗里间,飘着三四片茶叶,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那一碗泡茶的水,莫说没有红色,连黄也不曾黄一黄,竟是一碗白冷冷的开水。高升心中,已是暗暗好笑。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掏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象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甚么字。原来他那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的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舐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叫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看他写了半天字,桌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象想甚么似的。想了一会,忽然又象醒悟过来似的,把桌子狠狠的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甚么呢?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他不到嘴里,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
我听了这话,不觉笑了。说道:“这个只怕是有心形容他罢,哪里有这等事!”继之道:“形容不形容,我可不知道,只是还有下文呢。他烧饼吃完了,字也写完了,又坐了半天,还不肯去。天已向午了,忽然一个小孩子走进来,对着他道:‘爸爸快回去罢,妈要起来了。’那旗人道:‘妈要起来就起来,要我回去做甚么?’那孩子道:‘爸爸穿了妈的裤子出来,妈在那里急着没有裤子穿呢。’那旗人喝道:‘胡说!妈的裤子,不在皮箱子里吗?’说着,丢了一个眼色,要使那孩子快去的光景。那孩子不会意,还在那里说道:‘爸爸只怕忘了,皮箱子早就卖了,那条裤子,是前天当了买米的。妈还叫我说:屋里的米只剩了一把,喂鸡儿也喂不饱的了,叫爸爸快去买半升米来,才够做中饭呢。’那旗人大喝一声道:‘滚你的罢!这里又没有谁给我借钱,要你来装这些穷话做甚么!’那孩子吓的垂下了手,答应了几个‘是’字,倒退了几步,方才出去。那旗人还自言自语道:‘可恨那些人,天天来给我借钱,我哪里有许多钱应酬他,只得装着穷,说两句穷话。这些孩子们听惯了,不管有人没人,开口就说穷话;其实在这茶馆里,哪里用得着呢。老实说,咱们吃的是皇上家的粮,哪里就穷到这个份儿呢。’说着,立起来要走。那堂上的人,向他要钱。他笑道:‘我叫这孩子气昏了,开水钱也忘了开发。’说罢,伸手在腰里乱掏,掏了半天,连半根钱毛也掏不出来。嘴里说:‘欠着你的,明日还你罢。’那个堂上不肯。争奈他身边认真的半文都没有,任凭你扭着他,他只说明日送来,等一会送来;又说那堂上的人不生眼睛,‘你大爷可是欠人家钱的么?’那堂上说:‘我只要你一个钱开水钱,不管你甚么大爷二爷。你还了一文钱,就认你是好汉;还不出一文钱,任凭你是大爷二爷,也得要留下个东西来做抵押。你要知道我不能为了一文钱,到你府上去收帐。’那旗人急了,只得在身边掏出一块手帕来抵押。那堂上抖开来一看,是一块方方的蓝洋布,上头龌龊的了不得,看上去大约有半年没有下水洗过的了。因冷笑道:‘也罢,你不来取,好歹可以留着擦桌子。’那旗人方得脱身去了。你说这不是旗人摆架子的凭据么?”我听了这一番言语,笑说道:“大哥,你不要只管形容旗人了,告诉了我狗才那桩事罢。”继之不慌不忙说将出来。
正是:尽多怪状供谈笑,尚有奇闻说出来。要知继之说出甚么情节来,且待下回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