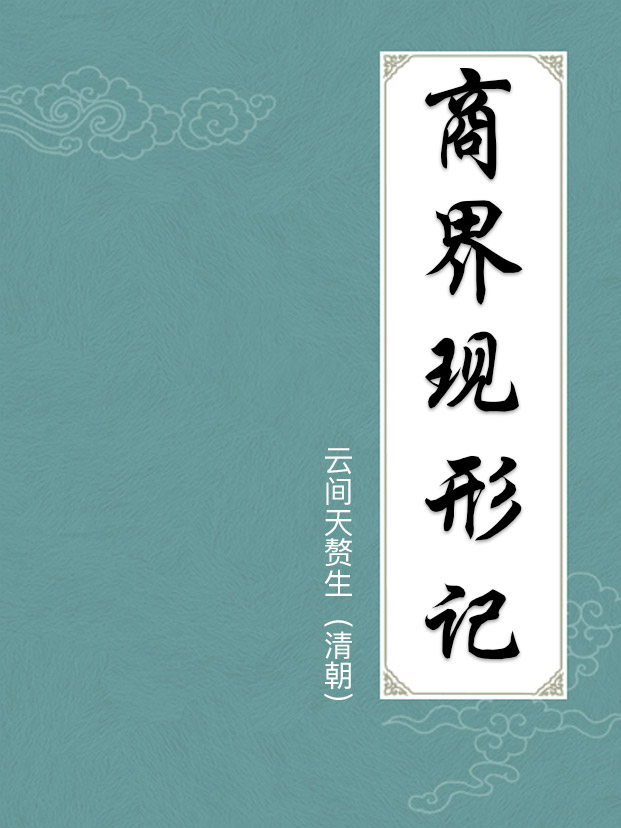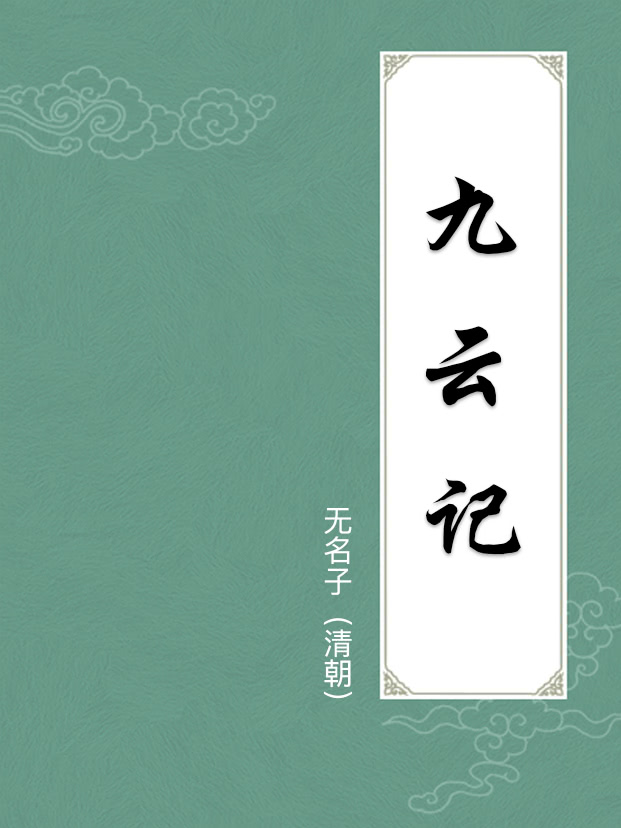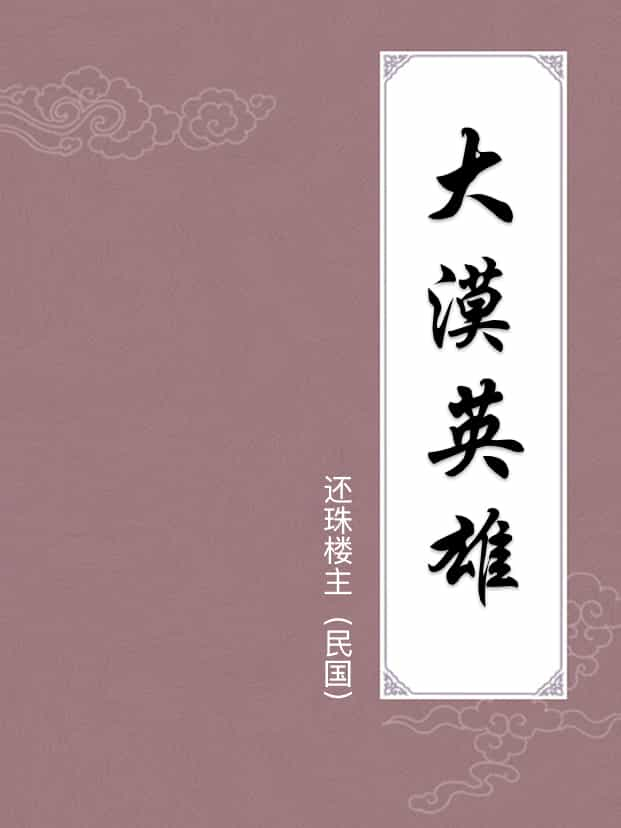话说上文所说的那个五爷,原来不是别人,却是主使乔养仁,倒掉官商二百三十多万银子的那个陈老五。那陈老五当初他老子手里,却在商界上有些小名声,有万把银子的家私,十几年前已死了。这五爷却装出富贵公子的模样,不屑做商界中人,偏偏自命为学界巨子。其实不过认得几个字罢哩。于是明知旧学界上挨不进,还是新学界上去混混,便想须得出洋才能骗人。他恰好堂子里搭上了一个大姐,租了一所小房子,何奈老婆凶得了不得,吃他想出这计较来了,假说东洋留学去,岂知把铺陈行李搬到了小房子里去。一住三个月,足不出户。那大姐也不要他了,他钱也用完了。便回到家里,扬言学的是地理速成科,如今卒业了。明白的呢,心里暗笑;不明白的,直当他是舆地大家。听他讲章起来,却是浑浑有味。
俄露斯的什么山几多高、英吉利的河几多长、什么海通到什么地方。大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自然没对证。岂知他心计果然聪明,科学之中唯有地理最容易骗人。说起来横竖在外国。决不致于有个笨人,听他说了美利竖有座几多围圆、几多高大的什么淡苗火路山。这个笨人备了资本,跑到美国去,寻这座淡苗火路山,丈量丈量,看对也不对。听他了土耳其有条什么港,也决不致于有人跑到土耳其去,看看这条巷的。并且到底这山、这港,地球上有也没有,也不得而知。于是就有许多人和他做朋友,请教他地理的学问,一会儿说捐了官了,捐的五品官,分发湖南〈(五品官奇称)〉种种奇怪,不可尽说。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些小家财不经他挥霍,忽又想出一条计策来。同那乔养仁本有些交情,不过往来却多年没有了,假意儿的要好起来,就此银钱进出。一日弄到了乔养仁出的银票一纸,去和一个刻字的商量,照此样式刻起来,那刻字一看,只有两个本印,一个是年庚,一个是养记两字。
便道:“的包管你一些不走。”
五爷欢喜道:“我情愿给你十块洋钱,千万不可走漏风声。”
那刻字的道:“刻工一个钱不要,我刻好了,放在我这里,你不可拿去。你如若做一百两假票,你拿五十两银子来给我,我便拿木印出来印一张。总而言之,做的银子大家一半,哪怕几百万我也要一半,而且我却要现银子的。假票子用不来的,万一弄穿了下来,岂不是害了你。”
那陈老五道:“如此你忒便宜了,我担了干系去做,你却安安稳稳用大注儿的钱。”
刻字的冷笑道:“把柄在我手里,自然要便宜的。若不答应,我便乔养仁跟前出首去。”
陈老五道:“阿也。”
没奈何,只得依了这刻字的。
陈老五原有一所房屋,抵押一千五百两银子,在一个姓福的福大人那里的,过期了好几个月,福大人催他赎去,催了三五次,只是不赎。福大人恼了,说:限你三日再不把本利送来,写信到衙门去。把房屋拍卖了,不够数还得吃官司哩。我们官场敢是肯吃亏一个钱的吗?陈老五一想懊恼,把房屋押给福某人。他是道台,并且有差事的,于是慌了。连忙找那刻字连夜刻起来,写了一张一千九百三十五两的票子。
刻字的道:“刻字容易,你须得端整九百六十七两五钱银子来。”
陈老五道:“我因为没钱了,所以做这事情呀!第一票生意,哪里来现银呢?”
刻字的一想:“不错,你有多少现钱给我,馀外写欠据。”
老五想了想道:“现钱不过几十元是有的。”
那刻字的又道:“这样罢,你印了去,我跟着你收到银子,大家分用就是了。”
老五道:“这银子是要福大人那里去赎押款的,合准的数儿呢。”
刻字的道:“明明你骗我,如此说来,你不是自己用的。”
陈老五顿然省悟道:“我真昏了,吃福老头子催昏了。”
连忙又写了二千两银子的票子。刻字的道:“横竖不怕你溜了,你若溜了我的钱,我这里马上出首,那怕你溜到外国,也要兜了你回来才是。”
陈老五赌神罚咒的不拔短梯,将来几千万家私都在这里。〈(做梦)〉
于是拿了票子一想,拿假的给福老头子有点不敢,〈(做贼人心虚)〉
去托一个有钱的朋友调了一张真的,不知那一家的银票,岂知老大一个破绽。帐房先生一看,果然真的。但是一千九百三十五两的数目,似乎记不起了。不知谁来打去的,于是瞧那票子的号码是:
第五一七三九六号
便把那一本五的根簿翻来一看:
五一七三九六
银二百三十六两二钱七分六釐
付艮记
那帐房先生一看,眼睛都定了,重又一个一个字对读了两遍,并无错误。正在纳罕,又交进一张来:
第五一七三九七号
九八规银二千两正。
咦?却是联号,瞧那根上,却又大差其远了,却是:
五一七三九七
银一百一十一两一钱一分一厘
付艮记
那帐房先生直跳起来,要把来收银人送到衙门去。跑出一看,却是同行中彼此熟识,便把原委说明,银子未便付得,不信拿根簿出来看。
这时际东家乔养仁也知道了,便道此事决非同行中做的。终竟有个来源的,于是不消一会工夫,一路一路的追根追去,那一千九百三十五两的是陈老五付来,一回儿那二千两的也是陈老五所付。
乔养仁舌头一伸道:“咳,陈老五我同他是父辈之交,并且他又是湖南的官,东洋留学地理的学生,极有学问。我今年七十三岁了,儿子也没有,落得做做好事。”
于是三千九百三十五两银子,叫帐房先生照付,便叫人去请了陈老五来。
陈老五还不曾得知,连忙跑来,乔养仁同了陈老五到一间密室里说道:“老世侄,你如何做得这种事体,须知一辈子不好做人的呢?”
说著把两张票子向陈老五面上一撒道:“你看,你看。”
陈老五大惊失色,强辩道:“小侄也有来源的。”
养仁道:“不用强辩。银子我已照付了,共总四千不满的数儿。一来你老的份上;二来你也是名士。〈(名士?笑话、笑话,吾为名士一哭。)〉不过嗣后是不许做了。你把木印交出来销毁了,人不知鬼不觉,依旧做你的好人。”
陈老五大为感激,连连答应,连忙去找刻字的要木印。
那刻字的道:“不兴。”
老五道:“事体穿了,好容易说得私和,销毁了木印便了结。限三个钟头的,若是不去销毁,马上送官究办,可知吃不住哩。”
刻字的冷笑道:“受罪有你,干我屁事。空手好来拿吗?”〈(须知雕刻伪章同科呢)〉
陈老五急了。“要多少呢?”
刻字的大声道:“二十万现银子。”
陈老五急得哭了。后来倾其所有一切金银首饰等顶,也值四六百银子呢。终算了结了这件事。于是感激那乔养仁不尽,情愿做他的儿子。天天跑去孝敬养仁,因为一时义气,保全了老五名声,哪里要这个下流东西做儿子呢?
过了几时,养仁已死,便由子侄辈前来承受。老五又把养仁的子侄,叫做一官的拍上了,知己得亲人一般。因此便有倒欠官亲商二百多万的一节。被上司访明情由,罪魁祸首却不是乔一官,是陈老五。所以捉了来,差人还看管着。陈家老栈弄几个钱来使,使得够了再解进衙门去。可知差人权柄真不小呢。所以朱润江、金子和要老枪抽烟,三三儿说被五爷借去了,就是这缘故。
且说差人海狗唇老大调处了一回,润江一定不肯,子和也说情愿见见官,不情愿私和。老大只得趁著随大老爷不曾退堂,把朱金二人解上堂来,照例先叫原告朱润江来问,润江便呈上禀词写著
具禀职员朱润江,本地人,年二十八岁。
为串骗银钱,屡索不理事。窃职员曾于美洲法政学校肄业八年,卒业回来,在北省齐中丞幕办事五年,历保知州,分发西省当差八年,署缺二次。一官羁身,未曾回里。旋于五年前看破红尘〈(奇语。该去做和尚,不该回来。一笑)〉告假回籍,乃知职妻言氏出银九百两,被拐棍金子和拐去开设栈房,在东兴路。栈店第一旅馆。职便亲到东兴路查看,并无第一旅馆牌号。明知受骗,即寻金子和理说,拐棍金子和始则一味支吾,后来被逼不过,始显拐骗情形,并未闻设第一旅馆,所有九百银两,早已花用无遗。职系在官人员不欲声张,责令还银九百了事,讵延宕至今。已有五年之久,从未还过分文。为此情急伏求公祖大人严究拐榻金子和,从重治罪、以安善良、而保血本、实为德便。
沾
仁上禀
随大令看罢禀词,笑了一笑道:“朱润江,你今年几岁?”
润江忙打一躬道:“职员年二十八岁。”
随大令道:“少年英俊,这点年纪已做了这么样的大事业。可敬,可敬。”
润江又一躬道:“后生小子樗栎庸材,不敢当公祖谬赞。”
随大令自言自语道:“留学八年,作幕五年,八五一十三年。当差八年,已是二十一年了。回来了五六年,已是二十六、七了,光景只得一岁就出洋留学了。”
便又笑道:“你几岁出洋留学?”
朱润江打官司,打了好多回,并不曾提问过这句话。
便道:“职员二十一岁出洋的。”
随大令道:“如此,你写错了,今年该是四十八岁哩。”
润江这一惊惊的呆了,好容易挣出一句道:“职……职……职……职员实……实……实在这几岁。”〈(倒是妙语双关)〉
随大令喝道:“跪下。”
朱润江只得跪了。随大令道:“且问你假冒绅衿是何缘故?可知罪吗?”
润江道:“知罪。”
随大令“哼”了一声道:“可知所告也是虚的了。”
润江道:“这却是真的。”
随大令便叫带金子和,金子和连忙跪下。随大令便把一双近视眼用力看去,仿佛极美的一个。
猛叫一声道:“来!”
贴身大爷金印答应道:“者者。”
随大令道:“拿眼镜来。”
金印又答应了一阵:“者者。”
连忙飞奔进去。
要知眼镜拿得来否,且听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