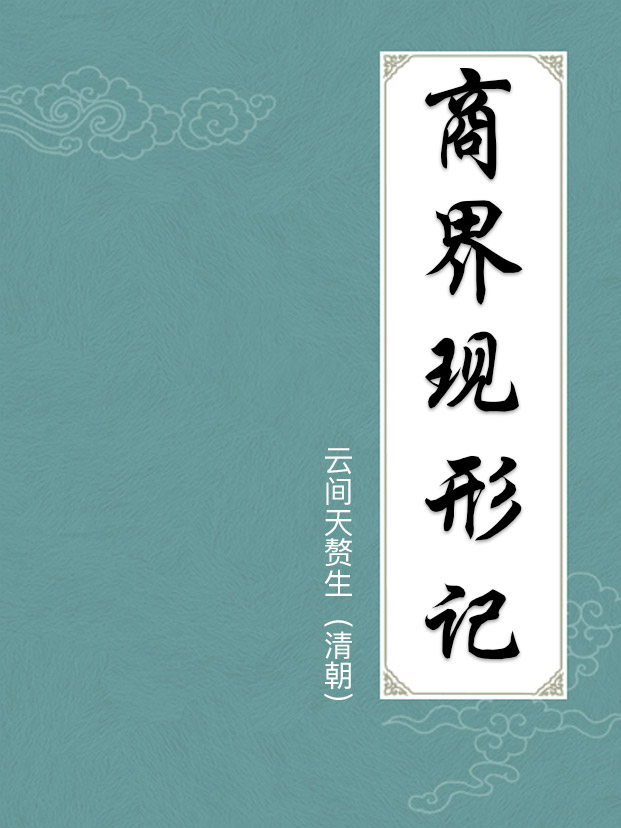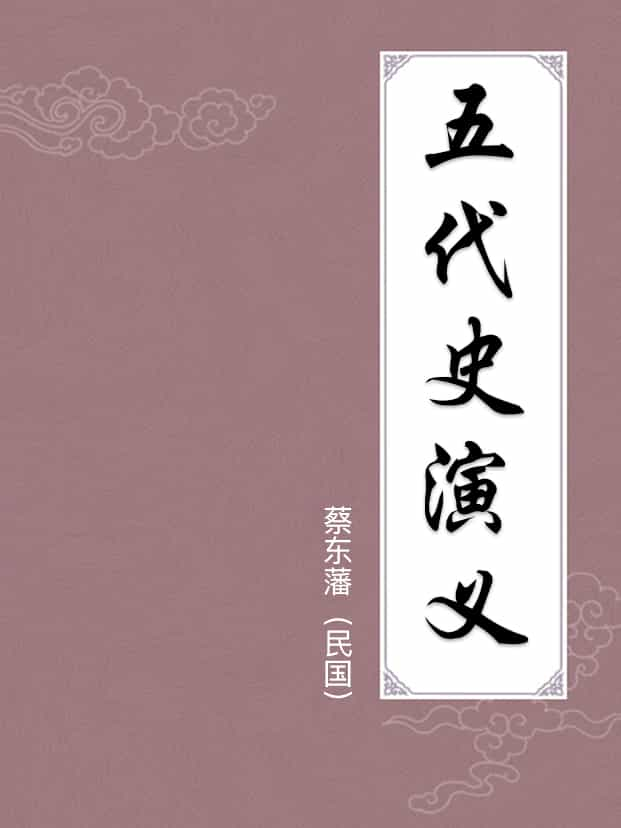却说周子言周三,别过了崇茂钱庄的第一天接手的挡手杜筱岑,心里一百二十分的高兴,想道:气运红起来,只这样的顺溜。原想在陈少鹤身上哄个千儿八百的一票,够了端午节的开支,也心满意足了。到底还虑著方老头儿从中作梗,少鹤也操不得全权。岂知老天方便,先给我调排开了,接续的又是这个杜筱岑。当日在花想容台面上,凡他很像一个人,一脸的精明样子。岂如今儿一看,也不是个上流东西---创业不足、破产有馀的一个人。
是和陈少鹤朋同类也,“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一点不差。如今既是我要交大运了,少不得要改个样子。老底子那几处玩惯的门户,屏而不用。想到这儿,向身上一摸,摸出个皮夹子来,就在电灯底下打开来看,里头却有五元的钞票一张。三个英洋、二十来个角子。
自言自语道:“大约有十元之谱。绰手有馀的了。
仁寿里可在眼前,“绮云阁烟馆”
里的老二,我心心念念,要去住它一回,看他两腿儿肥的什么似的,叫人看了怎的不动火呢!曾经去过抽过三、五趟阿片,探探住夜的价值,至不可少要“梅花”之数。还须加上小帐:两只烟钱,半夜点心、水果、小吃等项。少不了又是两只大洋。算算七、八块洋钱玩一趟,委实舍不得。曾经和他商量,做两不吃亏的方法---花两只洋关房门。他说不是野鸡,做不到。好人家女儿,小老班娘娘认起真来,两记“绍兴大耳脖子”。〈(寄文不知所指。)〉
今儿既有这几块在身上,落得阔一阔。明儿就面团团了。主意决定,便弯进了仁寿里“绮云阁”老二那里去,开了个过夜灯,抽了一夜。须知这回所抽的,并不是阿片。〈(妙不可言)〉
次日十二点钟才得出来。
身上只有一块英洋,七、八个角子,便坐把车子来到宝善街“怠园烟馆”〈(“怠”字妙极,具有深意)〉
老主顾巧生堂里开了个灯,巧生代烧着烟道:“周先生,今儿怎地这么早?看来神气不清,很乏的样子。敢是在相好那里快活哩?”
周三伸了个欠,笑而不言。
接着抽了两口阿片,便笑说道:“有趣,有趣!‘绮云阁’里的小老班娘娘着手了!”
巧生“嗤”的一笑道:“哪一个嗄?老二呢,还是老三?”
周三道:“自然是老二了!老三是丑来,倒贴我钱,还不高兴哩。”
巧生又“嗤”的一笑。
周三道:“笑什么?”
巧生道:“小老班娘娘,谁和你说来?既是小老班娘娘,时小老班呢?”
周三道:“小老班倒很得意。据说现在青海电报局里,要赚到一百两银子一月哩。”
巧生大笑道:“鬼也鬼也!……”
周三忙问缘故。巧生道:“日后自知。---光景没吃饭哩,去叫饭罢。”
周三道:“也好。就对过‘得和馆’去叫一个生妙鸡片、虾球、腰片汤。三样够了吗?”
巧生笑道:“唷?周先生阔哉!不然,是老花样---不是一碗清血汤,便是一客木樨饭。要不了一角洋钱的。”
周三笑道:“别乱说!你须知道我三老班发了财了!”
巧生笑着去叫了饭菜。吃罢,又添两盒阿片,消磨了一会儿。
已三点钟了,只见那些掮客,陆陆续续到来,头里都不开谈买卖,尽著抽烟。只抽得烟雾腾天,云霞匝地。差不多又是两个钟时间,那班掮客一个个蠕蠕作动,欠身而起,〈(精妙入神,吴道子无此神笔。)〉开谈起生意经来。周三瞧著一个叫做王二夫的招招手,二夫促过来道:“子翁有何见谕?”
周三道:“墨其〈(同行暗号)〉长〈(长,便是涨也。)〉足了吗?”
二夫道:“长的十足,不过三天的市面,就要回了。〈(回,便是跌价也。)〉这一回,回下去,不知要回到什么地步哩。所以这两天市面都没了。大家观著,晓得就在眼前大宗到来,立刻要回到顶底度数。固此手里有货的,要想出脱抢个鲜。只是没有胃口〈(胃口,即买进也。)〉子翁若有时小胃口,兄弟还可以应酬。不过三、五十件罢了。”
周三笑道:“你手里有多少?”
二夫皱着眉道:“说不得。这两天我肠子都愁断了,手里有八千件哩。”
周三道:“我通买。有时我还要。---八万件也不嫌多。”
二夫愕然道:“子翁说玩话?”
周三正色道:“我何曾玩过来?银子是现的。拿货单来,立刻拿银子去。”
二夫惊疑不已,含糊著和别个商量道:“可知墨其有什么信息吗?看长有吗?”
一个道:“没有长的道理。”
又一个道:“我有计较在这儿,---周三要买,无非看长。索性加上两三个长头,打伙儿一起去唬他一唬,看他怎样?”
二夫道:“我做了十多年的生意了。细细想来,断无长的道理。---看他神气,极似大长而特长的样子。倒决断不来哩。”
一个道:“坎坎你说急的要上吊,这会儿子有了这好机会,有甚商量?卖了就完了,赚了一票,也算济运大好的了。又要痴心妄想到长的念头上去了。”
二夫一想,果然不错。便自顾去和周三交易了。
那一个问那一个道:“怎地你也劝二夫卖去?倘使真的长起来,岂不是对不住他呢?”
一个道:“你忒煞女人腔了!他今儿通卖了,也着实掘了一票哩。他手里有七、八千呢,头二万弄进了,等他真的卖掉了,足见有稳长的消息。我们手里虽没有二夫这么多,大可以放心,不到合资钱不卖。落得叫他给我们做一粒定心丸。他嫌多嫌少,干我们什么?”〈(算你晦气)〉又一个着实佩服。这且搁过一边。
且说王二夫听了那一个的议论,着实不差。转念道:“他既劝我卖掉时,他手里又不过一、二百件,何不托我并卖了?只怕果有长的梦想。〈(真是梦想,梦想!并非“妄”字之讹)〉
点了点头,便对周三道:“那几个朋友手里真……真一件也没了。我手里的,也不能一起卖脱。子翁面上,让三千件吧。不过价钱不能依现市的。”〈(二夫亦殊精炼的,是此辈人口吻,作者何处学来?)〉
周三笑道:“简直些儿吧。我也不是糊涂虫。〈(妙语如珠。)〉
你有多少?通拿来。要甚价钱?尽管儿说。不过有一句话要和你说明白,烦劳你对众朋友知照一声,今儿是四月二十三,〈(忽点出日子,奇极!有了日子,便好查对,足见无一事没来历者。即如“怠园”明眼人一望而知,不过一个心横了下去。)〉
二十五的四钟为限。在期限之内,有多少?要多少。价钱不论。只消说得出。要十两银子一件;二十两银子一件,说得出口,我就拿出银子。限一点钟之内,即期汇划到庄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说著倒转身,抽阿片烟了。〈(活现活现)〉
那王二夫倒找不到是何秘诀。〈(我也不懂。何况你们)〉
心上忐忑不定。摸拟了一会儿,道:“四两银子一件,你要时八千件一起买去。”
周三道:“拿单子来看!”
二夫便取出栈单,共有十来张。一一看了数目,合拢来一点,不错!恰正八千件。
便道:“我去出票子。”说著匆匆而去。
那许多墨其掮客,并自己做点小货的,不止十几个。瞧著周三看过栈单匆匆而去。都一蜂上来,围住了王二夫,七张八嘴的问道:“多少数目?”
王二夫说了。便把限期一层也宣布了。〈(或谓二夫是忠厚人,我谓二夫是乖觉人)〉大家也以谓诧异,议论纷纷,莫衰一是。内中一个姓牛的,忽然省得〈(省得的不姓牛姓了,牛省得什么?一笑。)〉
道:“没有道理的。周三光景合上了一个大资本家?想做一个海底枪笆的事业?”
大家咸以为然。〈(一群牛)〉二夫沉吟了一会儿道:“未必是的。大凡做海底枪笆的人,一定特别的识见,非常的手段。若是现在九月间,或是来源还远?……我便猜定了。你们想呢,现在是四月,来源就在目前,而且这宗来货比寻常要多三、四倍。那里做得到呢。”
众人想想,却又不错。这事其实作怪,现在一顿买去八千件,银子三万二千是真的。只见对面炕上一个人在那里冷笑。二夫一看,不是同行朋友,却是“上海日报馆”改本地新闻的金先生。便道:“金先生是聪明人。做到主笔的,必定有特别的见识。倒详详这市面看。”
金先生笑道:“‘古吉鲁轮’触礁的。电报,不是今天各报都有的?”
二夫道:“那是知道的。但是‘古吉鲁’并不是专运墨其的,不过带装着一千多件,与市面上九牛一毛,毫不干涉。”
金先生又冷笑一声道:“你知道周三是甚等样人嗄?”
众人一想,恍然大悟,于是打伙儿应有尽有,只等周三到,一起卖给他。
恰正周三已到,拿出崇茂庄即期票五七张,合成三万二千两之数,交易已定。众人公举王二夫做代表和周三交易。周三心里已想过:这事情做得拙了。在少鹤终算丢了三万多银子,然而究竟不是一文不值的,哪怕折到天尽头去,两万银子到底收得回来。不过一万多点银子---,他也不要紧,我就不过摸了二千还不到的银子,就做断了这条路,不大合算。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便道:“一古脑儿,究竟还有多少?”
二夫道:“尽在于此四千七百件。这点点通市面十有八九了。”
周三点了点头道:“怎地这般少?上海市面端的不兴了。我想至不可少终有三万件,才可以销差,如今一半都不到,怎好呢?”
二夫听他自言自语,又是到死也懂不来的事。只见他又道:“我拜托你通市面,收一收看。有大票儿的,最好,省得一趟一趟的零碎做。今儿什么时候了?打票子是来不及了。明儿一起算罢。不过这四千七百件,明儿短了一件,我不答应的!”
又三十六张货单,腾来倒去,翻了一阵,交给二夫道:“你去敲敲着实,不要到明儿多一句话。”
二夫沉吟了一会儿,悄悄的对周三说道:“你肯加五钱银子二件,通在我身上,包管四千七百件,一件不短。”
周三大为欢喜,一口应承。二夫便去和众人只说老价钱,银子明儿付清,货单存在我处。如若不信,就把我的银子算给你们。为因周老三忒利害,倘使明儿短了一件,要罚我一千银子呢。众人都道:“笑话了。我们还信不过你王二翁吗?”
说罢一蜂都散了。二夫也着实欢喜---不道又是二千几百两银子外快。便回复周三道:“敲着实了。一定明儿。向我一人说话就是了。”
周三道:“你须叫个人出来保一保,〈(奇)〉若是短了一件,怎样说话?我和你说一句知己话:你们都在梦里,包不住明儿还有比我更大的胃口,更肯出重价的人出来呢?所以我的心都急碎了。你们做做买卖,巴不得多赚一个是一个。我终不放心,只怕明儿等得我到来,四百七十件都没了。并且我打不得早起,到得又迟。”
王二夫吃周三说得六神无主,便道:“货单你先拿去,终好了。”
周三笑道:“无此情理。别和我说出外教话来。”
二夫又道:“那末一张万三千的存在你做保证,就是了。”
周三道:“也好。待我写张收条给你。”
二夫道:“你出了收条,明明要我证据了。”
周三笑道:“随你大才的便。”
二夫道:“我也彼此信得过你。也不用出收条,我也不写证据了。”
说罢,把三千张的那张庄票向烟盘里一放,拱手自去。
周三便收好了,慌忙来到“海南春大菜馆”,寻到六号房间,只见杜筱岑一个儿拿着一本洋版小本子出神的瞧著。
周三忙招呼道:“筱翁,只怕等的不耐烦哩?”
筱岑忙放了那本书,笑道:“还好,还好。也来的不久。”
周三瞧那本书,原是一本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江南乡试闱墨》。〈(好笑)〉
便道:“筱翁,真是实心办事,一无假借的了。若是现今我们中国的大小官员,农、工、商、学界诸多人,也像筱翁这么实心实力,志在必成的办起来,还怕不振兴吗?”
筱岑道:“不瞒三阿哥说,我也不过在这么样的事务,自己信得过自己,不作兴放一点儿松。---若说除了这么样的事务呢,唯有抽大烟是认真不过的。譬如约朋友,约烟馆里,或是哪里有大烟奉客的,只作兴比约著的时间早两个钟头已到了。不作兴迟了一分钟方才到来。若是丢过了‘烟花’两字,约个去处,譬如原约的礼拜日一点钟,最快礼拜二的一点钟到来。还算着实不脱约。倘使懒待些儿,去年约的,今儿还没曾赴约哩。”〈(形容绝倒,虽无其事,却有是意。目下烟禁,虽不甚力,尚不曾罢休。然而烟禁的结果是否完全,吾不敢说。)〉
周三笑道:“那是言之过甚哩。”
闲话休题,且把请客票来写。筱岑道:“我想索性去请田家姊妹花来,你看好吗?”
周三瞧了一瞧时计道:“七点还欠五分,不过跳加官罢哩。她们俩个顶早要十点后上台哩。去请请看,作兴月峰倒肯来的。我代你写。”
筱岑忙道:“使不得!须得我自己写,笔气不落俗套。可知生意人的字和念书人的字截然不同,显而易见的很。我并非乱道,别的假充斯文,原来全本滑头。唯有几个书法,休说借一名举人做门面,倒委曲了。其实鼎甲都有意思,我的笔姿纯乎‘天公先生’的一路。我写字落了‘天公先生’的名款。好叫‘天公先生’自己也认不真。”
周三连忙把笔放下。筱岑便磨得墨浓、蘸得笔饱,一挥而就。写的是:
飞请
小峰月峰两位艺员速驾福州路中市、海南春西餐馆第六号请赏异味,藉聆。
雅教,谨此仰攀,伏祈。
俯就,万勿推却,不胜雀跃之至,专诚敬叩玉安。企候
宠临。是幸。
职生杜寂啸岑氏顿首
周三先生在座
周三瞧著筱岑一路写,一路没口儿的喝采道:“噎!好吗!银钩铁画。硬---硬硬---硬得不得了!噎,噎噎噎……好吗?笔走龙蛇飞舞得很,苍古得很。噎,噎噎,噎噎噎!”
筱岑写罢,掷笔狂笑道:“如何?……岂是代得笔的吗?”
周三又道:“噎!不得了!写得出神入化,而且句语也不比寻常。好个‘仰攀’,好个‘俯就’。”
筱岑长叹一声道:“冤哉,枉也!好处何尝在‘仰攀’‘俯就’之间哉?所以之最神是在‘雀跃’者也。而‘雀跃’一联,最得乎神者也!”〈(妙妙!如何形容出来。)〉反复读了两三遍,摇头摆尾,奇形怪状,实在描写不来。也是没法儿想的事。
周三瞧了一会儿,又道:“这‘职生’两字作什么解?敢是职员的意思吗?”
筱岑含着一脸的喜容,把身子东歪西扯了一阵,耸肩拥鼻的道:〈(说实在,描写不来,真真客气了。读来已觉有一个活现的杜筱岑在字里行间,“摇摆”两字,化作“东歪西扯”了一会儿,绝妙!)〉
“然而非也。〈(“然而”两字,其实用不着。恰恰假斯文口吻)〉职生者,举人之谓也。”
周三忙道:“承教,承教---。这么著交代细崽请去,别延待了。”
于是把叫人钟一按,便“唧灵灵……”的走响。细崽应声而至。
周三昂然道:“快去请来。”
细崽忙接了请客票一看道:“老班,小峰、月峰现在十九号里三层楼上。”
筱岑忙道:“单是姊妹俩吗?”
细崽道:“不只呢,大约十三、五个哩。”
筱岑道:“多是女客吗?”
细崽道:“男的多些。光景是京里出来的官场中人。”
筱岑没了主意。是请的好,还是不请的好?瞪瞪的瞧著周三。
周三道:“自然去请的。虽则她们不是婊子。然而终竟是唱戏的。和婊子却是朋同类也。怎好说是好人家的女孩儿?大人家的千金小姐?并且现儿上海,似乎不大作兴。京城里是名分应条子的。就是从前譬如谢家班、林家班、鲍家班、张家班……,哪一个不出局的吗?”
筱岑道:“终竟三阿哥熟悉‘花丛掌故’。”
正说得高兴,忽见一个人探了一探头,直冲进来。筱岑忙道:“咦!梅生,巧极哉!”
梅生道:“这里来谈一句。”
便看到阳台上嘁嘁喳喳了两三句,只扣得筱岑大有慌张之状。
道:“……真吗?”梅生道:“我是在那边来呀!”筱岑一跺脚道:“死的成哩!”
不知是何急事,且听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