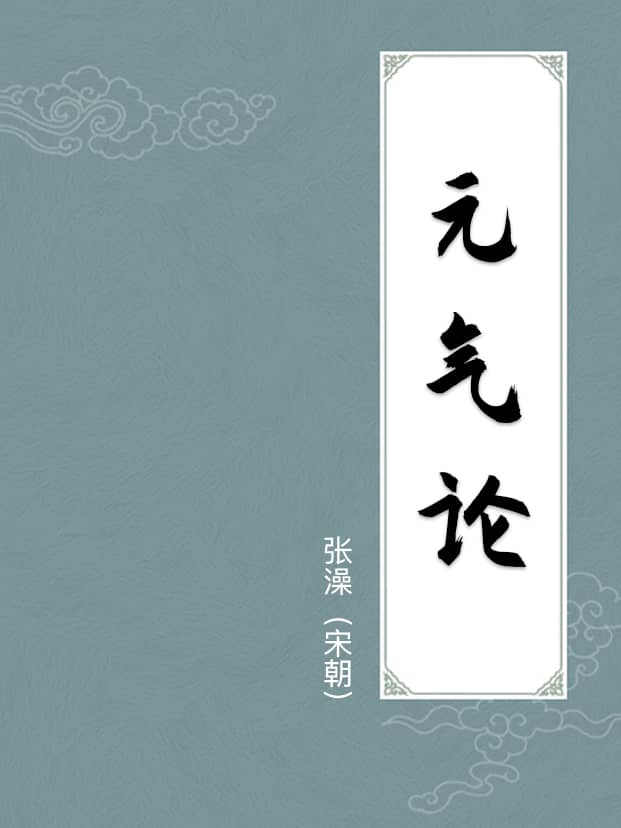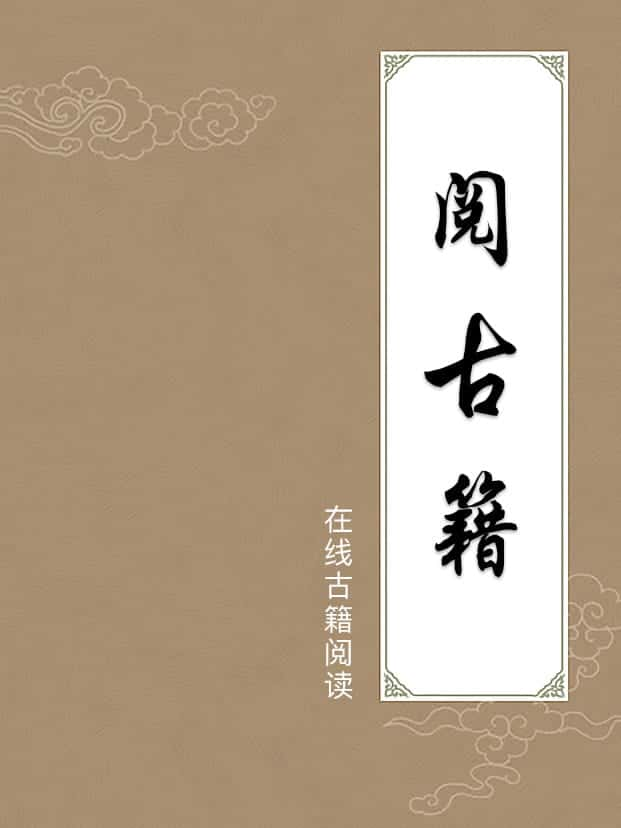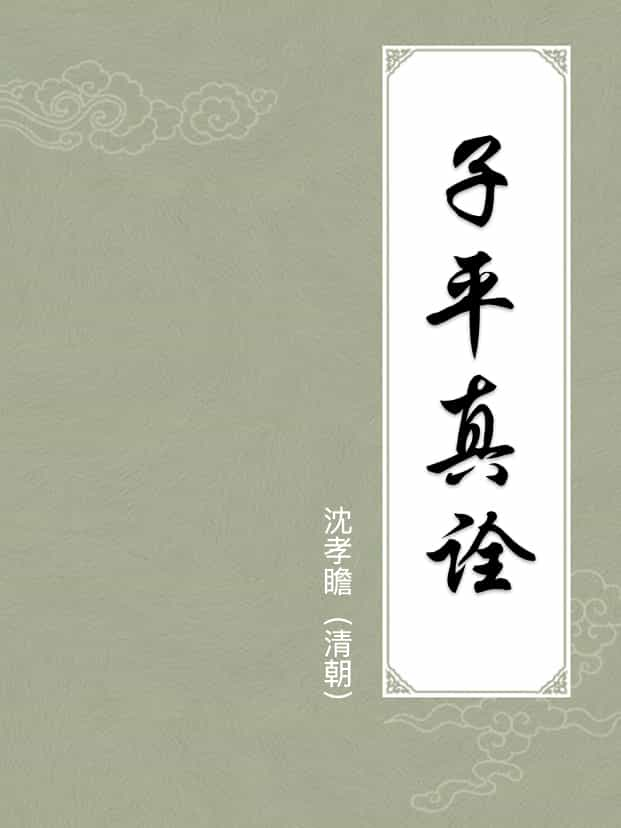且说杨小姐自杨梅窗死后,结识了一班女朋友,天天的到马路上,去兜着圈子,不是看戏,就是坐马车,倚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好借此出出风头。不想有一班马路上的流氓,看中了她,便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子,去引诱她。杨小姐一个十八九岁的女人,那里晓得什么世路的艰难,人情的险恶,况且又不比欧洲各国的女人,受过上等的教育,只觉得这几个流氓,在自己身上甚是尽心,二十四分的要好,她便也不知不觉的,和他们亲热起来,渐渐的上了他们的当,被他们拖下水去。那内里的事情,是不问可知的了。这位杨小姐,得了杨梅窗的遗产,任情挥霍,又没有什么人来管她,凭着那几个流氓,要借多少就是多少,不上几个月,差不多把杨梅窗一生辛苦挣下来一分小小的产业,一齐花在太平洋里去了。手头渐渐的不给起来,杨小姐挥霍惯了的人,那里过得这般拮据的日子?一班流氓,便撺掇她摆个碰和台子,招接客人。杨小姐想想,无可奈何,只得依了。自从摆子碰和台子之后,说也奇怪,竟是接接连连的,客人络绎不绝,生意兴拢到得后来,竟是苏州城内,没有一个不晓得这位杨小姐的名气。差不多仓桥宾里,有些名气的倌人,也没有她这般的生意。
这且暂时按下,再说苏州吴县,有一个皂班差役,官名叫做邵升,却是个奸刁阴险的东西。平日之间,倚着官势,在外面招摇撞骗的无所不为。那署事的知县,叫做方国珍,又把他当做走通线索的羽翼,甚是倚仗着他。邵升得了方国珍这般看待,越发的得意扬扬,横行无忌。不想过了一年,方国珍署事期满,例应交卸。藩台便挂牌委了个候补知县郭宝华,前来署理。这郭宝华是个拔贡出身,性情风厉,操守清廉,却有一样坏处:问起案来,专看人家的相貌,只要相貌良善些的,就是的的确确是个凶手,他也要想个法儿,和他开脱;若是相貌生得凶恶些儿,就是真真冤枉,他只说看你这个面貌,就不是个好人,一定要把他屈打成招,方才肯罢。有了这般的脾气,那些承审的案子,不免就有许多冤枉的人。这一面藩台委他署理吴县,他便拣了一个日子,接印点卯,点到邵升的名字,邵升答应一声,走了上来。这位郭大老爷举目看时,却却的冤家遇着了对头,只见他缩背拱肩,尖头圆眼,那一付奸滑的样儿,明明的露在面上。郭宝华看了,不知怎样的,好像和他有什么冤家一般,不觉登时大怒,把惊堂一拍,喝道:“看你这样形状,一定不是好人!本县这里用你不着。”一面骂着,不由分说,拍着旗鼓,拨下八枝笺来。值刑的皂隶,吆喝一声,那时满堂吏役,一个个心上骇然,彼此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想不出什么缘故。邵升也大大的吃了一惊,连忙跪上前去,分辩道;“小的无罪,求大老爷开恩。”郭宝华听了,更加大怒道:“你还敢在本县面前强辩!本县说你不是好人,难道是诬赖你的么?”
说着又喝叫:“着实与我打!”值刑的不敢怠慢,赶上前来,把邵升捺在地下,褪下裤子,一五一十的打了四十大板。这四十个大板,若是换了别人,就不打个半死,也要小小的发一个昏,幸而一班值刑的,都和邵升要好,打得还不十分厉害。当下打完了,磕头起来。郭宝华立刻把朱笔一勾,革了他的名字,吩咐差役把他轰出去。邵升垂头丧气的,被他们赶了出去,这一腔冤枉,真是梦想不到的。无妄之灾,好好的点卯,无缘无故吃了一顿板子,还把个名字革了,绝了他以后的生路。心中想着,越想越气,越气越恨,忽然想出个主意来。原来他想碰了这个钉子,从此不干这个差役的道儿,想要改了名姓,假充上流社会的人。好在这几年招摇撞骗,有的是钱。只要有了银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果能自此以后,邵升有志竟成,改了一个名字,叫做邵梓玉。穿得一身华丽的衣裳,学得一派时髦的应酬,竟也渐渐的有些大家子弟和他来往起来。那知就是这样的混了几年,那几个昧心钱儿,差不多慢慢的将要完了。老婆又得了个产后的热病,医治不好死了。邵梓玉办过了他老婆的丧事,还苦苦的支持着面子,恐怕人家看了他的内容出来,便又打算主意道:“照这个样儿,坐吃山空的下去,那里支持得来?不如想个法儿,续娶一房有些妆奁的老婆,倒也是今救急的法子。想定了主意,便托着许多朋友和他做媒,无奈总是高不成低不就,不是人家不肯给他,就是嫌着别人寒素。说了多时,还没有一些眉目。邵梓玉气闷不过,便天天到马路上兜个圈子,解解闷儿。忽然有一天,在马路上看见杨小姐,坐了马车过去,一头珠翠,哗哗有光,满面春情,融融欲化。手臂上带着四五付镯子,黄澄澄,金灿灿的,宝光夺目。手内更带着两个金刚钻戒指。看她那个样儿,定是个有钱的闺秀。又见他一人独坐,并没有什么同着的人,想来是没有什么拘束,可以自由的了。想到此际,由不得心中一动,便急忙也拣了一部极齐整的橡皮马车,跳上车去,吩咐马夫,只跟着前面的一部马车。那马夫听了,把马加上一鞭,飞一般的赶上前去,只跟着那一部马车,来来往往的在马路上兜了几个圈子。邵梓玉坐在车上,目不转睛的只看着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也似乎已经觉得他盯梢的意思,每到马路转弯的时候,便把那一对水汪的秋波,朝着邵梓玉飞了几个眼风。邵梓玉见了,喜得心花怒开,十分畅快。跟着她兜了几趟,那马车停在蔚南村大菜馆门口。
那女人袅袅婷婷地走下车来,看了邵梓玉一眼,就进去了。邵梓玉连忙付了车钱,也跳下来,跟着上楼。见他走进三号房间去了,邵梓玉掩在门口一看,见并没有第二个人,就是那女人一个,坐在那里。邵梓玉便走进他隔壁四号房间坐下,等那侍者进来,邵梓玉便问他,可认得三号房间里的女人?侍者微笑道:“他天天到我们这里来的,那有不认得的理?”便把杨小姐的历史,细细地告诉了他一遍。又道:“你不要看轻他,他的生意,比一等的红倌人,还要好些。倒是个有钱的人呢。”这一句话儿,正打在邵梓玉的心上,便向侍者说道:“你过去招呼一声,说他吃的不论多少钱,我都给了。”那侍者看着邵梓玉的面孔,嘻嘻地笑了两声,答应了出去。不多一刻,又走了进来,向邵梓五笑道:“杨小姐说,请你那边去坐罢。”邵梓玉听了叫他过去的一句话,就是做官的得了升官的信息一般,连忙恭恭敬敬地走了过去。杨小姐见他进来,立起身含笑相迎,两下说了几句套话,就彼此熟落起来。杨小姐天天到马路上去出着风头,原是为勾引客人起见,况且邵梓玉有心笼络,拼命地巴结她。杨小姐看着这个人,倒也并不讨厌,和他谈谈说说,甚是投机。吃完了饭,又同到新丹桂去,独包了一间包厢,却只有杨小姐和邵梓玉二人同坐。这包厢的钱,不消说是邵梓玉的了。直看到十一点钟,杨小姐方才进城,邵梓玉也自回去。
夜里头睡在牀上,便想怎样的骗他嫁我,怎样的哄他的钱。忽然又转一个念头道:“不好,不好!我虽然是个差役出身,那一班新结交的朋友,却都不晓得我的底子,现在平空的把一个半开门的私巢子娶做老婆,他们岂不都要笑我是个乌龟么?”想了一回,又拍着胸脯道:“我原是想骗她的钱,并不是要她的人。如今的世界,银钱为重,只要有了银钱,不要说这个乌龟的名目,本来是个假的,就是真的乌龟,也做她一做何妨?但是既要去骗她嫁我,一定先要花些本钱,装个有钱的人,在她身上,极肯花钱的样子,方才骗得动她。只是自己的钱,用得差不多了,那里来这一注本钱?”想来想去,想了多时道:“也罢。我也顾不得了,这一所祖传的房子,约摸也值几千块钱,只好把它卖了,做个孤注。”想定了主意,隔了一天,便托人去卖这所房子,只说他老婆死在这个房子里头,嫌它有了死人,甚是不利,现在想要续弦,不愿意再在这房子里头办事,所以要把它卖了,自己另外再寻合意的地方。这一番假话,说得甚是相像,倒也没有疑心他的人。果然不多时,寻着了一个主顾,把房子卖了。除掉中费一切之外,邵梓玉净得了三千块钱。便成日成夜的到杨小姐那里鬼混,巴结得杨小姐十分欢喜。
看官,你想杨小姐做了这碰和台子的生意,却免不得要应酬客人,就是心上有些不愿意的地方,也是无可如何。现在被邵梓玉拼命的拍着马屁,又把卖房子的那几千块钱,水一般的都用在她身上,便觉得来往的客人里头,从没有遇着邵梓玉这样一个温柔体贴的人物。杨小姐说什么就是什么,差不多杨小姐的溲盆溺桶,他都肯把他顶在头上,放在手中。杨小姐一个年轻女子,那得不上了他的圈套?觉得天下的人,都没有邵梓玉好。邵梓玉又是拼命的朝她求婚,杨小姐不由得就答应了。
邵梓玉心中大喜,连忙去赁了一处房子,择个吉日,清音彩轿,鼓乐喧天,把杨小姐娶进门来,还叫了一班堂名,在家里打唱,甚是热闹。邵梓玉到了此刻,心上想着大功也是告成,她既然嫁我,她的钱就是我的,不怕她不拿出来。等将来慢慢的骗尽了她的钱,再想个法子,和她翻面,把她打发出门。那时我就安安稳稳的享这一分妻财了。心上这般想着,面上不说出来。
过了月余,邵梓玉卖房子的钱,看看又要完了。他晓得杨小姐有一对珠花,珠子最好,差不多要值到二千块钱。他便起了个念头,想先要骗她这对珠花,便对杨小姐说道:“你那一对珠花,样子扎得甚好,我一个表弟要娶亲,要说到珠宝店去扎珠花,没有时式的样子,想借你这一对,做个样子。”看官,天下妇女的性儿,最是吝啬,听了邵梓玉的话,把头一扭道:“我的东西,不借出去的。你为什么不当时回报了他?”邵梓玉道:“我已经一口答应他,说今天我自己送去。现在你忽然不肯起来,叫我怎样说法?”杨小姐听了,只是不肯,邵梓玉再三央告,方才勉勉强强地拿了出来,交给他道:“你拿了去,却仍旧要和我拿回来,换掉了我的珠子,我是不答应的。”邵梓玉连声答应,拿了出去,暗想她这般的吝啬,却怎样的骗她,看起来,只好如此如此的了,便拿了出去。隔了一天,杨小姐叫他去拿,他不肯道:“昨天才拿去的,今天怎么就要去拿,我倒有些不好意思,还是我们同到城外去,兜兜圈子,吃顿大菜罢。”杨小姐是散诞惯的,听得丈夫同他出城,便不言语。换了衣服,插戴好了,和邵梓玉坐着轿子,一同出城,先到大菜馆里坐着。邵梓玉托个事故,把杨小姐卖在城外,飞奔回来,用钥匙抻开了她的箱子看时,只见不过是些衣裳,又开第二箱时,也是如此,邵梓玉暗暗诧异,想她有一个首饰匣子,平时见她总安在箱子里头,怎么不见了,又开了衣橱看时,也没有个首饰匣子的影儿,寻了半天,没有寻着,正在东张西望,猛然听得外面轿子进来的声音,邵梓玉吃了一惊,手忙脚乱的,不及收拾,早见杨小姐匆匆地走了进来,见了这个样子,便和他大闹起来,要扭着他去见官。那时的吴县,正还是那位郭大老爷,邵梓玉就打了一个寒噤,不肯前去。夫妻两个,吵闹了一场,后来杨小姐也看出了邵梓玉的来历,晓得他只要有钱,别的都可将就,便和他说道:“你要钱不难,你只要听着我怎生摆布,不要来管我的事儿,你要用钱,只顾来问我要就是了。”
自此,杨小姐虽然嫁了邵梓玉,仍旧还摆着碰和台子,招接那一班旧日的客人,邵梓玉竟居然做了个开眼乌龟,扬扬得意的没有一点惭愧的意思。看官你想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不能养活一个老婆已经是诧异的了,这邵梓玉非但养不起老婆反靠着老婆的身体挣钱养他自己,还不晓得一点羞惭,真是个脸厚三尺,胸无一丁的凉血动物,和那江念祖把自己的姨太大认做女儿,嫁给安弼士做了外室,这些忘廉丧耻的事情大同小异,都也差不多。所以在下借着他做个无耻奴的收束,如今的世界那里还有什么品行!那里还有什么廉耻!在下做书的把他们演说出来,虽然可笑,觉得又甚可怜,但是天下之大无耻的人,就如恒河沙数一般,在下这区区四十回书那里说他得荆不过就着在心目中间的一班人物,把他提演出来,或者将来隔了几年,在下的阅历深了些儿,再有引起卑鄙龌龊的人物印在做书的在下脑筋里头,便再出一部无耻奴后集,做个禹鼎烛奸,温犀燃怪,也未可知。
正是:一掬牢骚之泪,事情荒唐;十年阅历之谈,风波险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