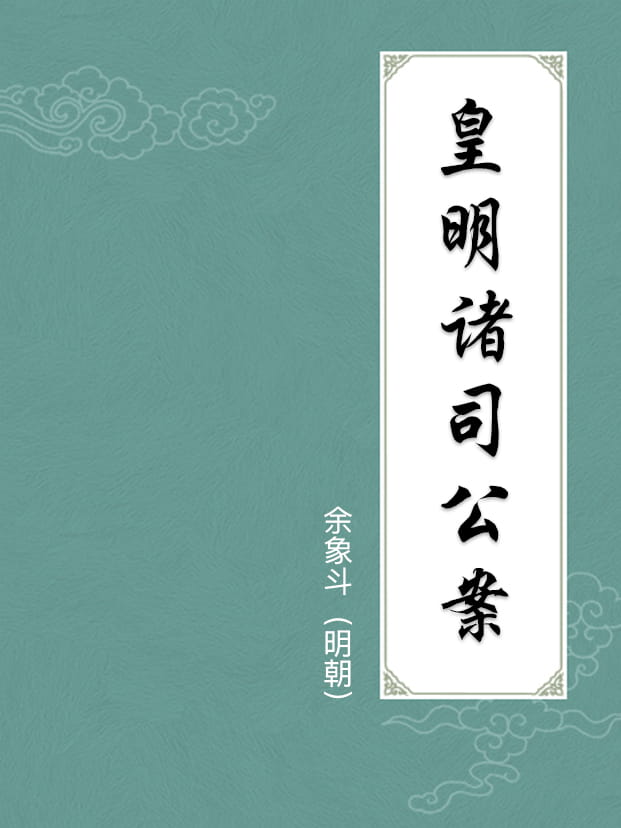杭州民朱必流,初在堂当皂隶,好饮酒喜□。门子所撰钱,随得随用。乃将皂隶本去当□,又不能供纳利息,后全卖出来,遂无生理。只与光棍之徒趋东奔西,着日挨度。因思量做贼,买一把鼠尾尖刀,常怀在身。一日,将往乡下,在高卓亭憩步。林木阴茂,前后无人。有一光棍计握权者,腰带鸡束,藏两桃在,独荷一伞,亦来到亭。
必流叹气曰:“这热天走路,汗如下雨,口如焦釜,真是辛苦。惟有钱雇轿者是天子命也。”
握权夸曰:“坐一乘轿者便是天子,我这鸡束中还雇得几乘,是我做得几个天子也。”
必流看其荷包,果有两块高起,疑必是银。及握权先行,必流右手持鼠尾刀在袖,左手倚握权之肩而行。
握权曰:“下岭我也难行,何故倚人肩。”
必流曰:“我走路不得,倚行数步无妨。”
遂以左手按其颈,右手持刀刺其咽喉,随手而殒。遂探其鸡束中银,取出乃是两桃。心下悔错,急挨青而逃往乡下去。后人来至亭中,见路傍谋死一人,聚众呈明于官。官委人收贮,即埋于路傍。十数日后,必流从乡下回,复过此亭,见前所谋人,已埋殡讫,自幸无人知觉。
乃检途中黑炭,写于亭柱曰:“你也错,我也错,我在杭州打毕剥。你若取我命,除非马头生两角。”写完而去。
盖马不能生角,彼谓此人不能取彼命也。过两月,察院冯谦底公巡按浙江,将临杭州,从此亭经过。忽一阵黑风从轿前起,冯院心下凛然。轿已进数步,见路傍有一新坟。
问手下曰:“此是那家的坟?”
杭州来接者曰:“不知何人,两月前被人谋死,官委人收埋在此。”
冯院心想曰:“黑风必此冢之冤魂也。”到亭,即命停轿散步于亭中。
四顾风景,见柱上写数句字,未云:“要取我命,除非马头生两角。”
心臆曰:“此必谋人贼所题也。”思之不得其故。
及到杭州,众官参见后闭门不出,沉思亭中之语。过第三日,天骤雨,屋有一点漏,正坠在案上朱笔头。初亦不觉,渐久水渍朱湿,红流于案,方见朱笔流红。
乃问一门子曰:“杭城有人名朱必流者否?”
门子曰:“有其人,先亦在衙门,今出外为光棍。”冯院即升堂开门,仰府速拘朱必流来。移时,即拿到。
冯院曰:“你在高卓亭谋人得财多少?可自供来。”
朱必流曰:“小的在城生理,并未到亭,何知谋人事?又何为问得财多少?”
冯院曰:“杭城百姓无虑数万,单拘你来,自然我是知实了。且你自题柱有言‘你要取我命,除非马头生两角’,今我姓冯,是马头生两角。你当还他命无疑矣。但起头两句说‘你也错,我也错’是如何讲,可好好供来,免受刑法。”
朱必流见说起亭中题字,又大巡姓冯,果应口谶,自知分当偿命,遂直招曰:“老爷果是生城隆,能于杭城百万民中单拿出我,是果得真矣。我前月在亭中歇步,有光棍计握权,鸡束中藏两个桃,自夸他是银,我因此谋他。及解看是桃,是他说银者也错,我谋他者也错。我谓马头不能生角,谋时并无人知,他必不能取我命。今老爷姓冯,是马头两角,我当还他命,乃天数排定也。”遂拟死偿命,亦不加刑。满城人无不羡冯爷神明者。
冯院判曰:“审得朱必流游惰棍徒,贪残浪子。东流西荡,资身无粥之谋;前突后冲,恶念起盗贼之计。潜形高岭,思鼠伏以伤人;隐迹深林,欲阻击而害物。人炫有而为盗,诚为自取之灾;伊见利而生心,岂非自作之孽!绿林之下,白刃横飞;长途之中,短刀骤刺。欲图厚利,故越人而不辞;探得余桃,虽悔措其何及。方幸漏网之罚,敢为题柱之词。须信马角易生出,出尔必应反尔;谁云口域无验,伤人适以自伤。冤抑鬼来诉,轿外之旋风起黑;姓名天自报,案头之朱笔流红。谋财虽未得财,害命必然偿命。据情已实,拟死何辞。”
按:黑风吹轿,冤情易猜。漏雨流朱,知名不易。此固冯公之积诚所致,抑亦天牖其聪也。盖观马头两角,早著兆于寓言。则冤仇报复,岂偶然哉!人其慎于独知,充善过恶,勿谓天远无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