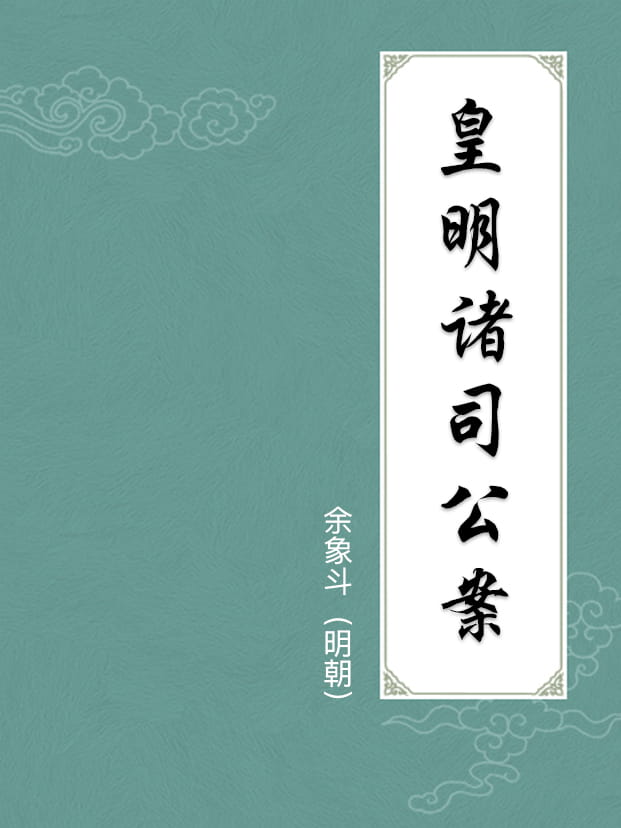浑州上里民费牖,家富万金。娶妻倪氏丑而无子,尝不惬意于夫。倪氏又无亲父母兄弟,茕然无倚也。牖乃娶妄殷氏,美而有能,甚快夫意。即命之掌管家务,而倪氏益宠衰,无权如闲废人矣。未几而殷氏生子,名费弘光。长而伶俐、聪明,父钟爱之。母宠,子肖,父爱,夫偏。倪氏惟抑郁抱忿,年月累久,渐成痴懦。
既尔夫死,殷氏益刁蹬之,其痴愈甚,言语无序,笑哭不常。亦或行乞于人家,去住无定。乃全赶追之,不许人家。时或心孔暂明,亦知控诉于官。及官审问之,又言颠语倒,不知应答。以此官以为狂,皆不为直其事。王罕为司理,严明慈祥,肯切心为民。倪狂妪又在路诉告,言无伦次,从骑欲屏逐之。
王司理曰:“狂妪或有故而诉,不然狂人必不妄投官也。”引归衙叩问之,狂枢虽言语杂乱,然时有可采者。
王司理谓手下曰:“狂人皆痰迷心窍,心神荧惑,故不能自主。你可于药店讨化痰九、镇惊丸来,与服得,彼迷痰暂开,即取问之。”
手下依言,与之午饭,服以牛黄丸、辰朱砂等药,然后引问。王司理执笔在手,令倪妪道来。其中间胡乱语时有。参其前后言说,乃知是浑州上里富民费牖之嫡妻,以无子夫死,后为其妄殷氏及庶子费弘光所逐。王司理以富子逐狂母,虽有于证,彼必买赂不认。乃先行牌该县,但浑州上里地方有告状者,仰县解馆亲问。时适有民争田土者,其干证费以约解到。
王司理不问田土上事,但问曰:“汝里中有个费牖否?”
以约曰:“是我五服内之故兄。”
王曰:“彼有妻子否?”
以约曰:“他富家,有一妻倪氏,一妄殷氏,子名弘光。”
王曰:“他妻妄都在否?”
以约曰:“他妄在,其子即庶出。其妻狂懦,流外失落。”
王曰:“倪氏外家更有何人?”
以约:“闻倪氏早无兄弟,未知其更有甚亲,但有倪广者,曾与我事卖买。那人亦老实,有二子,名大本、立本,本亦是倪氏从堂姑侄。”
王曰:“费牖有亲兄弟否?”
以约曰:“无,止有从堂弟费镛、费黼。”
王曰:“汝有几子?”
以约曰:“有三子,弘大、弘中、弘正。”
王司理发费以约一起人出外候审。即行牌去拘费弘光、殷氏、费镛、费黼、费弘正、倪广、倪立本等一干人。既到府,弘光始知嫡母之告己,即贿买堂叔镛、黼共证勿认,以避逐母之罪。
及提倪氏与子审,王司理曰:“你何为逐母不供?”
弘光曰:“小的父母都死,埋葬已久,只生母在,何为更有母?可问我亲叔即知。”
镛、黼触曰:“弘光嫡母果死,埋了。”王司理问倪广曰:“此狂妪是汝姊否?”
倪广曰:“姊出嫁年久,今不能认。”再提费以约来问曰:“此狂妪即弘光之嫡母,是否?”
以约本认得人,先已吐实于王爷之前,即认曰:“此正弘光之嫡母也。”王爷将殷氏一,弘光逐母打三十。
镛、黼偏证,各打十五,俱拟罪。再将费家万金之产,以四千与弘光。又为倪氏立二侄费弘正、倪立本承嗣,共分业六千两,各给帖执照,比□批于帖。令弘正、立本宜孝养倪氏,如有一不孝,即告逐出,专以一为后。二人骤得厚产,争相孝奉,胜于亲子。倪氏心乐神舒,不二岁,偏狂症寻愈。每朔望;”必率二嗣子弹祝王爷官高寿长者。
王公判曰:“子以母为天,小无加大;妾以嫡为主,卑不逾尊。大舜之母至嚣,惟号泣而怨已;归妹之姊虽善,亦恒德以相君。稚子私焚,申夫人尚尔呵责;尊长任事,陈义门所以久居。故世无不是之萱堂,特患有不才之胤嗣。今殷氏为费牖之孽妾,弘光乃倪氏之庶支。只合朝夕寅恭,奉唯诺于主母;惟应恪其子职,展定省于慈阑。乃忘姆训之三从,鸦振羽而搏凤;却效浅人之六逆,枭锐嘴而啄鸠。乘庸懦之易凌,不知救恤;任流离于道路,罔念懿亲。以今日执对于堂,且坚不识认;则昔日挫抑于内,必恐尔欺陵。强凌弱,贱压尊,岂是贤姑之行;弃天亲,团长上,殊惭令子之规。宜服不敬不孝之刑,方为无仁无义之戒。姑念费牖惟一子,且留妄庶之两生。仍为倪氏过房,庶几老有所养;且为嗣子给照,或可杜其所争。费黼、费镛偏汪,还拟不合;弘正、立本堂侄,俱可承宗。”
按:狂妪告诉,状无可准,言无可听。王公独细心采其言,先事求证,然后方提孽庶,立折其罪,则恶有所惩。又为狂妪立继,责以孝养,则人思承其业,必务孝其人,而老有所倚。王公之处事精密,爱惜废人如此,虽天地父母之心不过是也。可为敬老哀矜者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