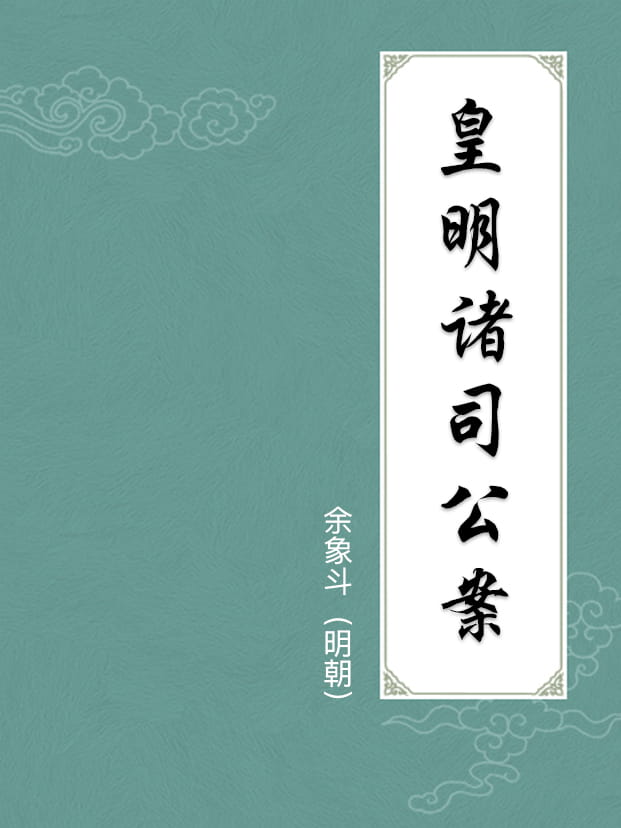扬州民勾泰,家颇饶足。年四十,止生一子,已三岁矣,甚爱惜之。一日偶出,路逐群儿戏,迷不知归,呱泣于途。人过者亦不之顾。一光棍见此儿手带银镯,自泣良久,又无人携抱,料是迷失归途者。
乃去抱之曰:“吾与若归。”
此儿泣久,得人提抱,自然泣止。彼即抱出城外十余里。有一富民赵奉伯,年老无子。光棍将此儿卖与之,得银二两而去。奉伯与妻郑氏,抚爱此儿如亲生无异。勾泰四处出赏帖寻求,不能得见。过了一年,适往城外去取苗租,经奉伯门首过,见此儿在门外嬉戏。勾泰细看之,愈似己子。呼其乳名,儿亦知应。久看之,儿亦似认得熟人,渐与勾泰狎近。
乃问其近傍人曰:“此谁家子?”
傍人曰:“此赵奉伯之子。”
勾泰曰:“彼亲生的抑是抱养的?”
傍人虽知是养子,只为之回护,曰:“自然是亲生的,你何须问他?”
勾泰不信,径入奉伯家曰:“我有儿名一郎,旧年三岁被人抱去。今你此儿是我儿也,须当还我。”
奉伯曰:“老兄好差,你旧年失儿,我儿是从幼亲生的,安得云是你儿?天下儿子同面貌者何多,休得要痴想也。儿子岂是妄占得的?”
勾泰曰:“缘何与我甚熟,呼他名又应?”
奉伯曰:“我儿常不择生熟人,都与他习熟,他亦名作大郎,故你呼一郎亦应也。老兄乃痛伤而迷耳,何故若此痴也?”
勾泰口争不得,心不能舍,即往府告曰:“状告为取子续宗事:泰年逾四十,止得一子,乳名一郎,宗桃实攸。旧年三岁,门外嬉游。陡遇败豪赵奉伯,潜地抱去。今亲寻见,往门里取,彼侍刁强,白占不还。切老景一儿,嗣关绝续,是我天性,伊占何益?乞断儿归宗,惩恶兴贩,阴德齐天,万代衔思。叩告。”
赵奉伯遂买嘱邻佑,硬作干证,亦到府诉曰:“状诉为飞空占子事:父子天亲,不假人为。骨肉至爱,难容白夺。奉伯家足度日,何曾兴贩?亲生一子,并非抱养。历今四岁,邻里周知。悬遭奸豪勾泰冒认为子,平地生波,雪中布桥。彼非病狂,必有唆陷。乞亲提洞察,杜奸保婴,感激上诉。”
时李崇为知府,最贤明,有治才。数日提到来问,勾泰称为己子,朗朗可听。赵奉伯认是己儿,历历有征。难以断折,乃再取干证审问。原告边干证执是勾泰之子,被告边干证争是奉伯之儿,又难凭据。
李太府心生一计,乃曰:“这干证都是买来偏证的,都不要。你儿子可令赵家领出抚养,待我差人密访得出,然后重惩此囚奴。勾泰、奉伯且权收监候。”
忽然过了七日,李太府召禁子曰:“前勾泰、奉伯为争一儿子,收候在监。今吊审皂隶,报此儿子昨已中惊疯死,两不必争了,可放出来发落他去。”
禁子入监言之。勾泰闻言涕泣横流,悲不自胜。奉伯惟嗟叹而已,殊无痛意。禁子引二人人府堂。
李太府曰:“此儿子既死,你二人不必争了,可都去罢,免供招。”勾泰泪注如雨,下堂即放声而哭。奉伯只是叹气数声。
李太府乃复召回曰:“今事已然矣。你二人可说个凭心话,此儿还真是谁的?”
奉伯曰:“真是小人的,只福薄难招此子也。”勾泰曰:“你尚且欺心,本是我的,想你家怕老爷断出,故加毒害也。”
李太府曰:“人心不公乃如此哉!此儿岂真有死理?盖可承家万代也。特假此试汝二人心耳。此儿明是勾泰的,故闻死而深悲。奉伯惟略叹息,便见非天性至亲,故不动念也。今此儿当归勾泰。”即命领去。
欲加奉伯刑,乃供出昔用银买得,非己之兴贩人口也。
李侯判曰:“父子天亲,不假人为。死生大变,乃见真性。今勾泰连老得子,惜如掌珍。出外忘归,茫如丧命。想昔孤雏之失道,何弄彀雀之离巢。赵奉伯虽买自棍徒,原非贩卖,但认于亲父,理合送还勾姓。非赵宗,岂楚方而楚得。人心合天道,自塞马而塞归。胡乃执迷,坐生讦讼。及至谬传诈死,全无悲心;便非属毛离衷,故不溅泪。尔不予人之子,人安亲汝为亲。骨肉重完,一郎自欢。有父箕裘可绍,勾老岂恨无儿。思移异姓以承宗,奉伯宜加深罚;姑念辛勤于抚字,计功且示薄惩。”
按:勾、赵皆富而无子,其争必坚。幼儿又无知,何以辨之?惟诈传儿死,则亲父必然痛心,养父自不深悼,便可知其真伪矣。其妙全在此处也。